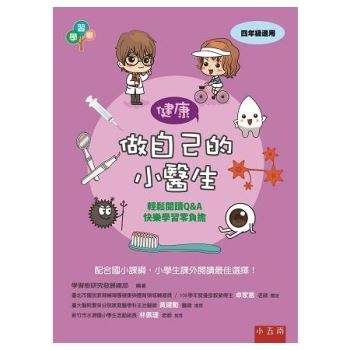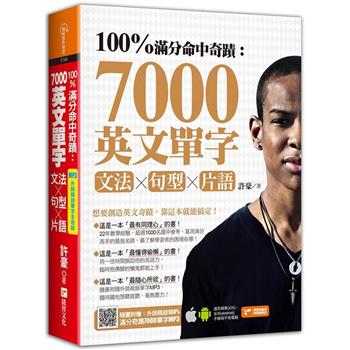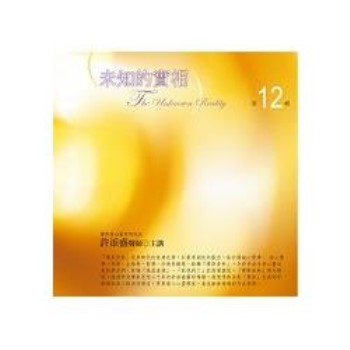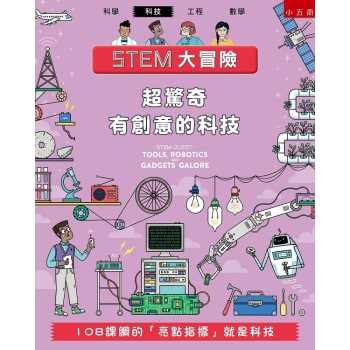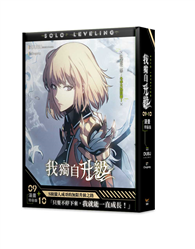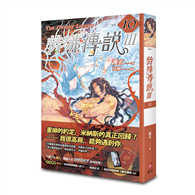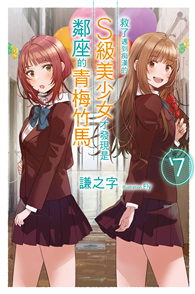生物學家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以自然現象為討論起點,是本書嘗試用來述說生醫科學知識的基礎。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中,利用生醫科學的案例來跟科學史/STS學者對話。基於生物的特殊構成、動態的生命現象等等面向,重新討論孔恩關於科學變遷的觀點。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的內容呈現生醫科學研究的策略。在討論理智能力天生的侷限之外,透過科學辯論的文本,來說明生物學家克服困難的方案。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是鳥瞰式的年代紀,將近代生醫科學的發展依序分成:觀看、分離提純、變化路徑、結構、預測與工程五個年代。透過分析各時期經典文章的研究手法,來呈現知識樣貌的變遷:由強調感官、對照組設計、以實在物為基礎的最佳說明推論,到不得不借重儀器、數學分析工具,進而建立以功能干預為基礎的因果關係。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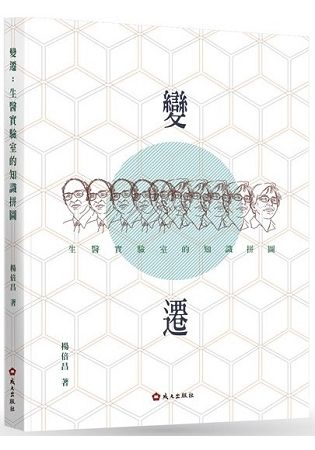 |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 作者:楊倍昌 出版社: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8-03-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44頁 / 15 x 21 x 1.8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教育學習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健康醫療 |
$ 340 |
醫療保健 |
$ 360 |
醫學總論 |
$ 380 |
教育學習 |
$ 380 |
生命科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
內容簡介
目錄
推薦序/賴明德
推薦序/陳瑞麟
前 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
第一章 閱讀孔恩《結構》之台灣帖
第二章 常態研究與新理論
第三章 看見孔恩的異例
第四章 孔恩,或者不孔恩的生物科學史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
第五章 演化之下,人類為什麼會保留錯誤的認知模式?/副篇:答客問
第六章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實作科學家之間的辯論/副篇:答客問
第七章 證據與想像交纏的生物醫學:以「Fas 反擊」理論的起落為例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
第八章 觀看的年代
第九章 分離提純的年代
第十章 變化路徑的年代
第十一章 結構的年代
第十二章 預測與工程的年代
第十三章 由科學革命的結構到生物醫學的未來
後 記 另類的「惡補齋」
附 錄 當生物學遇到 STS
推薦序/陳瑞麟
前 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
第一章 閱讀孔恩《結構》之台灣帖
第二章 常態研究與新理論
第三章 看見孔恩的異例
第四章 孔恩,或者不孔恩的生物科學史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
第五章 演化之下,人類為什麼會保留錯誤的認知模式?/副篇:答客問
第六章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實作科學家之間的辯論/副篇:答客問
第七章 證據與想像交纏的生物醫學:以「Fas 反擊」理論的起落為例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
第八章 觀看的年代
第九章 分離提純的年代
第十章 變化路徑的年代
第十一章 結構的年代
第十二章 預測與工程的年代
第十三章 由科學革命的結構到生物醫學的未來
後 記 另類的「惡補齋」
附 錄 當生物學遇到 STS
序
前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西式的現代科學屬於「訴說型的知識」,「說明」是知識得以成立的要件,也是大學裡重要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碩、博士研究所的課程中,多半會安排專題報告、書報討論來演練科學說明與溝通。只是,台灣的一般教學方式以大講堂授課為主,讓學生口頭表達的機會不多。每次輪到上台報告,學生總是緊張的不得了。此外,因應英文為科學通用語言的現況,學生也必須學會使用英文來報告研究成果。對於新手學生來說,要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常常陷入缺乏科學知識與外語能力的雙重負擔。
後來,有些學生想出一種取巧的辦法:設計投影片時,在呈現實驗結果與圖表之外,直接在畫面上寫好完整的英文結論句。簡報當下,先忠實地按照投影片上的英文句子念一遍,然後指著投影圖表直接說:“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一開始,覺得他們說的「英文」還算順當,後來發現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來拼湊「數據」的手法就跟元代詩人馬致遠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手法一樣,讓讀者在腦袋裡自己組裝風景印象、自己建構意義。對沒有親身體驗的人而言,看不到畫面,就學不到新東西。而且,這種表達手法缺乏推論的過程,只是一堆零碎結果的疲勞轟炸,讓人跟不上演講者所要表達的意思。“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跟以「專業行話(technical jargon)」為基礎的演講形式一樣。專家之間的討論,透過行話,三言兩語簡潔又明確;對初入門的新手,或異領域的聽眾來說,過多的行話只是一種用來讓人墜入迷霧的伎倆。以訓練學生溝通的目的而言,這種演講方式並不理想。
對於學生使用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表達方式,我深感同情。這幾年來談論科學時,我也常常陷在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或是必須夾雜行話來述說科學的尷尬與懊惱。這種尷尬與懊惱就跟畫家對著空白的畫布,或是小說家看著稿紙上的空格的情況一樣。以教書為職業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說明自己的「科學」,又如何能稱職呢?
在大學講課時,最常讓我陷入詞窮窘境的課是:「科學的邏輯─以生物學為例」與「近代生物科學思維的變遷─史學與哲學考察」。這是兩門通識課,學生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課程的內容是利用生物科學的研究素材,來闡述科學發現的歷程,帶一些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趣味,期望可以深化學生的觀察與分析能力。原先以為科學家講述自己的經驗應該不難,沒料到解說的過程非常吃力。面對來自不同領域的台灣大學生不只需要跨越轉譯的語言障礙,還必須面對文化的差異。課堂上,有位學生的提問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多年。他說:
嚴格說來我們僅有的只是在西方科學應用的知識,但由於沒有像他們一樣的歷史背景,當我們在學習他們的系統時,還是純粹的使用原來中國的習慣來學習這套西方的科學。我認為台灣的社會並不具有西方科學的知識,充其量我們有的只有西方科技及其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這位學生所指出的缺乏,是科學發現的歷程中科學邏輯與方法論、知識論、倫理學等等求真、求善的精神。科學精神不存在,照本宣科就只是勉強學個樣。它不只是教育的議題,不只是科技的知識經驗,還有重建在地科學文化的想像。困難在於,所謂的「中國的習慣」、「西方的科學」到底是什麼,如何呈現呢?對於不參與科學實作的人而言,「科學家」日常到底在做什麼?科學精神展現在那些事情上?台灣的大學生怎麼會有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印象呢?會不會是他個人的要求太高了?這些問題都不是憑著常識就可以輕易回答的。
2005至2012年間,我針對上課時學生的提問議題,出版了《看不見的工具》和《科學之美》兩本書。這兩本書的內容略過了傳統科學哲學家所關注的問題與爭論,也不談論英美科學哲學界的主流思想的得失,純粹以實作科學的經驗來說明我對於現代生物學的見解。對於這種在地提問、自我凝視的書寫方式,哲學家陳瑞麟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挑戰:
楊有很多科學研究成果和一組哲學(方法論)論點。可是,不像波以爾的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他的科學研究內容(空氣泵浦實驗)緊密結合,楊的科學哲學和他自己的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對這兩本著作提出的第一個評論,也是對楊的一個挑戰:是否能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
實驗室是實作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場域。科學家自己對於研究的雜事多半也是日用而不知。常常要等到做錯了、被考倒了、被提醒了、撞到了牆,科學家才會反省檢討。生物學家習慣的說理手法與專業哲學家不相同;對我而言,要「將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科學研究內容緊密結合,並且合理說明」的難度,並不亞於新手學生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時所面臨的負擔。面對台灣多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只是拼湊一堆名詞,「邏輯實證社會建構論;否證常民行動者網絡」、「波普孔恩維根斯坦;拉圖傅科費耶阿本」,後果應該會跟“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剪貼手法一樣,肯定會搞得許多都人頭痛,達不到解說、溝通交流的效果。
此外,找尋共同的認知基礎是另一個必須克服的困難。一般人對於生醫實驗室的刻版印象,在親自到實驗室觀察後,可能會被實際的工廠氛圍所顛覆而感到驚訝:
原本想像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人員進入前都必須做好萬全的防護措施,就像進入手術室那樣,而做實驗是一個令人緊張的過程;但實際上,實驗過程動作不斷重複,節奏相當穩定、單一,加上有音響播放音樂,研究者穿著也算輕便,反而有點像工廠。不過透過這些不斷重複的動作,以及大量的樣本,才讓我能夠理解實驗的「精確性」與「必要性」指涉的事。
近年來,人類文化學者以實驗室為田野,將科學家當作部落來觀察。有系統地以文化誌的角度探索生醫實驗室,最著名的研究是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書中透過甲狀腺激素釋放荷爾蒙(thyr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發現案例,記錄生物學家日常討論的內容、時間、手勢、語氣,作為分析事實建構的基礎。他們在現場勘查也包含實驗室的空間配置,用來呈現文獻與儀器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幽微的解說方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面相。對我來說Latour及Woolgar在《實驗室生活》所描述的科學場景,跟我自己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認知經驗不相同,缺了共同的對話基礎,只是抱怨他們的「理解有差異」,連爭論、吵架都有困難,根本於事無補。
討論科學知識發展時,找尋合適的在地語言與共同的對話基礎,是我所關注的課題。總結近幾年與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的學生討論生物學的經驗,我的體認是:有效的溝通,大多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以自然現象為討論起點,不要因為麻煩瑣碎而只想說結論。這個方法學包含三項原則:一、問題宜具體,不要太大。討論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握的大問題常常徒勞無功,反而阻礙溝通;二、不用假設性的虛構事件當作推論基礎;三、以科學實作的歷程作為對話的起點。不只是通識層級的討論課,這些原則對於碩、博士班介紹科學新知的專題討論也同樣適用。生物學的研究雖然繁雜,事實上每一項實驗都相當具體,理解的門檻並不高,大部分的新手學生也都可以理解。在跨領域的科學溝通過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建立共同的對話基礎,雖然了解實驗過程需要花時間,至少容易聚焦,降低發生雞同鴨講的機會。
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討論知識論、科學哲學會不會比較好?能達到「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的理想嗎?不試試看,我也不知道。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這本書就是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的實驗。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西式的現代科學屬於「訴說型的知識」,「說明」是知識得以成立的要件,也是大學裡重要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碩、博士研究所的課程中,多半會安排專題報告、書報討論來演練科學說明與溝通。只是,台灣的一般教學方式以大講堂授課為主,讓學生口頭表達的機會不多。每次輪到上台報告,學生總是緊張的不得了。此外,因應英文為科學通用語言的現況,學生也必須學會使用英文來報告研究成果。對於新手學生來說,要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常常陷入缺乏科學知識與外語能力的雙重負擔。
後來,有些學生想出一種取巧的辦法:設計投影片時,在呈現實驗結果與圖表之外,直接在畫面上寫好完整的英文結論句。簡報當下,先忠實地按照投影片上的英文句子念一遍,然後指著投影圖表直接說:“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一開始,覺得他們說的「英文」還算順當,後來發現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來拼湊「數據」的手法就跟元代詩人馬致遠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手法一樣,讓讀者在腦袋裡自己組裝風景印象、自己建構意義。對沒有親身體驗的人而言,看不到畫面,就學不到新東西。而且,這種表達手法缺乏推論的過程,只是一堆零碎結果的疲勞轟炸,讓人跟不上演講者所要表達的意思。“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跟以「專業行話(technical jargon)」為基礎的演講形式一樣。專家之間的討論,透過行話,三言兩語簡潔又明確;對初入門的新手,或異領域的聽眾來說,過多的行話只是一種用來讓人墜入迷霧的伎倆。以訓練學生溝通的目的而言,這種演講方式並不理想。
對於學生使用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表達方式,我深感同情。這幾年來談論科學時,我也常常陷在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或是必須夾雜行話來述說科學的尷尬與懊惱。這種尷尬與懊惱就跟畫家對著空白的畫布,或是小說家看著稿紙上的空格的情況一樣。以教書為職業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說明自己的「科學」,又如何能稱職呢?
在大學講課時,最常讓我陷入詞窮窘境的課是:「科學的邏輯─以生物學為例」與「近代生物科學思維的變遷─史學與哲學考察」。這是兩門通識課,學生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課程的內容是利用生物科學的研究素材,來闡述科學發現的歷程,帶一些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趣味,期望可以深化學生的觀察與分析能力。原先以為科學家講述自己的經驗應該不難,沒料到解說的過程非常吃力。面對來自不同領域的台灣大學生不只需要跨越轉譯的語言障礙,還必須面對文化的差異。課堂上,有位學生的提問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多年。他說:
嚴格說來我們僅有的只是在西方科學應用的知識,但由於沒有像他們一樣的歷史背景,當我們在學習他們的系統時,還是純粹的使用原來中國的習慣來學習這套西方的科學。我認為台灣的社會並不具有西方科學的知識,充其量我們有的只有西方科技及其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這位學生所指出的缺乏,是科學發現的歷程中科學邏輯與方法論、知識論、倫理學等等求真、求善的精神。科學精神不存在,照本宣科就只是勉強學個樣。它不只是教育的議題,不只是科技的知識經驗,還有重建在地科學文化的想像。困難在於,所謂的「中國的習慣」、「西方的科學」到底是什麼,如何呈現呢?對於不參與科學實作的人而言,「科學家」日常到底在做什麼?科學精神展現在那些事情上?台灣的大學生怎麼會有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印象呢?會不會是他個人的要求太高了?這些問題都不是憑著常識就可以輕易回答的。
2005至2012年間,我針對上課時學生的提問議題,出版了《看不見的工具》和《科學之美》兩本書。這兩本書的內容略過了傳統科學哲學家所關注的問題與爭論,也不談論英美科學哲學界的主流思想的得失,純粹以實作科學的經驗來說明我對於現代生物學的見解。對於這種在地提問、自我凝視的書寫方式,哲學家陳瑞麟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挑戰:
楊有很多科學研究成果和一組哲學(方法論)論點。可是,不像波以爾的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他的科學研究內容(空氣泵浦實驗)緊密結合,楊的科學哲學和他自己的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對這兩本著作提出的第一個評論,也是對楊的一個挑戰:是否能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
實驗室是實作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場域。科學家自己對於研究的雜事多半也是日用而不知。常常要等到做錯了、被考倒了、被提醒了、撞到了牆,科學家才會反省檢討。生物學家習慣的說理手法與專業哲學家不相同;對我而言,要「將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科學研究內容緊密結合,並且合理說明」的難度,並不亞於新手學生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時所面臨的負擔。面對台灣多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只是拼湊一堆名詞,「邏輯實證社會建構論;否證常民行動者網絡」、「波普孔恩維根斯坦;拉圖傅科費耶阿本」,後果應該會跟“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剪貼手法一樣,肯定會搞得許多都人頭痛,達不到解說、溝通交流的效果。
此外,找尋共同的認知基礎是另一個必須克服的困難。一般人對於生醫實驗室的刻版印象,在親自到實驗室觀察後,可能會被實際的工廠氛圍所顛覆而感到驚訝:
原本想像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人員進入前都必須做好萬全的防護措施,就像進入手術室那樣,而做實驗是一個令人緊張的過程;但實際上,實驗過程動作不斷重複,節奏相當穩定、單一,加上有音響播放音樂,研究者穿著也算輕便,反而有點像工廠。不過透過這些不斷重複的動作,以及大量的樣本,才讓我能夠理解實驗的「精確性」與「必要性」指涉的事。
近年來,人類文化學者以實驗室為田野,將科學家當作部落來觀察。有系統地以文化誌的角度探索生醫實驗室,最著名的研究是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書中透過甲狀腺激素釋放荷爾蒙(thyr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發現案例,記錄生物學家日常討論的內容、時間、手勢、語氣,作為分析事實建構的基礎。他們在現場勘查也包含實驗室的空間配置,用來呈現文獻與儀器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幽微的解說方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面相。對我來說Latour及Woolgar在《實驗室生活》所描述的科學場景,跟我自己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認知經驗不相同,缺了共同的對話基礎,只是抱怨他們的「理解有差異」,連爭論、吵架都有困難,根本於事無補。
討論科學知識發展時,找尋合適的在地語言與共同的對話基礎,是我所關注的課題。總結近幾年與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的學生討論生物學的經驗,我的體認是:有效的溝通,大多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以自然現象為討論起點,不要因為麻煩瑣碎而只想說結論。這個方法學包含三項原則:一、問題宜具體,不要太大。討論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握的大問題常常徒勞無功,反而阻礙溝通;二、不用假設性的虛構事件當作推論基礎;三、以科學實作的歷程作為對話的起點。不只是通識層級的討論課,這些原則對於碩、博士班介紹科學新知的專題討論也同樣適用。生物學的研究雖然繁雜,事實上每一項實驗都相當具體,理解的門檻並不高,大部分的新手學生也都可以理解。在跨領域的科學溝通過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建立共同的對話基礎,雖然了解實驗過程需要花時間,至少容易聚焦,降低發生雞同鴨講的機會。
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討論知識論、科學哲學會不會比較好?能達到「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的理想嗎?不試試看,我也不知道。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這本書就是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的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