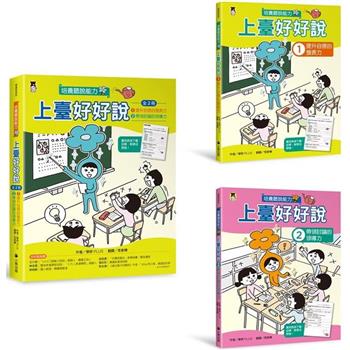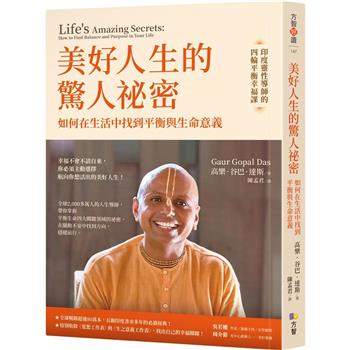第一章
道可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語譯
任何「有」、「無」之間的轉化方式只要呈現出某種方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轉化方式。任何「有」、「無」的表現形式只要表現出某種形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表現形式。
「無」可以稱為天地開始的起點,「有」則可以稱為萬物出現的源頭。所以,面對最根本恆常不變的「無」,我們應該觀察其如何轉化的各種奧妙,面對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我們應該觀察所出現之各式各樣的形式。「有」、「無」這兩個東西出自同一個源頭,卻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無」出自同一個源頭就表示「有」、「無」之間的轉化是循環的,循環轉化之後再繼續不斷循環轉化,所有各種萬事萬物變化的奧妙都從這裡開始。
註解
要了解老子在說什麼,一定要先知道老子的「道」、「名」、「有」、「無」這四個字的涵意。這四個字可以視為老子思想體系的基本範疇,老子的所有論述幾乎全部建立在這四個字上面。這四個字顯然是老子觀察大自然與人類社會之後,抽象歸納出來最宏觀、而且互相正交的基本特徵,也就是所謂「觀物取象」之後最終極的產物。我國古人所說的「象」是指一種針對思維對象全貌所萃取出來之整體性、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資訊,也就是任何一個「名」之所「指」的對象(景鴻鑫,2015)。至於從整體中取出那一部分的資訊成為「象」,則沒有一個標準化的過程,說的人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清楚,故一般人很難單純從字面上的「名」去理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這些基本特徵,則古聖先賢的思想與言論其實並不難懂,包含老子在內,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看世界的角度,以及理解世界所使用的框架。
老子《道德經》中的「有」就是「有序(order)」,代表資訊組織化的狀態。「無」就是「無常(chaos)」,代表資訊散漫化的狀態。宇宙中任何的萬事萬物都是物質與能量的某種配置,任何物質與能量的配置方式即是資訊。就人類目前所知,宇宙中所有的資訊只有兩種基本型態:有序與無常(Kauffman, 1993; Cowan, et al., 1994)。因此,宇宙中任何的萬事萬物只要存在,必然是有序與無常的某種穩定組合。對於任何一種組合當下所呈現的狀態,人類都可以設法給它命名,也就是都可以想辦法用語言文字去描述它。一旦如此,萬事萬物的「名」就出現了。因此,老子所說的「名」,是泛指任何一個有序與無常的資訊組合狀態,或者是任何一個有序與無常及其組合的表現形式。故如果我們給「名」下一個定義,則「有序與無常的表現形式」非常適合。如果「名」是指「有序與無常的表現形式」,則「名」就是一種特定的「形式(form)」,或是西方哲學中所指的存在(being)。
另外,宇宙中的萬事萬物沒有不變的,而萬事萬物的任何變動必然牽涉到物質與能量的流變、轉化。然而,根據熱力學,質能是不滅的。因此,宇宙中萬事萬物的流變與轉化只是配置方式的變動。換句話說,變動的只是資訊。然而,資訊只要有變動,則一定是從有序到無常,或從無常到有序,二者必居其一,因為萬事萬物的變動必然是傾向越來越有組織,或越來越散漫。故萬事萬物的變動雖然表面上看千變萬化、無奇不有,歸根結底卻只是資訊之有序與無常之間的轉化而已。老子用「道」來指宇宙間所有有序與無常之間的轉化方式!有序如何轉化成為無常,無常如何轉化成為有序都是「道」。所以,我們可以為老子的「道」下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有序與無常的轉化方式」。故「道」是指一種「方式(way)」,或是西方哲學中所指的過程(becoming)。
這樣的看法與王弼相當一致。王弼注老子第一章說:「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王弼雖然沒有說明「道」是什麼、「名」是什麼,但顯然王弼認為「道」是指「事」而言,「名」是指「形」而言。「道」指何事?「道」指有序與無常的轉化方式。「名」指何形?「名」指有序與無常的表現形式。正因為如此,任何浮現出來的事與形,都不可能永恆。因此,永恆的常道必然不可道,即指不出任何事,故「常道無事」;永恆的常名必然也不可名,即造不出任何形,故「常名無形」。
現在,我們以水為例。相對於水,冰的結晶組織嚴密,故可以形成堅硬的固體。相對於冰,水分子的結構鬆散,無法形成固體。「水」與「冰」都是「名」之所指,都代表著水分子所含資訊的某種「有」、「無」表現形式。單以水與冰而言,水代表「無」,冰代表「有」,因為冰比水更「有序」,水比冰更「無常」。當冰化成水的時候,資訊組織化的程度下降,「有序」變少了,「無常」變多了,「有」「無」發生了轉化,儘管水分子本身並沒有任何改變。冰化成水呈現的就是一種「道」的運作。同理,水結成冰呈現的是另一種「道」的運作。雖然資訊組織化的程度提高了,資訊是從「無」流向「有」,但依然是一種「有」「無」的轉化,故還是一種「道」的運作。水與水蒸氣之間的變化也一樣。相對於水蒸氣而言,水代表「有」,水蒸氣代表「無」,因為水比水蒸氣更為組織化。水氣化成水蒸氣,或是水蒸氣凝結成水,所呈現的也都是「道」的運作,因為都是「有」「無」的轉化,只是轉化的方式不同而已。故不論是水結成冰、冰化成水、水化成水蒸氣等等各種變化都是「道」,而在所有萬事萬物變動背後所包含共通的資訊「有序」與「無常」之間的轉化方式則是「常道」!任何的變化方式只要具體呈現出來,如水結成冰,或冰化成水,就不是存在於所有變化方式背後共通的變化方式!所以老子才會說:「道可道,非常道」。因此,將本句中第二個「道」字解成「說」是錯的,它仍然是「道」。如果解成「說」,則「道可道,非常道」與「名可名,非常名」在意義上將有所重複,而且「道」與「名」的意義也會發生混淆。
如果「名」代表「有序與無常的表現形式」,則任何一個可以描述出來的表現形式都將只是某一個特定的形式,都可以用某個「名」來稱呼,如冰、水與汽。而萬事萬物背後所包含共通的資訊上「有序」、「無常」之一般化的表現形式則是「常名」,因此,「名可名,非常名」應解為:「任何有序與無常的表現形式只要具體表現出來,就不是存在於所有之『有』、『無』背後共通的表現形式!」所以,老子所說的「名」不應該理解為「名稱」或者「命名」(陳鼓應,2000;高明,1996;傅佩榮,2006;吳怡,2010),因為一旦如此,則不僅本章於多處出現的「名」將很難理解,全書各處出現的「名」也將無法得到一致流暢的解釋。「名」如果是指「名稱」或者「命名」,則「名可名,非常名」只能解為「可以命名的名,就不是常名」,或者「可以用名稱界定的,就不是恆久的名」。結合「道可道,非常道」之後,此兩句所討論的就只能是語言的侷限性了。這個觀點顯然還值得商榷,因為老子全書看不出有那裡像是在討論語言的侷限。此外,如果將「名」解為「名稱」或者「命名」,「名」指的將只是人類語言的產物,人類的語言中怎麼可能會有恆常不變的「名」呢?「常名」這個詞立刻陷入自我矛盾的窘境,就像「黑白的彩色電視機」一樣。何況,老子自己也說「道常無名」、「道恆無名」、「道隱無名」,既然如此,何以又說「常名」呢?豈不連老子自己
也自我矛盾?
任何資訊中的「有序」都從「無常」中凝聚而成(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 Kauffman, 1993)。「無」並不是一無所有,而是指資訊上的「無常」,即毫無秩序可言、毫無條理可講的物質與能量的配置方式。人類不但不能用語言文字來描述或稱呼,甚至也無法用有限的思維去理解。在這個宇宙中,如果存在任何一項事物,一出現就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秩序,那將是人類理性根本無法想像的事。或者,人類思維也必將繼續追問:那存在的秩序又是從何而來?因此,以人類有限的思維能力,只能沒有選擇的接受:「無,名天地之始」。也就是說,宇宙間一切的有序都只能來自無常。
宇宙中任何的事物之所以能夠存在,必然是因為它擁有某種秩序。如果一項事物完全沒有任何的秩序,則它只能是一種「無」,就不會是所謂的事物。故所有的事物都只能是「有」。萬事萬物的差異在於其中「有」的表現形式不同,也就是其中所包含的秩序各不相同。因此,宇宙中所有的萬事萬物必然是各種不同形式之「有序」的呈現,這就是「有,名萬物之母」。
接下來,「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是指面對「常有」與「常無」應該觀察的重點,觀察到重點才容易理解老子的思想。「常無」是指恆常不變的「無」,一種存在於天地萬物之內共通的無常狀態,並不是指某一種特定的「無」。例如,水對冰而言是一種「無」,水對水蒸氣而言卻是一種「有」,故水中的「無」即不是一種「常無」。「常無」應理解為天地萬物中資訊上共通的散漫狀態,如相對於冰之水的狀態,或相對於水之水蒸氣「常有」是指恆常不變的有,一種存在於天地萬物之內共通的有序狀態,並非指某一種特定的「有」。例如,水對水蒸氣而言是一種「有」,水對冰而言則是一種「無」,故水中的「有」即不是一種「常有」。「常有」也應理解為天地萬物中資訊上共通的有序狀態,如相對於水之冰的狀態,相對於水蒸氣之水的狀態等等。面對常有,老子告訴我們要觀察有序所帶來之各式各樣之組織上的形式,因為「有」包含了無窮無盡、千變萬化的「有序」。「徼」是邊際之意,引申為形式、形狀,因為任何的形狀都有邊際。
最後,老子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主要是在說明一切的萬事萬物都來自「有」與「無」兩者之間的循環轉化。「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中的「兩者」是指「有」與「無」,「有」與「無」出自同一個源頭,卻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因為只要有形式即可以用「名」來稱呼,故曰:「同出而異名」。「玄」是一個象形字,形狀類似一個環節接一個環節:「」(南懷瑾,1992),有一環扣一環、循環不已之意,可以解為「旋」。「有」「無」既然是「同出」,就表示有無之間的轉化是循環的,也就是「玄」,因為只有循環的想法可以讓我們理解「同出」的意義,故曰:「同謂之玄」。牟宗三也認為:「圓周之轉就是玄」,以及「玄是個圓圈」(牟宗三,1983),因為只有接受玄就是循環,才能真正理解有無同出的道理。此外,只要「有」、「無」之間存在任何的落差,轉化運作就會繼續循環不已。根據熱力學,宇宙中任何一個地方的「有」「無」都不可能達到完美的平衡而使「道」的運作停下來,除非處於絕對零度。故「有」、「無」之間的循環轉化會不斷發生,此即的狀態等等。面對常無,老子告訴我們要觀察無序所帶來之千變萬化的奧妙,因為「無」可以產生無窮無盡、千變萬化的「有」。老子所謂的:「玄之又玄」。一旦「有」「無」的轉化循環持續發生,就會形成各式各樣的「有」與「無」及其間的組合。於是,各種不可思議、奇妙異常的萬事萬物就會源源不絕的出現,這就是所謂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傳統上一般均將「玄」理解為幽昧深遠,或神秘難解、高深莫測、神奇奧妙等,或甚至文字無法形容之意,還進一步被引申為赤黑色(陳鼓應,2000;吳怡,2010)。當然,這些都是誤解,因為如果這些解釋正確,則「同謂之玄」將莫名其妙。當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時候,「玄」與「妙」很自然的連在一起而成為「玄妙」,代表一種無法理解的奧妙,於是「玄」開始擁有幽暗難解之意。其實,老子「玄妙」的本意顯然是指往復循環所產生的各種奧妙,而不是在說這些奧妙幽昧難解。只是因為這些奧妙確實幽昧難解,造成後人誤以為那就是老子的本意。不過,由於這個誤解已經由來久矣,早已積非成是而為大家所沿用。
後論
老子在第一章裡開宗明義就先提出道、名、有、無四大範疇,作為《道德經》的起點。對於「道」與「名」,老子只說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並沒有解釋「道」是什麼與「名」是什麼。對於「有」與「無」,老子不但解釋:「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且還進一步描述「有」與「無」如何運作,以及該如何觀察。在比例上,本章的重點應該在講「有」與「無」。不過,「有」、「無」的觀念太深奧,老子的闡述遂讓人難以理解,甚至造成誤解。當然,造成誤解的不只「有」、「無」而已,「道」、「名」也一樣造成誤解。不過,因為「道」、「名」都是針對「有」、「無」而發,如果能夠清楚理解「有」與「無」,則「道」與「名」將不易誤解。反之,一旦誤解「有」、「無」,則不可能正確理解「道」、「名」。
從資訊的組織化與散漫化角度來解釋「有」、「無」確實是現代科學的觀點。老子當然不可能懂現代科學,故老子不可能擁有「有序」與「無常」的科學概念,但這卻並不表示老子就無法建構「有」、「無」的想法。更何況老子所觀察的大自然跟現代人所看到的本是同一個,所描述的對象也相同,描述很接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古代中原人對於水在冬天結成冰的現象必然習以為常,對於水燒開之後化成水汽的現象想必也司空見慣。當老子看到冰在春天又溶化回完全一模一樣的水,或是水汽遇冷同樣凝結回完全一模一樣的水的時候,必然會去思考到底是什麼變了,以及又是什麼東西回來了。我國古人基於漢字的影響,非常善於觀察各種現象的變化與其間的關聯,易、八卦、五行、中醫都是典型的例子。當水結成冰的時候,水跟冰之間有何不同?當冰化成水的時候,冰跟水之間又發生什麼事?在冰、水、水汽之間,顯然作為水的本身並沒有不同。因此,水結成冰之後,除了水本身,冰比水多了什麼東西?是不是多了形狀?多了可描述的邊界?水化成水汽之後,除了水本身,水汽比水又少了什麼東西?是不是少了形狀?少了可描述的邊界?反過來說,基於同樣的道理,冰化成水的時候,除了水本身,什麼東西不見了?是不是剛才多出來的邊界不見了?水汽凝結成水之後,除了水本身,什麼東西回來了?是不是剛才失去的邊界回來了?老子既然要我們透過「觀其妙」去理解「常無」,以及透過「觀其徼」理解「常有」,說明了在老子心中,難以捉摸
就是「無」的本質,形式邊界就是「有」的呈現。當冰化成水的時候,水比冰更難捉摸;當水化成水汽後,水汽同樣比水更難捉摸。另外,水結成冰之後,冰比水多了可觀察的邊界;水汽凝結成水,水比水汽也多了可觀察的邊界。因此,當老子以非常接近現代科學之有序與無常概念的「有」與「無」,來表達在冰、水、水汽變化之間所出現與消失的東西時,也就十分合理而且貼切。
只是老子雖觀察到萬事萬物之間「有」「無」的交替變化,卻無法確定誰先誰後,只好推論「有」與「無」同出。可是「有」與「無」卻又明顯不同,只好又說「而異名」。而且,在老子眼裡,不論是「有」或「無」,都無法離開對方而單獨存在,就像所有生命有生必有死一般,所呈現的是一個往復循環的過程,故老子又說「同謂之玄」。接著老子又發現大自然裡似這般往復的循環過程無休無止,而用「玄之又玄」來形容。所有萬事萬物的奇妙變化都從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地冒出來,就像是一個奇妙之門被打開了一般,老子於是把這個過程形容為:「眾妙之門」。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景注老子:老子思想的體系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哲學79折起 |
$ 340 |
社會人文 |
$ 360 |
社會人文 |
$ 380 |
大學出版品 |
$ 380 |
哲學 |
$ 380 |
中文書 |
$ 380 |
中國哲學 |
$ 380 |
大學出版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景注老子:老子思想的體系化
老子《道德經》是一部奇書,古今中外註解老子的書已經數不勝數。但是,關於老子到底在說什麼,至今沒有一個定論;雖然存在大致的共識,但詳細的內容依然非常分歧。即使連老子思想的核心——道,竟然都需要建立六個意義。既然老子談論的道與大自然關係密切,而西方科學對於大自然的了解早已遠遠超過老子時代,故本書基於西方科學的最新發展,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建立一個滿足唯一性要求的道,與符合現代知識的全新詮釋,來解釋《道德經》中的每一章,再進而將各篇章按條理重新整理成《道德新經》,以追求將老子思想體系化,為理解老子思想提供學界與社會各界一個全盤性的參考,期望能夠發揮承先啟後的功用。
作者簡介:
景鴻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力學博士
專長及研究領域
以飛航安全與人為因素為起點,長期關注中西思維方式的相關議題,以及對文化與科技的影響。
著有
《實驗火箭原理設計與製作》
《龍在座艙》
《孩子謝謝你》
《西方哲學批判》
《景注公孫龍與名家》
The Dragon in the Cockpit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道可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語譯
任何「有」、「無」之間的轉化方式只要呈現出某種方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轉化方式。任何「有」、「無」的表現形式只要表現出某種形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表現形式。
「無」可以稱為天地開始的起點,「有」則可以稱為萬物出現的源頭。所以,面對最根本恆常不變的「無」,我們應該觀察其如何轉化的各種奧妙,面...
道可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語譯
任何「有」、「無」之間的轉化方式只要呈現出某種方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轉化方式。任何「有」、「無」的表現形式只要表現出某種形式,就不是最根本恆常不變的「有」、「無」表現形式。
「無」可以稱為天地開始的起點,「有」則可以稱為萬物出現的源頭。所以,面對最根本恆常不變的「無」,我們應該觀察其如何轉化的各種奧妙,面...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序
《老子》一書充滿智慧,做為僅次於聖經、全球被翻譯第二多的書籍,確實當之無愧。曾經有人統計過,古今中外,註解老子的版本據說有上千種,單單世界各國的翻譯本就有兩百多種。不僅如此,即便已經有如此多的版本,新的註解還是源源不斷湧出,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然而,在數不勝數的版本中,針對老子的思想言論,固然存在約略一致的解讀,但更多的是各說各話,以致於有學者以「鏡子」來形容《道德經》,因為註解的人從《道德經》中看到了自己。換句話說,註解的人透過《道德經》表達的其實是自己的看法。至於是不是老子的本意,...
《老子》一書充滿智慧,做為僅次於聖經、全球被翻譯第二多的書籍,確實當之無愧。曾經有人統計過,古今中外,註解老子的版本據說有上千種,單單世界各國的翻譯本就有兩百多種。不僅如此,即便已經有如此多的版本,新的註解還是源源不斷湧出,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然而,在數不勝數的版本中,針對老子的思想言論,固然存在約略一致的解讀,但更多的是各說各話,以致於有學者以「鏡子」來形容《道德經》,因為註解的人從《道德經》中看到了自己。換句話說,註解的人透過《道德經》表達的其實是自己的看法。至於是不是老子的本意,...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始 章 老子在說什麼
第一章 道可道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第三章 不尚賢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
第五章 天地不仁
第六章 谷神不死
第七章 天長地久
第八章 上善若水
第九章 持而盈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
第十六章 致虛極
第十七章 太上
第十八章 大道廢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始 章 老子在說什麼
第一章 道可道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第三章 不尚賢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
第五章 天地不仁
第六章 谷神不死
第七章 天長地久
第八章 上善若水
第九章 持而盈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
第十六章 致虛極
第十七章 太上
第十八章 大道廢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景鴻鑫
- 出版社: 成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7-09 ISBN/ISSN:97898656353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50mm \ 高:21mm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