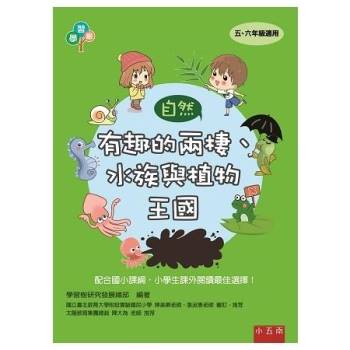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唐詩成法》的特點與點校說明
屈復(1668-1745),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十九歲應童子試得第一名,此後不再應科舉考試,乾隆元年(1736)亦不應博學鴻詞科之徵,其〈留別王介山使君〉詩自言:「七十有七齡,半百在行旅。」(《弱水集》卷三)平生足跡半天下,先後遊歷齊、魯、燕、趙、吳、越、閩、粵等地,晚年以詩教授於京師。
屈復存世著作不多,目前可見的是其詩集《弱水集》,詩歌評選則有《楚辭新注》8卷、《杜工部詩評》18卷、《玉溪生詩意》8卷,以及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詩成法》12卷。據本書卷前〈凡例〉後附識本書出版始末,屈復早於雍正元年(1723)應友人岳禮(號蕉園,-1666-)之邀,開始著手自《全唐詩》中選錄唐詩,歷時兩年完成。但選詩完成後,屈復「貧不能梓」,因缺乏經費以致無法即時出版。乾隆八年四月,屈復偶遇江都人吳家龍(?-?),兩人談詩甚洽,待吳家龍「請其著作」時,屈復原本只以「所注《離騷經》、所著《弱水集》見贈」,吳家龍隨後表明:「初學之士作詩,多不知法,蓋迷津不渡,終難登彼岸,先生將何以教後人耶?」屈復這才出示《唐詩成法》稿本。吳家龍閱後自覺受益匪淺,遂於當年八月將書稿付梓。推算《唐詩成法》由雍正元年開始選錄點評,至乾隆八年正式刻板印刷,前後歷經二十年。筆者點校參閱的版本,是目前館藏於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江都吳家龍刻本、弱水草堂板的《唐詩成法》。書中因有部分缺頁,遂又補以北京圖書館古籍庫的館藏本。
屈復在卷前〈凡例〉自言本書是「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旨在指點初學詩者習詩入門之用。今人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中,也稱揚本書:「雖不是一本著名的唐詩選本,但在評詩方法上卻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特點。」本書所以能獨樹一幟、裨益初學,得力於書中以下幾項特點:
其一,僅選唐人五、七言律詩
初學詩者應由何種詩體入門?一直是歷來爭論的話題。就詩歌格律而言,律詩四聯八句,不僅須符合平仄黏對的條件,並有偶數句平聲一韻到底的押韻限制,中間兩聯更有嚴格的詞性對仗要求。相形之下,同為近體詩的絕句,並不講求對仗,加以絕句僅有四句,章法起結變化也不如律詩繁複多樣。至於偏重鋪排敘事的古體詩,在句式、字數與押韻各方面,都不像律詩般讓初學者有「律」可循,學詩若由古體入手,終究要另外學習近體詩的格律。因此,以律詩作為初學詩者的入門詩體,在嫻熟近體詩的各種格律後,不僅可以將單首律詩以連章方式(如杜甫〈秋興〉八首)擴大題材或內容,使之具有古體的長篇鋪排效果;也能在精省篇幅後變化為絕句。屈復《唐詩成法》選擇以句數長短得宜、格律嚴謹、變化繁複的律詩,作為學詩者的初階、基礎,實有其獨到的見地。
詩體因素之外,清廷加考試律的時代背景,也與本書的刊刻、出版密切相關。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曾研議於科舉二場,加試五言六韻排律一首。雖然這項試詩政策,直到乾隆廿二年(1757)才正式施行,但已在康熙年間逐漸發酵,促使人們開始重視律詩並研習試律。印證寫於康熙五十四年的黃六鴻(1630-1717,號思齋)〈唐詩荃蹄集序〉所言:「一時學者,聞風鼓舞,朝夕吟詠,罔間遐邇。」而屈復在《唐詩成法》卷前〈凡例〉中,也有「每見舉業家之詩,多有場屋文字氣」之言,據此推論本書所以單選律詩,或有因應清代科舉試律的考量。筆者在檢校古籍時偶然發現,乾隆廿一年(1756)蘇州人顧安(字小謝,?-?)評選、乾隆廿七年(1762)書商何文煥(1732-1808)增評重刻的《唐律消夏錄》,也是一部因應試律政策,僅選唐人五律的詩歌選本,書中評語更多有襲自屈復《唐詩成法》者。不僅印證了屈復評詩,確有其獨到精要處,故而吸引時人抄襲、化用,亦可見清廷試律政策,對詩歌選評與出版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其二,詩句旁加圈點
詩句是否旁加圈點,可謂見仁見智。有主張讓讀者自行領悟,故不著圈點以免影響閱讀;亦有主張以圈點畫龍點睛,提示讀者留意詩人用心或詩作佳妙處。就初學詩者而言,詩句旁加圈點,確實要比不著圈點,更具有引導、啟迪作用。《唐詩成法》中,屈復以密集單圈(。)標示詩中佳句,以雙圈(。。)標示詩中關鍵字詞。讀者參照詩評內容,不難尋得詩眼或佳句所在。惟筆者點校時發現,雙圈符號與密集單圈易混淆不清,遂改以實心「‧」取代。
其三,詩作首首附有詩評
屈復自言《唐詩成法》一書,是由《全唐詩》中歷時兩年選錄而成,選詩之不易,可見一斑;評詩則需於選詩之外,耗費心神對詩作進行詮解。偶一為之或寥寥數語帶過,尚非難事,但若首首皆附詩評,非傾注大量時間心力不可。因而一般詩歌選本,或者有選無評,或者僅有「佳妙」、「好」之類的簡短批語。初學者不僅難以理解詩作佳妙的關鍵,更難以推測詩作入選的考量因素。屈復《唐詩成法》則不然,不僅每首詩都附有詩評,詩評重點也不在於詩中名詞釋義或典故出處,而是其熟讀深思詩作後的體悟或批評。每首詩評長短不一,短篇詩評多僅說明詩中上下承接照應關係,或者結合詩句旁的圈點,指出詩作精鍊處或不足處。至於長篇詩評,或者陳說詩作結構應如何調整安排,更加得當;或者評詩而兼及詩人的創作成就,或者論及「初盛中晚」四唐詩之高下,對於研究唐詩相關議題,或是理解屈復選詩理念,都有莫大的助益。
由於屈復終身不仕,以布衣終老,詩評中遂常流露其客遊淪落之歎,對孤寒不遇之詩,更是深有所感,例如:
窮途惟賴友生,忽而遠去,如嬰兒之失慈母。後四真情實語,氣味悲涼,聲淚俱下。吾客遊五十年,從無張卿其人者,竊為顧君慶也。(卷九,評顧況〈送大理張卿〉)
一碧潯,二宴上。三收上,四起下。五六自比孤弱,知己難得。七八世無知己,故欲遠隱,寫「懷」字微妙。笙歌鼎沸中,每吟此詩,淒然欲絕。(卷十二,評曹鄴 〈碧潯宴上有懷知己〉)
通篇言生長孤寒,遭時搖落。扶持者少,凌轢者多。忽念天下梁棟之才,老死於深山窮谷者,不可勝道,聊以自慰耳。(卷十二,評吳融〈紅樹〉)
天下高人,多在草野,名利多忙,如何知得?所以興歎於寒地之才,貧家之女也。不競仕路,細心憐才,舉世惟我一人。結得身分高甚。(卷十,白居易〈晚桃花〉)
以上數則詩評,既體現了屈復對所選詩作的見解,也是屈復流落不偶的內在情志折射,為研究屈復的生平或詩學觀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其四,以「詩法」作為評詩、改詩的準則
坊間所見的詩歌選本,多就詩作佳妙處而發,罕有如屈復《唐詩成法》般,以「詩法」作為評論詩作佳妙或疵謬的準則,有時甚至還提出「如何修改」的具體建議。
先就合乎詩法的正面詩例來看,如收錄於卷五晚唐于武陵〈贈賣松人〉:
原詩: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劚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
詩評:一二虛寫賣松人,三四實承一二,五六寫松之清高,逼出結句俗人不買,法好!賣松人有何可贈?寄托之旨,言外自見,雖淺近,取其有意。
詩作表面上寫「賣松人」入長安城販售寒澗孤松,卻因俗人賞重桃李而不受青睞。屈復說解本詩,聚焦於詩作各句的旨趣與彼此承接照應的關係,本詩因八句上下連貫,屈復故而予以「法好」、「有意」的肯定。
至於「不講法」的負面詩例,如卷五之周朴〈董嶺水〉:
原詩: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
詩評:三四誠佳,但山色、月光全無關合,乃湊字耳,所以不為合作。中晚不講法,多如此。
第三聯的「山色」、「月光」,屈復認為不過是為了合乎對仗而勉強湊字,兩句上下並無關合,屈復是以有「不講法」的負評。
在批評詩作「不講法」之餘,屈復還進一步對這類詩作提出了「改字」或「改句」的具體建議。
改字者如卷一收錄的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歎之〉,詩中頷聯以「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概括孔子生不逢時的遭遇。但在屈復看來,孔子既貴為聖人,自不應如凡夫俗子般嗟怨命運,且由唐玄宗對孔子祭祀之尊隆,可見孔子所傳之道,在後世確實是未「窮」的。遂主張將二句改為「歎鳳身雖否,傷麟道未窮」,以「雖」、「未」兩虛字,扭轉原詩的負面語意,也更能符合孔子的聖人高大形象。同為卷一的初唐陳子昂〈春夜別友人〉詩,五六句「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屈復以「明月」、「長河」為秋夜景色,認為改用「柳月」、「華星」,更能切合詩題的春夜時令。
改句者如卷二之綦毋潛〈送章彝下第〉,詩中三、四兩句「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皆明寫下第。屈復認為,「三明說下第,四當含蓄;四明說則三當含蓄」,亦即上下兩句宜有區隔,故而建議第三句改為「有渡春波淺」,使兩句的句意更有層次對比。又如卷五選錄晚唐溫庭筠〈商山早行〉詩,屈復認為頷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與頸聯「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既重複書寫詩題「早」字景色,也與末聯的思鄉之情全無關照,是以主張「五六若寫故鄉景,結句再明白,則合作矣。」亦即五、六句宜由眼前所見山路、驛牆,改成記憶中的故鄉場景,方能與第二句的「悲故鄉」與第七句的「杜陵夢」前後呼應。
據清人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卷四所載:「屈翁傲岸,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牀下。專改削少陵,訾陵太白,以自誇身分。」袁枚將屈復對李、杜詩的「改削」、「訾陵」,與屈復的「傲岸」個性及「自誇身分」的行徑相聯繫,難免讓人對屈復產生負面觀感。但對照《唐詩成法》的詩評內容,屈復除了直指前人詩作缺失並提出修改建議外,也往往不憚詞費,多方提點唐人詩作佳妙處。此舉猶如教學現場重現,教師除了在課堂分享佳作,也針對表現不佳者予以修正、提點,讓學生得以透過正、反詩例,趨長避短,從而嫻熟遣詞用字與章法布局的技巧。
其五,說詩僅指點要旨,不拘文取義
屈復評論詩作時,常提醒讀者「不熟讀深思,不能領會」(卷六,陶峴〈西塞山下迴舟作〉)、「細玩方知曲折深隱,用筆用意,皆不令淺人易窺也」(卷四,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一字一淚,而味在字句之外」(卷四,杜甫〈天末懷李白〉),主張詩歌要細心熟讀,才能體會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然而,說詩者對詩句的獨得之見,有時難免拘文取義、引申過度。如清初金聖歎(1608-1661)《杜詩解》卷二說解杜甫〈江村〉之「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二句云:「正極寫世法嶮巇,不可一朝居也。言莫親於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於稚子,而拗直作曲,詭詐萬端。」將原詩的「長夏江村事事幽」的清幽閒適,曲解成世法嶮巇、人心詭詐。而歷來詩家在「杜甫每飯不忘君」的說詩前提下,也往往將杜詩詮釋成首首皆詩史、字字皆忠愛。可見說詩者在「發明詩中奧義」與「說詩穿鑿比附」之間,難免顧此失彼,不易取得平衡。
難能可貴的是,屈復在詩評中,不僅展現其「以法論詩」的獨到之處,也能以客觀的態度說解詩中寓意,而不過度引申。如卷四選錄杜甫詠物五律〈天河〉、〈初月〉、〈促織〉、〈除架〉、〈銅瓶〉等詩,屈復僅概略指點詩作要旨,讓讀者自行領會詩句的言外之意。以〈初月〉詩為例,首聯「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歷來說詩者,或者以之比附杜甫方任職拾遺、旋即罷去的處境;或者謂杜甫諷刺肅宗新皇即位未穩。屈復則以謹慎通達的態度說解道:「此等詩若無寄托,則不作;若必求事以實之,則鑿矣。」認為這類詠物詩作,杜甫必然寓有深意,但寓意為何?則未必要以具體的人事時地,一一比附穿鑿。卷十一說解李商隱的〈錦瑟〉、〈無題〉詩,也主張:「皆是寄托,不必認真」、「其意或在君臣朋友間,不可知」,並未刻意指實詩句的內涵,為讀者保留更多的閱讀與解釋空間,體現了屈復說詩的通達性與客觀性。
透過以上歸納屈復《唐詩成法》在選詩、圈點與評詩上的特點,可見本書確實無愧於「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自我定位,對於引導初學詩者掌握近體詩的字法、句法、章法結構,也的確大有裨益。無怪乎對學詩深感興趣,卻苦於不工詩律的江都人吳家龍,閱讀本書後如獲至寶,立即安排出版事宜,以公諸天下。
據吳家龍序文所言,屈復於乾隆八年四月與吳家龍會晤,出示《唐詩成法》底稿,爾後吳家龍命其兩孫細為參校,於當年九月旋即出版。或許正因出版時間匆促,校對難免疏漏。筆者點校《唐詩成法》時,除了將原書另加標點,也將原本易與單圈「。」混淆的雙圈「。。」符號,改以實心「‧」標示,方便讀者閱讀。另針對本書進行以下校對或補充工作:
其一,訂正錯別字與標明疑義處。書中錯字於字旁以括號補以正字,並略做縮小。如卷前〈凡例〉第一則之「關石和鈞」,原書「鈞」字誤植為「釣」,內文修正為「關石和釣(鈞)」。又如開元名相「張說」,錯植為「張悅」,內文修正為「張悅(說)」;卷五姚合〈武功縣中作〉詩評之「自愧素粲」,修訂為「自愧素粲(餐)」。而詩題有誤者如杜甫〈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人(夫)〉,崔顥〈行經華陽(陰)〉,蘇頲〈奉和聖製登麗(驪)山高鼎寓目應制〉,丁仙芝〈渡楊(揚)子江〉,祖詠〈泊楊(揚)子津〉等。此外,詩作有疑義者,如卷二邱為〈留別王維〉詩,《全唐詩》中另有王維〈留別丘為〉,兩詩內容是一樣的;卷五周朴〈春宮怨〉,《全唐詩》標示的作者為杜荀鶴;卷八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覲〉,清人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注》亦作「省覲」,但《全唐詩》則改作「覲省」。以上錯別字之訂正或疑義處,均在「校注」欄中予以補充、注明。
其二,統一正、異體字。本書乃屈復於乾隆八年四月偶遇江都吳家龍,同年九月即刊刻印行。在校閱匆促的情況下,書中遂屢見異體字並行的情形。如卷一杜審言〈夏日過鄭七山齋〉的詩評,先後出現「於飲一夜後」及「于飲一日後」的異體字;卷三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也有詩為「雁」字而詩評改作「鴈」字者;又如卷七張謂〈西亭子言懷〉,詩作與詩評也出現「閑/閒」的用字差異。其他如「遶/繞」、「隣/鄰」、「谿/溪」、「挂/掛」、「檐/簷」、「床/牀」、「翫/玩」等異體字,也屢見於書中。為求體例統一,筆者在校注時,遂將書中的異體字(如「筭」字),一律改為較常見的正體字(如「算」字)。
其三,補充詩人之字號、籍貫。由於屈復說詩時,慣以古人字號、籍貫或是官職代稱詩人,如卷一評張九齡〈秋夕望月〉所謂:「射洪〈月夜有懷〉,必簡〈和康五望月有懷〉,與曲江〈望月懷遠〉,俱從彼處說起。」句中「射洪」指陳子昂,「必簡」乃杜審言,「曲江」為張九齡。詩評中所涉及的古人字號、籍貫代稱,均於「校注」中補充說明。
其四,補充詩評典故出處或概念說解。屈復說詩,對於某些典故或詩句,往往信手拈來,不著出處。如卷二評王維〈山居秋暝〉詩,引「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說解三四句,又引「花落林愈靜,鳥鳴山更幽」說解五六句。前一則詩句,出自北宋邵雍(1012-1077)〈清夜吟〉;後一則詩句,出自南朝梁詩人王籍(-540-)〈入若耶溪〉,惟原句為「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疑是屈復引用有誤所致。再者,屈復說詩時所涉及的批評用語,諸如「點金成鐵」、「合掌」、「草蛇灰線」之類,或是偶有語意難明者,如卷八評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云:「冠帽犯」,乍看或以為文句有缺漏,實乃屈復謂詩中冠、帽二字,犯有語意重複之病。又如卷十二評秦韜玉〈貧女〉詩,屈復謂詩中「六句皆平頭,是一病。」惟檢視本詩各句前兩字,都未出現聲母或聲調相同的詩病,細讀後發現,本詩除首句「蓬門」與末句之「為他人」,其餘第二句至第七句的前兩字,如「擬託」、「誰愛」、「共憐」、「敢將」、「不把」、「苦恨」,第二字皆為動詞,句型也都是「2-2-3」句式,有節奏重複、句式呆板之失,此應是其所謂的「平頭」。以上涉及古人代稱、引用出處及語意難明處,為方便當代讀者理解閱讀,故於詩評之後,另加「校注」處理。
筆者曾先後赴上海與北京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於善本古籍庫中得見本書。研閱後,既深感屈復「以法論詩」之見識獨到;也敬服其「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良苦用心。但移地研究時間畢竟有限,只能概略整理選詩目錄與詩評要點,無法梳理全貌。今年因緣巧合取得本書完整內容,檢索後發現,學界目前尚未有本書之點校本問世,也未有針對本書所作的專題研究,與屈復詩學的相關研究更是屈指可數,殊為可惜。遂利用今年上半年休假研究之暇,對本書進行點校工作,以供學界日後進行教學、研究之用。值此點校完結之際,迴念清人吳家龍閱讀《唐詩成法》初稿後,「亟付棗梨,公諸天下」之情切,竟有異代相通之感。期盼能有機會,將本書介紹給有志學習或研究古典詩學的同好。
本書之點校完成,除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提點、建議,也得力於成大中文所黃嘉欣、鄭宜娟、黃絹文、郭欣同學的協助,並有賴成大中文所武玥同學於北京圖書館補全缺頁內容,謹此一併敬申謝忱。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5 |
中文書 |
$ 355 |
教育學習 |
$ 356 |
詩 |
$ 356 |
小說/文學 |
$ 383 |
文學作品 |
$ 428 |
大學出版品 |
$ 428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
屈復(1668-1745)《唐詩成法》,成書於清乾隆八年(1743),是一部單選五、七言律詩的唐詩選評本。基於「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著述理念,書中選錄的詩作,首首皆有圈點與詩評,並由「詩法」的角度,針對詩作的用字、用詞與章法結構,提出具體的品評意見與修改建議,對初學詩者掌握律詩寫作技巧,大有裨益。此外,書中的詩評內容,也蘊含屈復對唐代詩家的評論,及其對四唐詩作的高下分判,亦可作為研究唐人律詩相關議題的參考文本。
原書因流傳有限,僅館藏於少數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點校本除了將詩評內容加上標點,也訂正書中的錯別字與異體字,並補充詩評所提及的詩人字號、籍貫,以及相關典故出處或概念說解,期能將本書分享給有心學習律詩或研究古典詩學的讀者。
作者簡介:
點校
陳美朱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專長領域為古典詩學之杜詩學、唐詩選本與明清詩話專題研究。已發表專著有:《明末清初詩詞正變觀研究——以二陳、王、朱對對象之考察》、《清初杜詩詩意闡釋研究》、《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與《唐宋詞選讀》等書。
作者序
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唐詩成法》的特點與點校說明
屈復(1668-1745),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十九歲應童子試得第一名,此後不再應科舉考試,乾隆元年(1736)亦不應博學鴻詞科之徵,其〈留別王介山使君〉詩自言:「七十有七齡,半百在行旅。」(《弱水集》卷三)平生足跡半天下,先後遊歷齊、魯、燕、趙、吳、越、閩、粵等地,晚年以詩教授於京師。
屈復存世著作不多,目前可見的是其詩集《弱水集》,詩歌評選則有《楚辭新注》8卷、《杜工部詩評》18卷、《玉溪生詩意》8卷,以及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詩成...
屈復(1668-1745),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十九歲應童子試得第一名,此後不再應科舉考試,乾隆元年(1736)亦不應博學鴻詞科之徵,其〈留別王介山使君〉詩自言:「七十有七齡,半百在行旅。」(《弱水集》卷三)平生足跡半天下,先後遊歷齊、魯、燕、趙、吳、越、閩、粵等地,晚年以詩教授於京師。
屈復存世著作不多,目前可見的是其詩集《弱水集》,詩歌評選則有《楚辭新注》8卷、《杜工部詩評》18卷、《玉溪生詩意》8卷,以及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詩成...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