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作!
萊辛巴赫瀑布連綿不絕的激流飛奔而下,傾瀉進萬丈深淵,浪花拍擊著黑色的岩石,發出經久不息的隆隆響聲。
莫里亞蒂教授一心想要將福爾摩斯置於死地,精心策劃的陰謀將福爾摩斯逼上了絕路……
莫里亞蒂魔高一尺,還是福爾摩斯道高一丈?
最後的決戰,正義與邪惡的對決,一切都將在萊辛巴赫瀑布的山巔做個了斷!
| 購物比價 | 找書網 | 找車網 |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最後一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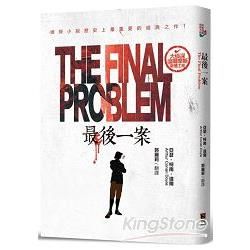 |
最後一案 出版社: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推理/犯罪小說 |
$ 220 |
推理小說 |
$ 220 |
推理小說 |
$ 225 |
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