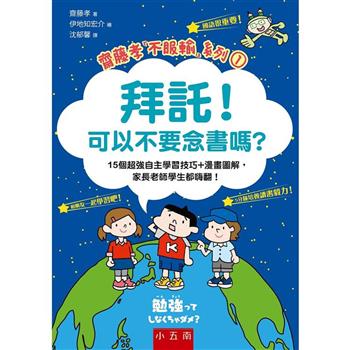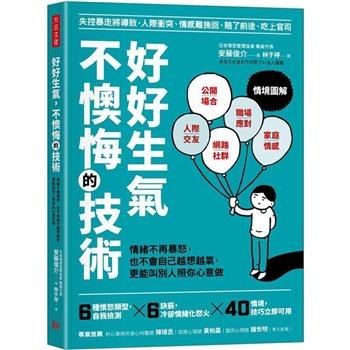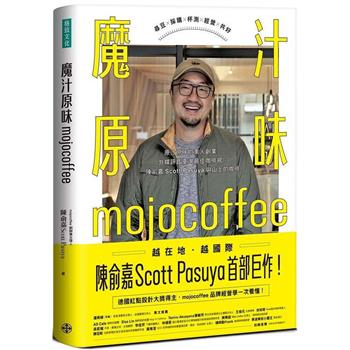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作!
蠻橫凶殘的老彼得船長死在了他的海邊小屋中!
案發現場慘不忍睹,地板上和牆壁上佈滿了血跡,看起來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死者去世前十分痛苦,他的整張臉扭曲變形,下巴上花白的鬍子也因為極度的痛苦而向上翹起……
一支捕魚用的鋼叉深深地穿透了他的胸膛,然後又插進了他身後的木牆中……
負責偵辦此案的霍普金警長一籌莫展,只好請出了我們的大偵探福爾摩斯……
柯南道爾如是說:
對於一個算正的推理家而言,如果有人指給他事件的一個方面,他不僅能推斷出這個事件的各個方面,而且能夠推斷出由此將會產生的一系列後果。正如動物學家居維葉經過仔細思考就能根據一塊骨頭準確地描繪出一頭完整的動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