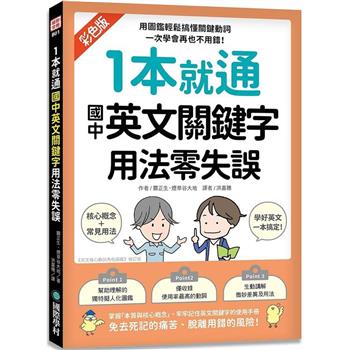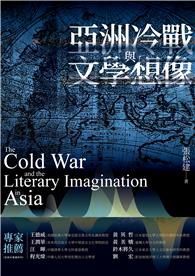「愈是鬱悶沉重的人生,愈要恣意瀟灑度過!」
◎日本暢銷1,300,000冊的新感覺娛樂系列小說!
改編電影奪下「日本電影旬報獎」& 獲「日本金像獎」7項入圍肯定
由《清須會議》大泉洋×《多田便利屋》松田龍平 魅力搭檔主演
老大不小的「我」自稱萬事代辦屋,其實是以賭博維生。
平日跟狐群狗黨廝混,晚上就找女人睡覺,閒閒才窩在酒吧等生意上門。
說我是自甘墮落也好,渾身散發垃圾氣息也好,總之生活不就是這樣?
反正經歷慘痛的教訓,也只是痛而已。就算身體受傷,也只是受傷而已。誰都無法傷害我。
【故事簡介】
在札幌紅燈區薄野經營萬事代辦屋的「我」,今晚一如往常推開酒吧的門,沒想到早有一個傻小子等著我。他自稱是我的學弟,說同居女友麗子四天不見蹤影,希望我能幫忙找找。
我隨口答應,照樣過著跟男人打屁抬槓、跟女人調情溫存、用拳頭與不良分子溝通、喝酒喝到茫的生活。不過,我還是抽空調查麗子住處,發現她的父親會寫信噓寒問暖,笨拙地叮囑「要幸福喔」;打電話回她老家,接聽的善良歐巴桑談起女兒就難掩懷念與喜悅。可是,她的帳戶卻有多筆來源不明的匯款,顯然是在兼差賣春。忽然,我想起數天前「快活城堡」愛情賓館發生的離奇命案,該不會兩者有所關聯……
不知不覺中,我對這樁委託愈來愈認真,是想讓傻學弟安心嗎?為了素未謀面的麗子的幸福嗎?不管是哪種理由,都有夠矯情,但我已無法袖手旁觀。
作者簡介:
東直己
1956年出生札幌,擔任過家庭老師、土木作業員、卡拉ok店外勤、雜誌編輯等等,1991年以《偵探在酒吧》出道,2001年以《殘光》獲第54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作品達十餘冊,「泡BAR偵探」系列為他知名系列作品,廣受好評,2011年改編成電影。
相關著作
《泡BAR偵探:打給那位偵探的電話》
譯者簡介:
鄭舜瓏
輔仁大學日文系、台灣大學日文所畢。曾擔任台灣戲曲學院日文導覽人員、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日文版權業務。現專事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家醺然推薦】
「光是閱讀本作,不喝酒也能享受到微醺的暢快感。假使能配酒,想必能醉得更痛快。
不如讀兩遍吧。一遍清醒時讀,一遍拿著酒杯讀。」
──推理小說評論家‧村上貴史
媒體推薦:
【讀者暢快推薦】
主角「我」稱不上是偵探,也不是善良市民,只是做為萬事代辦屋(不良成分居多)奮力謀生。跟「我」一起悲傷、焦慮、憤怒、大笑、忍受嘲諷與屈辱,最後卻不知怎麼有種「啊,真是太好了」, 眼淚快跑出來的感覺。──日本讀者 mocha
小說中你來我往、機鋒處處的對話真的很精彩。當你陶醉在輕鬆的敘述語調或「我」與人鬥嘴的場面,感到刺激興奮時,便能領會作者的節奏安排是多麼巧妙。
──推理小說評論家 村上貴史
衝突的動作場面非常到位。為了得知真相,「我」結結實實地遭受暴力襲擊,付出疼痛的代價後,解謎的進展突然加速。這種原始生猛的故事推進力,真是令人讚嘆。
──日本讀者Amazon Customer
對於生活在紅燈區「外側」的人,只是以客人的身分花錢買短暫的歡快。生活在內側的主角「我」,帶我們窺探紅燈區居住者的喜怒哀樂。這是一本可跟著「我」一起醺然而醉的迷人小說。──日本讀者 悶
名人推薦:【名家醺然推薦】
「光是閱讀本作,不喝酒也能享受到微醺的暢快感。假使能配酒,想必能醉得更痛快。
不如讀兩遍吧。一遍清醒時讀,一遍拿著酒杯讀。」
──推理小說評論家‧村上貴史媒體推薦:【讀者暢快推薦】
主角「我」稱不上是偵探,也不是善良市民,只是做為萬事代辦屋(不良成分居多)奮力謀生。跟「我」一起悲傷、焦慮、憤怒、大笑、忍受嘲諷與屈辱,最後卻不知怎麼有種「啊,真是太好了」, 眼淚快跑出來的感覺。──日本讀者 mocha
小說中你來我往、機鋒處處的對話真的很精彩。當你陶醉在輕鬆的敘述語調或「我」與...
章節試閱
0
不久前,在風俗營業法尚未修正,「泡泡浴」改稱「土耳其浴」,愛滋病被認為是只有美國同志才會得的怪病時,我已在薄野走跳。
1
一陣寒風突地迎面襲來,我忍不住皺起臉。街上燈光絢爛奪目,散落各處的三七仔捧著廣告傳單,緊揪著運動外套衣領,發出近似哀號的聲音。
「冷斃了。」
附近一個三七仔顫抖著上半身向我攀談。
「是啊。」
「看樣子快下雪了吧。」
「最近生意好嗎?」
「怎麼可能。瞧瞧,這種鬼天氣哪來的客人?連個鬼影都沒看到。」
如他所言,街道上除了蜷著身子杵在原地的三七仔,沒有其他人影。
「別急,等一下就全部出籠了,從那裡。」
我朝對面那排居酒屋抬抬下巴。薄野再怎麼不景氣,不,應該說愈不景氣,這一帶的店愈熱鬧。三七仔一臉厭煩地「呿」一聲。
「搞什麼,噯,你今天該不會又要去這家?」
三七仔像要甩出右手,指著「KELLER OHATA」的藍光燈箱招牌。我點點頭。
「偶爾也來我們家玩玩嘛。」
「是有這個打算。」
我擠出曖昧的微笑,轉身走下階梯。
「說好了,一定要來玩,我會找最正的妹陪你。」
三七仔的話聲從上方傳來,我沒回頭,只舉起左手回應,不曉得他有沒有看見。算了,我的背影他大概連瞧都懶得瞧。
店內只有一名客人。這家店格局狹長,吧檯貼著牆壁延伸,那客人就坐在吧檯正中央。穿純白襯衫打紅領結,瘦小身軀外搭紅背心的岡本,疏遠地站在前面。另一個酒保多田似乎在廚房用餐。老闆大概在休息室沉迷於掌上型電玩。
岡本發現我,故意客套地說「歡迎光臨」,點點頭,邪氣地笑著。
「心情不錯嘛。」
我脫下外套,也邪笑回敬。
「還好啦。」
岡本假仙地表現出極端謙虛的模樣,遞給我黃色濕手巾。
「我一點也不在意。」
「當然,那完全是僥倖,我瞭。我也是有自覺的人。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哈哈哈。」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輸給岡本。他性格認真,做任何事都進步得很快,而且十分單純,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所以不討人厭。
「不過是一盤黑白棋,又不是一次定終生的比賽,對吧。話說回來,怎麼一臉呆滯呀,師父。」
嘖,其實這傢伙還是挺討人厭的。
他廢話連篇碎碎念,在我前面排好濕手巾、罐裝Peace香菸、大盒腸胃藥、斟滿水的平底杯。我從盒子裡拿出兩包腸胃藥,撕開封口。岡本把冰塊倒進老式酒杯(old-fashioned glass),邪笑著調起濃烈的特製Rusty Nail。
此時,獨坐吧檯的男子幽幽出聲。
「請問……」
「是!」岡本迅速回頭。
「不,呃……我是要找那位先生……」
接著,那傢伙開口時,忽然在我的姓氏後面加上「學長」這個噁心的稱呼。我盯著天花板把腸胃藥倒進口中,他冷不防來這麼一招,害我咳得上氣不接下氣。只見綠色顆粒化為一道薄霧噴向天花板。
2
「你頭髮再長一點,剛才就挺像摔角的那個Kabuki,體型也很像。」
岡本不慌不忙地移開吧檯的菸灰缸、平底杯、罐裝Peace,拿濕手巾擦拭桌面。我大概應了五次「不,沒事、我沒事」,喝了五口水,邊咳邊乾嘔好幾次。最近刷牙時也常這樣。再怎麼說,我已是二十八歲的老頭。連肝臟都被我操得慘兮兮。
「好啦,我沒事。」
我重申一次,喝下第六口水,轉向對方。
「你是……?」
「不好意思,你好。」
仔細一瞧,對方稚氣未脫,約莫剛滿二十歲,穿普通的平底鞋、窄管牛仔褲,及印著HOKKAIDO UNIV.字樣的深藍長袖厚T,四處可見的土黃休閒羽絨外套掛在鄰座的高腳椅上。他喝著兌水淡酒,頭髮蓋住耳朵,感覺每天早上都會刮鬍子,不過下顎,應該說下顎深處沒刮到,鬍鬚稀稀疏疏亂長一通,而他似乎沒察覺。原本想問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隨即放棄,答案一目瞭然。
「呃,我叫原田。……是小學長六屆的學弟。」
果然,這小鬼講話不看人,對著膝蓋喃喃自語。這種傢伙到處都有,沒什麼稀奇。一點都不稀奇,只是模樣很寒酸而已。
「研究室有許多關於學長的傳聞。」
然後,他窺探般覷我一眼,笑了笑,又畏畏縮縮地低頭。以為我聽到「傳聞」二字就會暗爽嗎?
「哦,都說些什麼?……別害羞,過來一點,要不要坐這邊?」
「嗯。」
自稱原田的男孩老實回話,起身坐到我右邊。他體型瘦弱,身高約一百六十五公分,體重約五十公斤。比我矮十公分,輕三十公斤。不是我說,我還真胖。
「是這樣的,三村助教提過,學長在薄野做些幫忙尋人之類,像偵探的工作……」
我快失去耐性了。
「三村助教好嗎?」
「喔,不錯啊……」
「東海林教授明年退休吧?」
「是、是的,沒錯……」
「所以,木山副教授會升教授,三村助教會升副教授?」
「這個嘛,不曉得會變成怎樣……」
「還是先當講師?那副教授的缺……學校有從東大來的老師嗎?」
「不清楚……」
很好,對話節奏順暢。接下來問「你今年大三嗎」,原田會回答「是」或「不是」,我就丟下一句「唔,那你加油。抱歉,我有事先走,帳算我的,我請客」,然後離開,脫身。
「你呢?今年大三?」
在這節骨眼,岡本把一杯Rusty Nail Custom放在我面前。
「久等。」
原田沒放過這個好機會。
「是的,我今年大三。聽三村助教這麼一提……我有件事想找學長商量,應該說想借重學長的智慧……」
我不禁嘆口氣。
「我的朋友失蹤了。」
原田斬釘截鐵地說,從心急如焚的神情看來不是謊言。
「傷腦筋,三村助教似乎誤會我的工作……是喔,你的朋友失蹤。」
總之,就是同居的女友在外過夜沒回來吧?那又怎樣?
「四天沒回家。」
「你們同居嗎?」
「咦……」
他畏首畏尾地抬眼窺探我的表情,旋即低下頭。
「呃,沒有……我住在學校附近的套房。」
「上過她了嗎?」
「上……呃,嗯嗯……有。」
「正嗎?」
「我很喜歡她。」
原田忽然抬起頭,語氣坦率肯定。我有點嚇到。
「敗給你了。」
我嘀咕著,拿起Rusty Nail啜一口,原田露出笑容。
「對了……你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
「三村助教有學長的聯絡方式。」
申請退學時,我似乎填過一些資料。
「上面寫的幾個電話和住址,都是小酒館之類的店,這間酒吧還特別打雙圈。助教告訴我,看起來像道上兄弟的就是你。」
「……噯,話說在前頭,真正的黑道才不會穿成這樣。他們一定是穿高爾夫球裝、樂福鞋繫白鞋帶,這個季節可能會套上開襟拉鍊厚外套。我這身打扮,應該屬於黑色電影裡的黑幫角色。」
我總是穿雙排扣西裝,低領、側開叉。襯衫不是黑就是深藍,領帶偏愛暗色系配上華麗圖紋。身邊的傢伙都說我像黑道,這一點我可不服。
「這樣啊……反正我一眼就看出來。」
「好吧……聽你說也行,不過我會問很多細節,沒關係嗎?」
「我想不出其他辦法。」
我仔細打量原田,他猶如走丟的天真孩童般不知所措。
「她四天沒回來,這段時間你都在幹嘛?」
「我一直待在她的住處。」
「只有這樣?」
「嗯……我擔心她隨時會回家……不待在那裡,電話打來接不到。我不曉得怎麼辦,找警察也沒用。電視上不是常演,沒牽扯到犯罪,警方不會認真搜索。況且,即使去找警察,怎麼說……我的意思是,就算要報案,用什麼身分報?感覺怪怪的……」
「怪怪的……」
「對啊……通知她家人,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你覺得她可能遭遇不測嗎?比方,遇上作奸犯科的人。」
「因為……要是沒事,她應該會聯絡我。四天過去,錢也用得差不多了。」
我不可置否地點點頭,把Rusty Nail一飲而盡。
「方便的話,關於費用,能不能晚一點……」
我不由得笑出來。
「好啦,現在只是聊聊,不用錢。稍微放心了吧。」
「謝謝!」
我望著他求救的眼神,雖然厭煩,腦袋卻開始編織劇情,並化為影像,加上配樂。
老掉牙的劇情。男孩大概長住在女孩的租屋,兩人等於是半同居。然後,女孩愈來愈討厭他,約莫是他不可靠之類的。女孩漸漸不再回來,男孩一籌莫展,心急如焚。一週後,萬事代辦公司的人上門,把所有東西打包裝箱,轉眼屋子變得空蕩蕩。男孩纏著代辦公司的人問:「請告訴我她搬到哪裡?」
「這是客人的隱私,恕難奉告……」親切的大個子男人將防滑棉質手套塞進後褲袋回答,接著就開走小貨車。男孩步履蹣跚,打算回自己的住處時,「喂,你等等!」一道嘶啞的聲音喊住他。頭髮上盤、年過五十的歐巴桑走出「一號室」,一字一句地說:「鑰匙還來。」看情況,歐巴桑和女孩是同一陣線。少年有氣無力地遞出備用鑰匙,踉蹌離去。背景是催淚的夕陽餘暉。差不多是這樣。
「我叫原田誠。」
男孩一本正經地自我介紹,根本不曉得現在已播到離去的小貨車與「劇終」重疊在一起的畫面,背景音樂是嘉托‧巴比耶瑞演奏的〈布貝的情人〉。
「哦,叫誠啊。」
我點點頭,喝一口Rusty Nail。原田一語不發地看著我。
「怎麼?」
「沒有,那個……你不記一下嗎?」
大概是我的態度太隨便。不過,我確實是隨便聽聽。原田流露些許不悅之色。我朝在一旁偷笑的岡本,比比寫字的動作,他立刻遞來原子筆和紙。
「呃,ㄩㄢˊㄊㄧㄢˊ,就是最普遍的『原田』吧?」
「是的,誠實的『誠』,言字旁。二十二歲。」
「地址呢?」
依原田所述,他住在地下鐵北十八条站往北走一小段路附近。那條街上很多租給學生的套房和公寓,以前我常拎著便宜的酒去找朋友們玩,算算已是超過五年前的往事。
「那麼,你失蹤的朋友是哪位?」
「道央女子短期大學家政系二年級,諏訪麗子。」
原田用手指在吧檯上寫下漢字。那是間名不見經傳的女短。
「沒聽過,有這所學校嗎?」
「學長瞧不起人嗎?」原田發火。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真的沒聽過……在哪裡啊?」
「野幌。」
「哦,麗子小姐的住址呢?」
原田報出報出一個位在菊水的住址,「Maison de Shibata」公寓二○三室。
「離地下鐵車站很近。」
「對,她都搭到新札幌站,再換公車去學校。」
「嗯,她老家在哪邊?」
「置戶。」
「ㄓˋㄏㄨˋ?」
「在北見附近。」
「哦……我想起來了,『人力輓馬賽』之類的活動似乎很有名。……那你呢?」
「津別。」
「ㄐㄧㄣ ㄅㄧㄝˊ?」
「也在北見附近啦。」
「喔……」
世界還真大,這麼多沒聽過的地名。廢話。
「……上通識課時,大夥辦聯誼,因為我和她老家很近,就聊起來了。」
「那間女短不是在野幌?」
「是啊。」
「現在流行和那麼遠又沒聽過的女短聯誼?」
「我們班的某傢伙透過關係找到的,說道央家政系的比較好『把』。阿麗是被朋友逼來作陪,事後聽阿麗說,她其實不太想去那場聯誼。」
「好啦,這不重要。你們認識多久?」
「去年六月聯誼認識。」
「你們交往狀況如何?我是說,你不是還曉得她幾天沒回家?」
突然,原田講起自己的故事,而且愈講愈激動。起初只感覺得出他心情非常鬱悶,看久就明白──他深愛著諏訪麗子。
故事本身平凡無奇。兩人在聯誼聊得十分開心,約好兩天後再見面。兩天後,兩人晚上就睡在一起。原田還一臉認真地補充,他是第三次,麗子是第一次。(……「我是第三次。」「你數過?」「對啊,不過現在數不清楚幾次了。」「那當然。」
……)地點在薄野郊外一角的賓館,沒什麼新鮮。之後的相處,跟一般清閒學生的交往差不多。只不過,兩人都不是有錢人,漸漸改在菊水約會,於是原田直接在麗子的租屋過夜。唔,在女孩的租屋半同居,這也是常見的模式。
「然後,我們就這樣交往下去。原本擔心很快就膩了,沒想到不僅沒有,還發現我愈來愈不能沒有阿麗。
「嗯。」
「然後,阿麗也這麼認為。」
「挺幸福美滿的,很多人求都求不到。」
原田露出開心的表情。我暗自決定,以後不再開他這方面的玩笑。
「呃,她四天前失蹤,所以是星期六?」
「對。」
「那天她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嗎?」
「……阿麗去學校時,我還在睡。星期五晚上,我喝了些小酒,阿麗幾點進門我也想不太起來。星期六我睜開眼已是中午,阿麗早就在學校……之後一直沒回來。」
「……她經常外宿嗎?」
「從來沒有!」
「那是你們住在一起後的事吧?」
「對,沒錯,住在一起後,她從沒在外過夜。」
原田像在說給自己聽。
「她有沒有趁你出門回來過?」
「不可能,我幾乎足不出戶。」
我將剩下的Rusty Nail一口氣灌下肚,默不出聲。看來,目前最親切的做法就是直接告訴他:人家不喜歡你了,放棄吧。但原田駝著背,盯著我的側臉。
「這樣啊……」
我無意義地低喃。原田站起,傾身向前,從牛仔褲後袋掏出包著書套的文庫本。
「還有,這個……」
他坐回原位,把一張夾在書裡的三乘四吋的彩色照片放在吧檯上。
「這是阿麗最近拍的相片。」
真是敗給他。
「什麼時候照的?」
「今年九月中旬,大概是兩個月前。這時節她應該會穿深藍大衣。」
說不上來,乍看十分普通的女孩,對著鏡頭微笑。穿綠底方格的裏綁長裙(wrap skirt)配粉紅運動服,胸前印著POP GAL’S ARE NACHULALU幾個意義不明的白色字樣。直髮,似乎留很長。不美、不胖、不可愛、不醜,去除彷彿腦袋空空的微笑,像是天真善良的女孩。
「你拍的?」
「是啊。」
「難怪她笑得這麼開心。」
原田一語不發盯著照片。我嚇一跳,該不會要掉淚吧,當下衝動地想把憂鬱男孩從身邊趕走。
「家裡有電話吧,我是指她的住處。」
「有。」
「撥通電話看看,搞不好她回去了。那就恭喜恭喜,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好。」
原田不安地站起,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放在我身後的粉紅電話。
我向岡本點一杯Martini。
「沒人接……果然還沒回家。」
原田一臉悲傷地回座,有氣無力地報告。
「肯定出事了。」
「是喔……這樣吧,你先回家,回她住的地方,搞不好她會留話或留紙條。假如都沒有,真的失蹤(!哈哈哈),再打給我。」
「你會過來嗎?」
「假如她真的沒回住處。」
「約好嘍,一定要來。」
「我會去啦。」
「拜託,拜託學長了,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
「不用擔心。」
岡本把Martini放在我面前,啜一口,好喝。我不由得露出滿足的笑容,但隨即察覺一股悲傷的視線,只得慢慢收起笑容。
「總之,你先回去,確認她回來沒。」
「要是阿麗沒回家,學長真的要過來一趟。」
「知道,打電話給我。」
原田不停說著「拜託學長」,右手不牢靠地抓著外套,離開店裡。
0
不久前,在風俗營業法尚未修正,「泡泡浴」改稱「土耳其浴」,愛滋病被認為是只有美國同志才會得的怪病時,我已在薄野走跳。
1
一陣寒風突地迎面襲來,我忍不住皺起臉。街上燈光絢爛奪目,散落各處的三七仔捧著廣告傳單,緊揪著運動外套衣領,發出近似哀號的聲音。
「冷斃了。」
附近一個三七仔顫抖著上半身向我攀談。
「是啊。」
「看樣子快下雪了吧。」
「最近生意好嗎?」
「怎麼可能。瞧瞧,這種鬼天氣哪來的客人?連個鬼影都沒看到。」
如他所言,街道上除了蜷著身子杵在原地的三七...
作者序
【給台灣讀者的話】/東直己
初次見面,謝謝您拿起了這本書。
各位「現在」所處的地方,天空長什麼樣子,呼吸的空氣又是怎麼樣呢?想像著風吹來的香味、還有街頭人聲鼎沸的聲音就讓我樂不可支;另一方面,我這邊的「現在」是寒冬。雪祭延後了幾天,天空綿延不絕又寂靜無聲地在大地降下白雪(即使在這個當下,窗外也是降著厚厚一層雪幕) 。如果不穿上外套,根本連三步都踏不出去(超過三步就會死的)。我就是生活在這麼寒冷的世界。
不過,就算日本和臺灣的氣候和呼吸的空氣有多麼不同,就算沒辦法親眼見到住在街道上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我認為我們之間一定還是有交錯相通之處。而在這個故事中,我想描寫的,正是在札幌的街道上、繁華的紅燈區薄野裡,心裡擁有無限悲傷、拚命活下去的人們的故事。雖然我沒把握自己有沒有恰當表達出來,但如果您可以樂在其中,我會非常高興。
遺憾的是,我至今從未到臺灣旅行過,等到雪融之後、趁著這次作品翻譯出版的機會,我打算到臺灣叨擾一趟。如果那時可以在臺灣的書店找到這本書,想必是我無上的光榮。
【給台灣讀者的話】/東直己
初次見面,謝謝您拿起了這本書。
各位「現在」所處的地方,天空長什麼樣子,呼吸的空氣又是怎麼樣呢?想像著風吹來的香味、還有街頭人聲鼎沸的聲音就讓我樂不可支;另一方面,我這邊的「現在」是寒冬。雪祭延後了幾天,天空綿延不絕又寂靜無聲地在大地降下白雪(即使在這個當下,窗外也是降著厚厚一層雪幕) 。如果不穿上外套,根本連三步都踏不出去(超過三步就會死的)。我就是生活在這麼寒冷的世界。
不過,就算日本和臺灣的氣候和呼吸的空氣有多麼不同,就算沒辦法親眼見到住在街道上的人們的喜怒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