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相思成災(上下集套書)
「男人傻到極點,女人嫉妒到極點,
愛情是多麼虛幻而殘酷,
為何人們還是如此無怨無悔?」
本所深川的「糊塗蟲」巡捕井筒平四郎,極怕麻煩卻常惹上烏龍事,幸好老天爺待他不薄,賞賜活潑伶俐的小夥伴──十四歲的「萬人迷」天才外甥弓之助,和記憶力超群的耿直少年「大額頭」,陪他度過驚濤駭浪。
只是,近日江戶不太平靜,來歷不明的男子被砍為兩半,殘留的血水遲遲未消。不久,賣神藥「王疹膏」的瓶屋老闆橫死家中。更怪的是,失蹤的賣春女無端變成浮屍,搞得人心惶惶。
平四郎出馬調查,豈料小夥伴狀況多多,弓之助音訊全無,拋棄「大額頭」的生母上門糾纏。好不容易掌握線索,又挖出二十年前的慘案。千辛萬苦湊齊所有拼圖,他才恍然大悟,一切皆離不開世間最難解的男女因緣……
▍名家推薦
宮部美幸一路追索愛的痕跡,看愛怎樣生成,又怎樣錯落。愛是債,愛也是償,愛是永遠不能報償。
人們以為愛很浪漫,但講到「其後」,愛其實很務實,也正因務實,才讓人心頭重。
這不是時代的重量,那個時代的愛和此時一樣重,其實是活著的重量。
──作家 陳柏青
▍
作者簡介
宮部美幸 Miyabe Miyuki
1960年出生於東京,1987年以《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得獎作〈鄰人的犯罪〉出道,1989年以《魔術的耳語》獲得日本推理懸疑小說大獎,1999年《理由》獲直木獎確立暢銷推理作家地位,2001年更是以《模仿犯》囊括包含司馬遼太郎獎等六項大獎,締造創作生涯第一高峰。
寫作橫跨推理、時代、奇幻等三大類型,自由穿梭古今,現實與想像交錯卻無違和感,以溫暖的關懷為底蘊、富含對社會的批判與反省、善於說故事的特點,成就雅俗共賞,不分男女老少皆能悅讀的作品,而有「國民作家」的美稱。近來對日本江戶時代的喜好與探究,寫作稍偏向時代小說,近期作品有《怪談》、《落櫻繽紛》、《荒神》等。2007年,即出道20週年時推出《模仿犯》續作《樂園》。2012年,再度挑戰自我,完成現代長篇巨著《所羅門的偽證》。2013年,「杉村三郎系列」《誰?》、《無名毒》改編日劇,並出版最新作《聖彼得的送葬隊伍》。
譯者簡介
林熊美
畢業於台大,現為專職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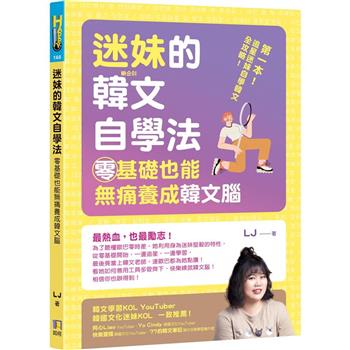








一直知道宮部美幸的推理小說分成很多類,但對於時代與奇幻系沒特別的興趣,卻莫名其妙地因為書名(還當時手邊沒特別有趣的?又或者是為了湊網購的免運費?)開始讀了起來。 有點意外登場人物這麼多,以致主、支線故事也頗多,但卻巧妙穿插、貫穿,卻又都圍繞著與書名一致的主題:男人與女人。連男三都排不上的、人如其名臉和身材都圓滾滾的十德長屋老好人丸助,和死去的老婆阿萬都有各種依賴、信任、嫉妒、分離的感情描述。故事的細節真的很細緻。 也喜歡故事裡各種很有人情味的互動,個人感覺相比模仿犯、所羅門的偽證、聖彼得的送葬隊等社會寫實系的小說裡,多了許多的溫暖、樸實、與憨厚,也不像電視上演的時代劇,特意強調嚴謹的階級、尊卑、從屬。劇情的展開也不是緊張刺激的路線,讓剛讀完野獸之城而繃緊高懸的心臟及大腦舒緩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