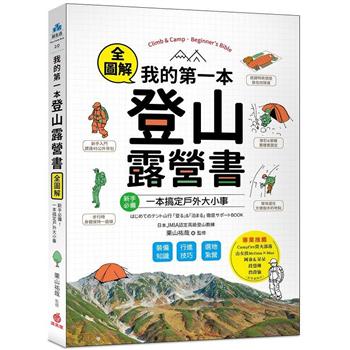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6 項符合
人間椅子(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中村明日美子獨家書衣)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電子書不附贈書卡
慾狂愛妒恨,人性的醜陋及癡狂而生的豔魅,
全是他筆下場場智性詭鬥的狂氣燃料。
他的文字如蟲蟻蠕動肌膚,教人喘不過氣……
★宛如文藝復興時的全方位創作者:關於江戶川亂步
喜愛歐美恐怖作家愛倫坡,故事流著東西的血脈,
推理研究評論、翻案文學、青少年文學、長短篇無一不精,
更是本格派、社會派的開山鼻祖。
影響橫跨推理、大眾文學、官能小說和純文學領域,
三島由紀夫、橫溝正史、松本清張、東野圭吾皆受其影響。
他晚期設立江戶川亂步獎,催生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提拔新人不遺餘力,推廣推理小說為一生職志;
作品也是名偵探柯南及影視動漫的取材對象,改編作就超過七十部;
更是日本男女老幼都喜愛的國民作家,影響力至今無遠弗屆。
一旦踏進閱讀的世界,不管路途再多麼峰迴路轉,
最後必然會走到這位大師--江戶川亂步的面前。
★跨領域的藝術家結合:中村明日美子的江戶川亂步
亂步的創作風格成功和大眾文化結合,成為日本國民不分男女老少的娛樂。超越領域的創作性,與漫畫家中村明日美子不謀而合。出道十六年的中村,是日本重量級漫畫家。畫風大膽俐落,同時散發禁欲的情色感,風格前衛耽美。從故事深刻,卻又性感豔麗、洋溢著情色官能味道的作品,到青春爽朗的日常題材都可駕馭,多變以及特殊的風格讓她成功贏得眾多讀者的絕佳評價。
★獨步文化‧亂步逝世五十週年精選改版計畫
獨步精選六部作品改版,封面邀日本異色漫畫家中村明日美子繪製,全文重新校稿,邀日本亂步研究者諸岡卓真撰寫全新導讀,用更貼近年輕讀者的方式重新介紹日本推理之父。根據經典性、題材的開創性,與亂步特色的代表性各精選出三部短篇選輯和長篇。短篇選《陰獸》、《人間椅子》、《兩分銅幣》,長篇作《孤島之鬼》、《D坂殺人事件》(日本三大名偵探之一的明智小五郎連作短篇)、《帕諾拉馬島奇談》,陸續於二〇一七年出版。
【令人愛不釋手,捨不得一次讀完--第二發:《人間椅子》
殘酷、瘋狂又悲哀,詭譎、獵奇又滑稽,
拋棄一切理性,只願耽溺在無邊無際的狂氣之中。
〈人間椅子〉
貧窮又醜陋的製椅工匠,過著無人相伴的寂寞日子。某天,他突發奇想,躲進了交貨前的豪華座椅中,而這張椅子送到了一名貌美貴婦的家中。沉溺於隔著椅子愛撫女體的荒淫生活的他,對椅子主人萌生了偏執的愛情……/亂步最廣為人知的奇異短篇,讀過便無法忘記。
〈阿勢登場〉
因為生病無法滿足妻子的格太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妻子阿勢在外風流。某日,他偶然被關在長衣箱中,不斷對外呼救後,終於等到了阿勢前來相救……/亂步筆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惡女。
〈芋蟲〉
時子和從戰爭中倖存,卻失去四肢,再也無法言語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兩人的生活猶如一場不可能假釋的無期徒刑。互相折磨的他們最後做出的選擇將會是……/亂步最知名的反戰小說。
〈和貼畫旅行的人〉
我在一次旅行中,邂逅了帶著貼畫的男人。貼畫上有著栩栩如生,貌美如花的豆蔻少女以及滿頭白髮的蒼老男子。男人見我好奇,便說要告訴我一個詭異的愛情故事……/亂步自認短篇代表作的浪漫幻想傑作。
收錄亂步寫盡人心最幽微、最不可告人的那一面的十五篇短篇小說,
引領你望進那深不可測的黑洞。你可有勇氣一窺究竟?
本書特色
★完整了解亂步世界:亂步研究者精彩的全文導讀,推理評論家傅博的豐富註釋,不僅了解亂步作品,及其相關風格的作品,更能體會到日本大正及昭和時代風情。
作者簡介
江戶川亂步 EDOGAWA RANPO(1894-1965)
本名平井太郎,生於日本三重縣名張町。江戶川亂步(EDOGAWA RANPO)為筆名,取自現代推理小說的開山鼻祖美國小說家愛德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日語發音EDOGA.ARAN.PO。
1923年在《新青年》發表備受高度評價的處女作〈兩分銅幣〉,從此展開推理小說創作。戰前日本推理小說通稱為「偵探小說」,之後在江戶川亂步為首的等人提議下,於1946年為「推理小說」所取代。
1925年1月,《新青年》刊載〈D坂殺人事件〉,名偵探明智小五郎初登場。此後,相繼發表了以青少年為目標讀者的《怪人二十面相》、中篇故事〈陰獸〉等,寫作風格多變,並撰寫大量評論文章。身為重量級作家,江戶川確實掌握推理小說的本質,理解推理小說是一種以邏輯解開謎團的文學,作為日本推理小說的開拓者當之無愧。
相關著作
《陰獸(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中村明日美子獨家書衣)》
《幻影城主》
《少年偵探團》
《黑蜥蜴》
《魔術師》
《詐欺師与空氣男》
《人間椅子》
《蜘蛛男》
《帕諾拉馬島綺譚》
《怪人二十面相》
《D坂殺人事件》
《孤島之鬼》
《陰獸》
繪者簡介
中村明日美子
出道十六年,日本重量級漫畫家。畫風大膽俐落,同時散發禁欲的情色感,風格前衛耽美,從故事深刻,卻又性感豔麗、洋溢著情色官能味道的作品,到青春爽朗的日常題材都可駕馭,多變以及特殊的風格讓她成功贏得眾多讀者的絕佳評價。
譯者簡介
王華懋
嗜讀故事成癮,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近期譯作有《所羅門的偽證》、《邪魅之雫》、《渴望》、《再見,德布西》等。
譯稿賜教:huamao.w@gmail.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