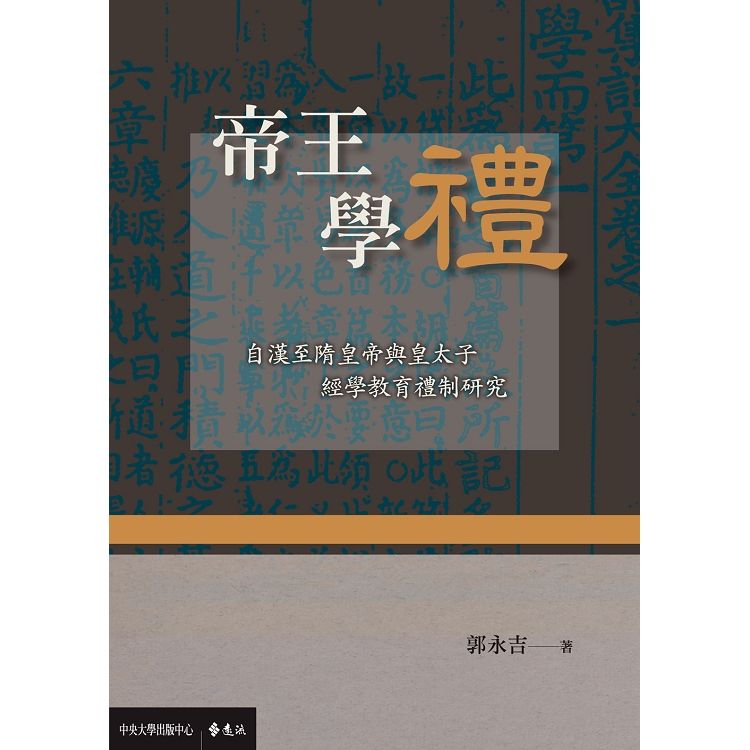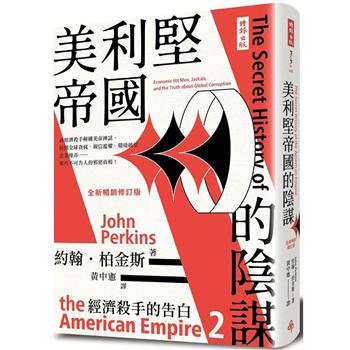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帝王學禮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32 |
中國史地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教育總論 |
$ 378 |
歷史 |
$ 378 |
教育學 |
$ 378 |
社會人文 |
$ 37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帝王學禮
本書探討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的經學教育禮制,依受學期間、學成儀式與學成後再度研習三個階段進行論述。主要針對執教者(伴學者)、受業年齡及教材、教育儀式、講經集會、教育地點等,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如執教者與伴學者的待遇、經書教育成果的評量等,予以探索。尤其在辨別實際執教者非名義上的師傅——太傅、少傅,而是朝臣以侍講、執經、侍讀等名銜兼職入授;釐清因不同身份、場合,所行釋奠禮實有差異,以及講經與釋奠禮之關係等;並詳細考察有關經書的講經集會也非僅一種,有因釋奠禮而舉行者,是作為幼君、儲君受學告一段落的考成典禮;也有平時召集群臣研討經義而舉行之講經集會,屬於學成後再度研習。凡此,均能提出有異於前賢的相關看法,並廓清歷來諸多疑義未解之處。
作者簡介
郭永吉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兩漢經學史、漢魏六朝文化與思想、兩漢魏晉南北朝辭賦。著有專書《六朝家庭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研究》,以及〈先秦兩漢東宮稱謂考〉、〈兩漢經學師法家法考〉、〈王粲〈登樓賦〉結構分析與創作技巧探索〉、〈鮑照〈蕪城賦〉研究〉、〈〈登徒子好色賦〉重探〉、〈試論先秦兩漢時期琴之功用〉、〈西漢朝廷樂舞之雅與俗——兼論儒家學說與西漢政權的關係〉、〈秦漢律令小議〉等學術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