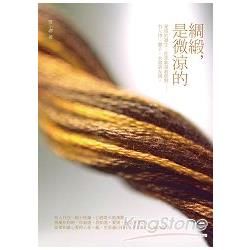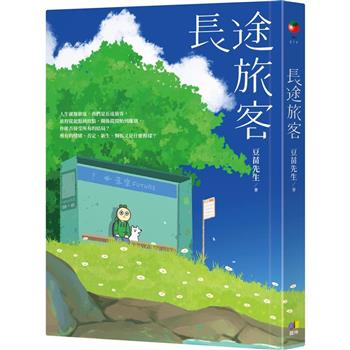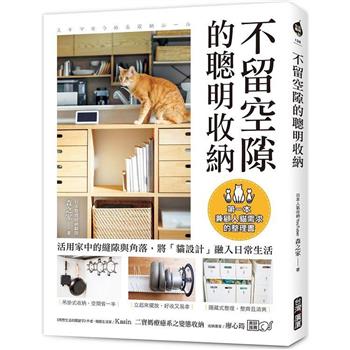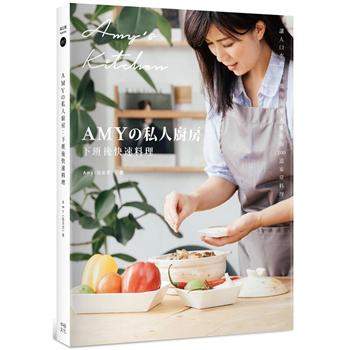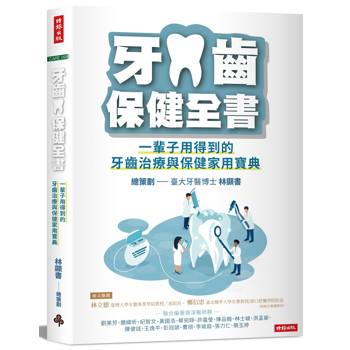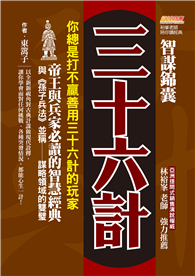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綢緞,是微涼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25 |
古典言情 |
$ 208 |
現代散文 |
$ 21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個執著於禪的女子,敘寫著唯美的傾城記憶與往事。一部關於情感、生活、心靈的隨筆。
這個充滿禪意的女子,用自己獨特細膩的視角、優雅寂靜的文字,書寫了無處不在的美與愛。愛情的發生,從來就是刹那間——有人待一輩子,永遠是友情。有人只在一起十秒鐘,已經是天地鴻蒙。春風吹到時,你知道,我知道,愛情,也是知道的。如果和最心愛的人在一起,生是滿目碧綠,看山絕色,看花傾城。
綢緞兩個字,是帶著涼意的。也只適合在蘇杭這樣的地方穿。或者說,江南的女子適合。綢緞,還有一種自憐、自哀、自珍惜的荒意。當人老了、珠黃了,把自己當年的綢緞翻出來晾曬,那是什麼心情呢?我忽然想到那沉箱幾十年的老絲綢。年輕的綠變成了蒼老的綠,不復當年的光滑與曼妙,一任華年老去。
綢緞,是微涼的。恰若,那光陰。一把把摸上去,是涼的。是涼的呀!愛情的發生,從來就是刹那間——有人待一輩子,永遠是友情。有人只在一起十秒鐘,已經是天地鴻蒙。春風吹到時,你知道,我知道,愛情,也是知道的。如果和最心愛的人在一起,生是滿目碧綠,看山絕色,看花傾城。個執著於禪的女子,敘寫著唯美的傾城記憶與往事。
雪小禪散文隨筆集。一部關於情感、生活、心靈的隨筆。這個充滿禪意的女子,用自己獨特細膩的視角、優雅寂靜的文字,書寫了無處不在的美與愛。筆調熱烈而安靜,豪放而細膩,看似平靜無奇的文字中,深藏著生命的禪意。就像作者說的那樣,如果你明白我,我們就是「素心花對素心人」。
【作者簡介】
雪小禪
中國作協會員,河北文學院簽約作家,《讀者》雜誌百名簽約作家之一。出版小說及隨筆集四十餘本,其作品多次入選中學課本讀物,並多次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同時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暢銷日本、越南等國家。繁體版《無愛不歡》《刺青》《我愛你,再見》已經在臺灣上市。曾為《流年》雜誌主編,迷戀戲曲,現任教於中國戲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