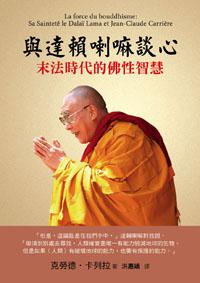1.末法時期
我從一個我們會(或幾乎都會)自問的問題開始:「我們是處在末法時期(Kali-Yuga)嗎?也就是說:我們是身處於一個毀滅的時代嗎?是否所有的希望都已消失?依照印度教傳統的說法,Kali-Yuga實際上是『黑暗時代』,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克里希那(Krishna)去逝後的次日。」
這是一個黑暗、愚昧、無知的時代,道德淪喪,正法消逝。也就是說,現今世界的規律,是充斥著野心、虛偽與商業氣息。阻擋無用,因為一切將會消失。也因為宇宙的輪迴已到了一片乾枯、饑荒、互相交戰,社會關係蕩然無存的時候。如同在《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古印度民族大敘事詩)已經提到過的:已到了人們不再有力量、勇氣,一切都乾枯困難的時候了。枯死與乾熱的土地,也變成了烈火下的犧牲品。一切都已陷在世界末日中。
緊鄰我而坐的,是這位大家皆尊稱為法王丹增嘉措(意為正法大海)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他看著我,並仔細聽著,非常地安靜與專心。
我繼續問完想問的問題:「然而,也有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我相信是較屬於佛教徒的。那就是認為: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有道德、互助、嚴守戒律的時代,也就是『賢劫』。在上述二種傳統中,您認為是那一種呢?」
「毫無疑問的,當然是第二種。」
「基於那些理由呢?」
「我想至少可依三方面來說。首先,我認為戰爭的觀念最近已有些修正。在二十世紀初,甚至到六○、七○年代,我們還是認為很多事最後是以戰爭來解決。而且有個很古老的觀念:戰勝者總是對的。勝利者是上帝或諸神的信物,他們總是站在他這邊。如此一來,戰勝者強迫戰敗者接受其法令。往往都以簽訂條約為方式,以抑制其將有報復的藉口。此外,武器設備的重要性,尤其在核子方面,都是末法時期的中心要素。核子武器競備,實已造成世界毀滅的大威脅。」
「您認為此威脅目前已漸漸消除了嗎?」
「當然,我深信這是必然的。其實,現在冷戰似乎已緩和,核子武器也在裁減當中,誰還能抱怨呢?」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在我們會談的同時,世界上有超過五十多個戰爭正在進行。而且有些就在我們附近。例如:阿富汗、喀什米爾,或印度境內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交戰;有許多戰爭,歐洲報紙從不提及的,如游擊戰,或不丹王國反對尼泊爾移民工人等。」我告訴他,真正的麻煩是南斯拉夫所謂的「淨化」與炮轟的戰爭。那些已造成整個歐洲的躊躇不前。老實說,沒人敢自稱比以前較不殘忍。
「我知道。」達賴喇嘛如此回答我。「這些當地的戰爭都非常殘忍,而且確實很不好。所有的戰爭,不論大小,都是負面的。它揭露人們險惡的一面,而且只會導致新的衝突。但是在核子的威脅下,地球上的每一個地方似乎無一能倖免。而至少,小的戰爭是有限的。就如今天,我們在達蘭沙拉(Dharamsala),我就覺得平靜。」
2.真正的力量
他微笑了一會兒繼續說。
「不過,的確很多這種戰爭的發生,是由於核子威脅的遠離。」
「怎麼說呢?您有其他樂觀的理由嗎?」
「當然有。那就是我要提到的第二點:雖然有許多表現,但我相信戒殺生、無暴力的觀念,已很明確的指出重點。在聖雄甘地時代,這位我所謂的先人,無暴力常常被視為懦弱,幾乎是種很可恥的行為。但現在的情形已不同了,以現今的觀點而言,無暴力的選擇是種正面肯定的行為,它創造出一種真正的力量。看看在南非的情況,以及阿拉法特與拉賓的和談。幾十年來,巴基斯坦與以色列,除了動武外,毫不相往來,而現在也已和平的對談了。」
「是的,但雙方也都還有所保留,而且會走到暗殺、大屠殺,或者高唱著殲敵的歌聲,屆時到處教導他們的孩子:拿起你的劍,去殺人吧!」
「當然,有可能會有這麼一回事。但您倒不用告訴我,人們有能力做出多麼可怕的事。而且,巴基斯坦人與猶太政府確實是個好例子,並且也已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此外我還有另外一種感覺,我相信透過新聞報導、媒體傳播,也就是所謂的聯絡交流,宗教團體已較以往更常互相拜訪,且更加的互相認識了。」
「但對有些回教國家,並不真的是這樣子。相反的,他們反而有將自己封閉在自己圈子裡的趨勢;並想杜絕所有外國人的影響。尤其是對西方人。在阿爾及利亞,有些激進團體更是進一步的殺害外國人。甚至,有些事業也同樣的荒謬與殘忍。他們反對時代精神,根本相反的培養出其他團體,去傷害那些被假設可傷害的,這些事進行得很快。」
「對一個國家而言,孤立是非常不好的,因為它會變得不實際。在本世紀前中葉,藏人非常少與其他種族或教義接觸,這導致很大的損失,時間遠遠的把我們拋在後頭。至於那些回教國家,雖然有些人同時維持甚至更強化他們的封閉性;但若以全世界來看,孤立的確是喪失了生存空間。二十年來,我拜訪了許多國家,所到之處,大家都告訴我:我們彼此更認識了。自第七到第十世紀,在極具包容性的唐朝;於中國西北土蕃區的敦煌,是一個亞洲宗教的研究中心。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後兩種宗教皆源自波斯)在那裡匯集,教義交流,致力於彼此的認識。」
「他們的原則是加強共通的義理,並略及迥異之處。」我說。
「無疑的,我們現在所欠缺的,就是類似那樣的交流中心。」達賴喇嘛接著說。「若能成立一個那樣的單位,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在我這邊,也經常盡可能的與其他宗教領袖碰面,並一起外出拜訪他們的聖地。所以經常發現有些傳統其實是互相關聯的。這也是我們常在一起思索的問題,並分享片刻的寧靜,我常常於其中獲得很深的領悟。」
3.和平的觀點
三月,也就是訪談達賴喇嘛幾星期後,他到以色列訪問。在那裡他還見了猶太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德魯茲教派穆斯林,甚至巴哈教派。當時,他也參觀了教堂,奧瑪(Omar)的清真寺、哭牆以及其他地方,並以和平的觀點,分別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會談。雖然他認為彼此的鴻溝還是很深,但同時,從各方面看來,他也很肯定的宣稱已看到雙方極佳的「脈動」。
「我一直堅信在宗教領域裡,與世紀之初相比,我們是在進步中。」他繼續說。
「但很多評論家卻持相反的看法。甚至在基督教與印度教裡,我們也到處聽到談論宗教整合主義。」
「這個現象的高漲,是令人擔憂的。」他告訴我說。「許多人想在那裡看到人們對於亙古恐懼的反應。」
「或者是對於空想破碎的理論所提出來的一種補償作用。基於一些理由,許多人認為五○年代全體教會合一的經驗,似乎已變成日益擴張的信仰分化。現在,宗派林立,各種不同的理論也在戲劇性的拓展中。去年,美國的大衛教派,寧願與信徒死於火中,也不願屈服於警方。」
我補充了一個個人的實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於孟買,我擔任了由一些法國專家所舉辦一系列會議的助理。內容是開於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的歷史,瑣羅亞斯德教以前是源自波斯,現在信徒約有八萬多人,大多數是印度瑪哈瑞斯塔(maharashtra)地方的居民。」
「是的,他們稱為祆教徒,我知道。」
「有一場會議主題,是在討論瑣羅亞斯德教在七世紀阿拉伯人入侵波斯時,他們逃至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其中,也影響了另外一個現已流竄他處的教派摩尼教。此兩種教派為適應在早以被佛教深入影響的土地上生存,很自然的被迫接受一些佛教的傳統。」
「這種情形,經常發生。」
「我們只是很單純的做了語言學的研究,重點放在當時銘文的探討。在會議結束時,我們看見一位身材肥胖,像生意人的男士站起來,以非常好的英文大喊著:『瑣羅亞斯德教不可被曲解。不論如何,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是唯一的真神,瑣羅亞斯德是唯一的先知。』這宣告帶來了許多種族、政治的省思。例如:我們是真正的雅利安人。當時,我驚訝的愣在那裡。我今天剛剛發現了一位瑣羅亞斯德的基本理論者。當時我只知道如此回答那位男士。」
達賴喇嘛微微的傾身向我,並問道:「他代表多少百分比的祆教徒?」
「據別人告訴我,大約是百分之八。」
「那還好。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二就是答案了。」
他第一次笑,一個很直接、自然的笑。往後,他就經常露出可親的笑容了。這就是人們所講,過著神祕的生活,卻也會突然顯露自己的人物。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與達賴喇嘛談心:末法時代的佛性智慧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與達賴喇嘛談心:末法時代的佛性智慧
「但是,這鑰匙是在我們手中,」達賴喇嘛對我說。
「毋須到別處去尋找,人類確實是唯一有能力毀滅地球的生物。但是如果(人類)有破壞地球的能力,也要有保護的能力。」
達賴很堅持證據:「而且,這個事實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它是我們共同的母親。而且,所有對它造成的傷害,也必定會回報在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注重地球,那我們就會毀了自己的未來。」
「我們還來的及救它嗎?」
「當然。要從節育開始,而且要盡可能的快點宣傳。同時,我們可以整治河川、土地與我們呼吸的空氣。當然,我們還來得及做!一切操之在我們。而且,這不是感覺或道德的問題,這是我們切身的未來。」
作者簡介:
克勞德.卡列拉
章節試閱
1.末法時期
我從一個我們會(或幾乎都會)自問的問題開始:「我們是處在末法時期(Kali-Yuga)嗎?也就是說:我們是身處於一個毀滅的時代嗎?是否所有的希望都已消失?依照印度教傳統的說法,Kali-Yuga實際上是『黑暗時代』,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克里希那(Krishna)去逝後的次日。」
這是一個黑暗、愚昧、無知的時代,道德淪喪,正法消逝。也就是說,現今世界的規律,是充斥著野心、虛偽與商業氣息。阻擋無用,因為一切將會消失。也因為宇宙的輪迴已到了一片乾枯、饑荒、互相交戰,社會關係蕩然無存的時候。如同在《摩訶婆羅多》(Mahabha...
我從一個我們會(或幾乎都會)自問的問題開始:「我們是處在末法時期(Kali-Yuga)嗎?也就是說:我們是身處於一個毀滅的時代嗎?是否所有的希望都已消失?依照印度教傳統的說法,Kali-Yuga實際上是『黑暗時代』,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克里希那(Krishna)去逝後的次日。」
這是一個黑暗、愚昧、無知的時代,道德淪喪,正法消逝。也就是說,現今世界的規律,是充斥著野心、虛偽與商業氣息。阻擋無用,因為一切將會消失。也因為宇宙的輪迴已到了一片乾枯、饑荒、互相交戰,社會關係蕩然無存的時候。如同在《摩訶婆羅多》(Mahabha...
»看全部
作者序
時機
此番對話開始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地點為位於印度北方靠近達蘭沙拉的麥克雷歐崗村。更詳細的說,也就是達賴喇嘛居住的泰秦曲陵(意為大乘佛法寺)喇嘛廟內。我於二月十日抵達,剛好趕上藏人在十一日清晨五點開始的新年華會,此次在麥克雷歐崗村共停留了兩個星期。
著手本書的動機,來自達賴喇嘛最近兩次的法國之行。起初,我與巴黎的藏委會代表們聯絡,由於他們的幫助,使一切進行得極為順利。當我回想起此次的旅程,以及成行前多月來一切必須的準備,更加珍惜此次愉悅深刻的回憶。尤其喇嘛廟裡的氣氛,使我感到莊嚴與可親...
此番對話開始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地點為位於印度北方靠近達蘭沙拉的麥克雷歐崗村。更詳細的說,也就是達賴喇嘛居住的泰秦曲陵(意為大乘佛法寺)喇嘛廟內。我於二月十日抵達,剛好趕上藏人在十一日清晨五點開始的新年華會,此次在麥克雷歐崗村共停留了兩個星期。
著手本書的動機,來自達賴喇嘛最近兩次的法國之行。起初,我與巴黎的藏委會代表們聯絡,由於他們的幫助,使一切進行得極為順利。當我回想起此次的旅程,以及成行前多月來一切必須的準備,更加珍惜此次愉悅深刻的回憶。尤其喇嘛廟裡的氣氛,使我感到莊嚴與可親...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我們生活的世界
1末法時期
2真正的力量
3和平的觀點
4不要去碰生氣的人
5普遍性的使命
6妙用活力
7所有的爭吵都是瘋狂的
8真正的天性
9人本一家
10危險的警覺
第二章 教育與汙染
1痛苦的啟示
2回到自己的空間
3沒有事物是分開的
4我們正陷身危機
5提升生命品質
6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7宗教領袖所負的責任
8修正經典的錯誤
9宏觀的思考
10微妙的意識
11探求古老的原因 ...
1末法時期
2真正的力量
3和平的觀點
4不要去碰生氣的人
5普遍性的使命
6妙用活力
7所有的爭吵都是瘋狂的
8真正的天性
9人本一家
10危險的警覺
第二章 教育與汙染
1痛苦的啟示
2回到自己的空間
3沒有事物是分開的
4我們正陷身危機
5提升生命品質
6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7宗教領袖所負的責任
8修正經典的錯誤
9宏觀的思考
10微妙的意識
11探求古老的原因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克勞德.卡列拉 譯者: 洪惠嬌
- 出版社: 華夏 出版日期:2015-04-10 ISBN/ISSN:9789865670405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20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14.8cmx21cm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