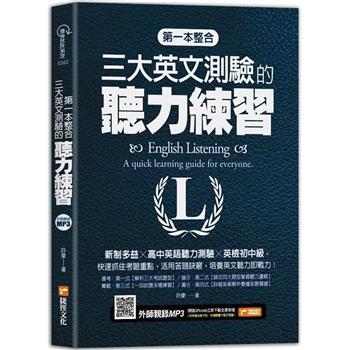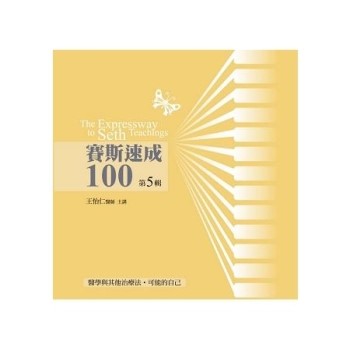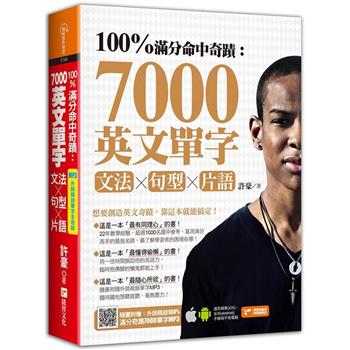高爾基三部曲 高爾基經典勵志巨作
在污濁、黑暗中看到純真、光明;
在邪惡、仇恨中看到善良、溫情;
在無盡的苦難中,找到戰勝苦難的巨大力量。
高爾基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童年》講述的是孤獨孩童「我」的成長故事。小說以一個孩子的獨特視角來審視整個社會及人生。「我」寄居的外祖父家是一個充滿仇恨、籠罩著濃厚小市民習氣的家庭,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家庭。此外小說也展現了當時整個社會的腐敗沒落而趨向滅亡的過程。小說透過「我」幼年時代痛苦生活的敘述,實際反映了作家童年時代的艱難生活,及對光明與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時也展現了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廣闊社會畫卷。
本書特色
《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取材於高爾基的真實成長經歷,主角阿廖沙便是作者「我」。
《童年》講述了「我」自三歲起,在外祖父家度過的苦難童年。
《在人間》講述了「我」十一歲時被外祖父趕出家門,在社會上獨自謀生的坎坷經歷。
《我的大學》講述了「我」十六歲時孤身前往喀山求學,卻在多所「社會大學」裡幾經磨礪,成長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經歷。全書筆調冷峻、凝重,卻不乏幽默、風趣,氣氛有些壓抑、悲傷,卻能使人看到頑強的生命力和不滅的希望。
瑪克西姆‧高爾基是蘇聯著名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蘇聯作家協會的發起人和第一任主席。除小說、戲劇外,還寫有大量文藝理論著作,對多民族蘇聯文有大量文藝理論著作,對多民族蘇聯文學的發展和世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等。列寧說他是「無產階級文學最傑出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導師,蘇聯文學的創始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童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小說 |
$ 252 |
中文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17 |
俄國文學 |
$ 32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