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傷慟是一種霸凌;
有時候,愛國也是。
有時候,愛國也是。
探討「九一一」備受好評的小說,榮獲眾多獎項:
★英國柑橘獎二○一二年初選入圍
★英國《衛報》二○一一年「首作獎」入圍
★美國海明威獎二○一二年「最佳首作小說」入圍
★《紐約時報》二○一一年「年度最受矚目好書」
★《華盛頓郵報》「年度矚目好書」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年度十大小說」
★亞馬遜書店「年度十大首作」暨「年度百大好書」
★邦諾書店二○一一年「年度矚目好書」
在九一一紀念館的隱名競稿決選會議中,經過幾番熱烈討論,
評審選出了一份兼具美與療癒功能的設計圖──《花園》。
就在評審團打開設計者資料時──「上帝啊,他媽的!是該死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可汗」這個名字就像另一顆炸彈,引發了紐約甚至全美國另一場不安與混亂。
●那是療癒人心的花園?還是烈士的天堂?
穆罕默德.可汗是建築師,也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
他只想出人頭地,讓更多人看見自己的作品,也相信自己的設計理念能為人們提供療癒。
然而,紀念館的用意在於安撫人心,是一種國家象徵、一種歷史符號,
由穆斯林建築師設計的九一一紀念館,帶來的是療癒,還是二次傷害?
在同一棵樹下、同一條步道上,它究竟為罹難者家屬提供了撫慰?
還是壯大了伊斯蘭極端份子永世不朽的幻想?
●容忍不是愚昧,偏見才是。
穆罕默德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的國家竟視他為外人;
假如他不是穆斯林,他的設計圖就不會被聯想為烈士天堂。
他拒絕回答設計理念,拒絕證明自己的清白。
他決定打死不退,不想拋頭露面叫賣自己,不願對同胞高喊:「我不可怕……」。
●他們該堅守信念,或屈從於疑懼?
這一切就像一場核爆,幾乎將所有人都捲了進去:
主張紀念館應體現寬容與和平、卻在最後一刻背棄他的評審團家屬代表;
自認能透過筆下文字呼風喚雨的嗜血女記者;
一心想填補遺址空缺、用盡手段勸退穆罕默德的評審團主席;
從反對《花園》興建過程中找到人生新舞台的酗酒男子;
為穆罕默德仗義直言而遭刺殺身亡的非法移民遺孀;
因為他再也分不清野心和原則而選擇離開的律師女友……
他們恐懼、傷痛;他們或歧視或包容,時而相濡以沫,時而彼此傷害。
他們因內心深處種種難以言說的情緒而失控……
這花園如此空靈,寧靜,美麗……
美不是一種罪,它的原罪不是因為美。
推薦者(依姓名筆劃序)
張翠容(香港傳媒人、《中東現場》作者)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楊照(作家、評論家)
蔡康永(作家)
戴立忍(導演)
媒體評論
一部真知灼見的作品,角色複雜,勇於質疑人類動機,正視九一一悲劇而不至於沉入濫情的泥淖……這是一部來得正是時候的小說。九一一事隔十餘年,如今終於能拉長景深,回顧過去、現在、將來的我們。──《美聯社》
沃德曼初入文壇之作敘事明確、筆力強勁,在九一一小說林中獨樹一幟,鼓勵人們反躬自省,並捫心自問九一一之後眾人迴避的一些問題:意識形態與道德觀之間的樊籬何在?歧視與愛國心如何劃清界限?──《新聞週刊》
沃德曼的《穆罕默德的花園》,是一本刻劃複雜心境、呈現社會勾心鬥角的小說,面對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提出痛徹心扉的諸多疑問,深究「美國人」一詞的真諦。──《今日美國報》
《穆罕默德的花園》讓我們與代表各界的角色共處,體會他們個別的處境、團體向心力、野心、心痛,感受這些人如何左右美國民主,讀來令人大呼痛快。──《舊金山紀事報》
文思清晰,發人深省,娛樂性十足……──《紐約時報書評》
《穆罕默德的花園》是一本成就卓絕的小說,節奏、對話、人物、情節從開場就引人入勝……故事以美國民眾辯論議題為主軸,同時痛心疾首暗示,後九一一現象的元凶不是凱達組織,不是小布希,而是大眾傳媒。──《克里夫蘭公論報》
沃德曼過人之處是讓讀者融入對話──生動且衝擊力大的激辯──以巧妙的手法將焦點從九一一轉移至紀念過程,藉由文字推衍,透過她對歷史的敬意──選擇踏上謙卑的文字舞臺表現個人的屈從心──使其小說傲然屹立於歷史中。──《華盛頓郵報》
大師級的處女作……沃德曼在敘事過程中展現資深記者追究真相的膽識,也顯露天生小說家信手拈來的文采。──《娛樂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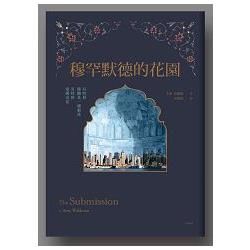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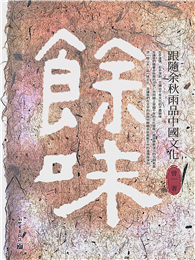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恐怖組織ISIS在法國巴黎發動大規模恐怖攻擊事件,短短幾個小時造成129人死亡,三百多人受傷。幾天後的11月20日,開達聖戰士組織在馬利共和國挾持170名人質七小時,殺死27人。 幾起恐攻事件激怒了全世界,但也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伊斯蘭的仇恨,以暴制暴的腥風血雨氣氛瀰漫全球,不論是被害人還是無端遭到歧視仇視者,他們是無辜的,但我懷疑這世界上願意心平氣和看待他們。 最近剛好出版了這麼一本關於穆斯林遭歧視的小說,我特別從書架上取下本書,從虛構的故事中探索「仇恨心」與「被歧視」之間的界線。 當然故事是虛構的,場景是九一一攻擊事件後,美國打算在世貿遺址重新打造一座足以撫慰亡者靈魂的建築物,基於公平與民主的原則,他們公開舉辦徵求設計圖的活動,評審過程完全不公開設計者姓名資料,評審委員由遺族、政客與專家共同組成,經過審閱了上百份設計圖後,他們一致通過選定了其中一件作品:兼具美與療癒功能的設計圖──《花園》。 沒想到,設計者姓名最後公佈時,全體評審通通傻眼了,設計者叫做「穆罕默德.可汗」,看名字就知道這是一位信奉穆斯林的教徒,後來一查,果真如此,穆罕默德.可汗是中東穆斯林美國移民的第二代。建築師穆罕默德.可汗,投稿的理由和其他件築師一樣,積極向上努力爭取作品曝光機會,他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一輩子只去過阿拉伯世界一次,加上轉機的時間還不到一個禮拜, 「穆罕默德.可汗」這個名字就像一顆炸彈,許多美國人無法忍受讓穆斯林教徒來設計在九一一遺址上的紀念花園,於是各種歧視穆斯林的言論、個人與團體,宛如被喚醒的惡靈,無所不用其極的詆毀設計者,另一方面,部份美國人則認為應該維持美國開國以來的包容文化與精神,接受由穆斯林建築師來設計九一一遺址。 一件單純的建築比圖事件卻引發了大規模的反穆斯林運動,遺族中的有心人士藉此興風作浪,藉操弄民粹博取民調支持的政客,為求獨家新聞不顧新聞倫理甚至人身安全的新聞記者,跟著搧風點火的穆斯林團體,中東地區的恐怖份子…..都企圖藉由此事來謀圖私利,事情的演變越來越不單純。 誠如本書的原文書名Submission(屈服),穆罕默德.可汗會不會在巨大壓力下屈服?相反地,評選委員們會不會屈服在各方壓力之下,自然成為本書表面上的衝突亮點。 但我卻以為,本書內容最根本的核心應該是「價值與尋根」以及「救贖與超脫」,對自己宗教與血緣完全沒有認同的穆罕默德.可汗,他一步步找到屬於伊斯蘭文化的自我,那些九一一亡魂的遺族們,能否超脫極端仇恨心而尋求真正的救贖,才是本書最精彩的部份。 另外還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世貿大樓中唯一伊斯蘭亡者的遺孀,沒有居留存的她抱持著什麼樣的美國夢從孟加拉跟隨丈夫非法移民到美國?丈夫的死到底要怪罪命運還是要怪罪同屬伊斯蘭教的恐怖份子?對於「穆罕默德花園」爭議,美國捲起歧視穆斯林教徒,被受困腦的無辜者,又該如何自處?是跟著極端團體起身捍衛伊斯蘭信徒在美國的基本人權?還是自私自利地抱怨起那個無謂挑起爭端的建築師或建築物? 本書是作者的處女作,多少在某些角色的心境轉折,不是過於繁瑣,不然就是過於急促,某些橋度也寫得過於熱鬧或矯情,但..瑕不掩瑜啦!Submission告訴了讀者一切的答案,但歐美世界所有人難道都會遷怒99.9999%的無辜善良伊斯蘭教徒嗎?我相信不會!也希望不會!但現實局勢似乎不一定會朝樂觀的方向行進,我們所信奉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與人權、同理心,會不會面臨被質疑甚至面臨崩壞的邊緣呢? 這本書不會告訴讀者這些,大概也沒人能夠回答,只是在此時此刻,恐佈攻擊與仇視穆斯林兩股力量已經慢慢撕裂出普世價值的些許裂痕,讀這本書格外會讓我得到許多省思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