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老派探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老派探戈 作者: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 / 譯者:葉淑吟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15-11-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77 |
小說 |
$ 357 |
小說/文學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西葡語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西班牙熱銷30萬冊
◎空降西班牙《ABC報》排行榜亞軍
◎西班牙網路書店書屋網(Casa del Libro)讀者評價四顆星
◎版權已售美、法、德、義、荷等23國
1928年,富有的西班牙作曲家阿曼多帶著年輕貌美的妻子梅嘉,搭乘豪華輪船遠渡重洋來到阿根廷,尋找探戈的原貌:「老派探戈」。一名在船上專門陪貴婦名媛跳舞的英俊舞者馬克斯,成為他追尋老派探戈的嚮導。然而,馬克斯與梅嘉卻因為一曲沒有伴奏的探戈,滋生了曖昧的情愫。
他們三人在阿根廷的貧民區酒館裡,見識了原汁原味的老派探戈,也陷入一場愛慾糾纏。不久之後,馬克斯偷走梅嘉價值非凡的珍珠項鍊遠走高飛,原來他不僅是個社交舞男,也是個專門竊取貴婦財物的小偷。
時隔九年後,馬克斯和梅嘉在蔚藍海岸重逢,彼時正逢西班牙內戰,阿曼多在獄中生死未卜,梅嘉則流亡法國等待戰事停歇。馬克斯依舊靠昔日手段維生,不料卻因此被義大利與西班牙的政府密探盯上,捲入涉及國家陰謀的間諜活動。他身負機密文件和命案,只能再度與梅嘉分別。
又過了近三十年後,人生歷經坎坷的馬克斯流落義大利淪為私人司機,再度意外地遇到梅嘉,兩人相互糾葛的宿命,將在1966年寫下句點。此時梅嘉卻要求馬克斯為了她的天才棋手兒子重操舊業……
*「老派探戈」源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阿根廷與烏拉圭交界銀河兩岸,本為中低下階層移民娛樂的舞蹈。1920年代傳到歐洲之後,經過改良發展成「新派探戈」,舞姿優雅,廣受上層社會名流喜愛。
貝雷茲-雷維特這次寫了一個頗具懷舊時代色彩、浪漫又哀傷的愛情故事。本書一開始寫於1990年,直到2012年才完成,作者認為自己有了不同的目光,長了白髮和皺紋,才有辦法完成小說。他耗時兩年考據資料,讀者一致認為角色刻劃入微,寫作功力尤勝《大仲馬俱樂部》和《法蘭德斯棋盤》,特別是男女主角間簡短卻觸動心弦的對話,經典而寫實。
作者簡介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原為新聞工作者,在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有九年擔任戰地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在戰火前線從事報導,成了西班牙家喻戶曉的新聞英雄。其豐富的報導經驗,培養了他敏銳的洞察力和飛快的寫作速度。自1986年推出處女作《輕騎兵》以來,他出版過十九部長篇小說,以及一系列以「阿拉特里斯德隊長」為主角的歷史冒險小說,是當代西班牙最暢銷、被譯成最多國語言的作家,作品全球銷量超過一千萬冊。
2003年他當選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2008年的小說《戰爭畫師》更獲得義大利的Vallombrosa Gregor von Ressori最佳翻譯小說大獎。其作品不僅完美結合文學內涵、閱讀娛樂和藝術高度,且每每穩居排行榜之列,更贏得讀者和評論家一致喜愛。稱他是西班牙「國民作家」,絕不為過。
譯者
葉淑吟
大學西語系畢業,喜愛拉美文學。譯有《謎樣的雙眼》、《南方女王》、《海圖迷蹤》、《風中的瑪麗娜》、《愛情的文法課》、《12神探俱樂部》、《時空旅行社》、《黃雨》等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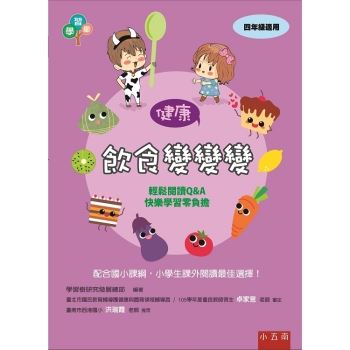







比起美英日本,西班牙小說對我有股難以抗拒的誘惑,如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卡洛斯.魯依斯.薩豐(風之影三部曲)、伊德方索.法康尼斯(Ildefonso Falcones海上教堂作者ˋ)、安立奎.莫瑞爾(沒有時間的城市)….等等,西班牙拉丁風格的作品對我而言,有豐富層次的感情,毫無隱晦的直白,濃厚的歷史感等優點。 我稱得上是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的忠實讀友,包括本書在內,一共讀過八本在台灣發行的繁體中文譯本(當然他的作品不只有這八本),從《法蘭德斯棋盤》、《大仲馬俱樂部》、《聖堂密令》、《海圖謎蹤》、《南方女王》《戰爭畫師》到《擊劍大師》。他以往的作品多半融合歷史、宗教、戰爭、藝術與推理元素,將個人的博學知識和懸疑情節連結到古書收藏、祕教崇拜、藝術修復、棋局爭鋒甚至古航海圖庫等主題。然而到了後期,我個人認為他有點技窮,如2006年出版《戰爭畫師》就顯示出有些千篇一律,主角不小心捲入風暴,藉由古書古籍或宗教歷史的考證,很強悍且很睿智地冒險氾濫解開謎團…..我想他也思考過這些創作困境,所以他一直磨了六年多到2012年才出版本書《老派探戈》。 《老派探戈》的風格一掃昔日的創作模式,主角再也不是出神入化的印地安那瓊斯,內容再也不是達文西密碼之流的解謎公式,冒險與解謎的領域變成愛情,或許全世界最危險、最難解謎的正是愛情吧。很高興,自己喜歡的作者能夠自我突破,繼續帶著粉絲朝不可測的創作天地冒險。 這是一本徹徹底底的愛情小說,主角不再飛天鑽地,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痞子騙徒,專門靠自己的舞技與帥氣的外表談吐,欺騙有錢女人的財富。 主角馬克斯是個職業探戈舞男,在舞池中,他總能完美地抓住節拍,靠著精明機伶,談吐得宜,對答如流,外表光鮮獲得女人的景仰。他除了在舞廳靠探戈賺錢糊口外,他用舌粲蓮花以及善用沉默妝點憂鬱氣質的本領騙取出身上流階層有錢女人的珠寶或金錢,他甚少失手,不管是什麼年紀女人,不管是在皇宮、麗池酒店、蔚藍海岸的露天廣場,或者在輪船頭等客艙的舞廳,他都能騙光女人的錢,後用漫不在乎的神情用口哨吹著〈蒙地卡羅賭場大贏家〉(The Man Who Broke the Bank at Monte Carlo)迅速逃離,到下一個行騙處尋找下一個上流階層的女肥羊。 角色設定讓我感到新穎,催促著自己迫不急待地捧著書一頁頁地讀下去,厭倦英雄的我,還蠻喜歡這種痞子騙徒。 女主角梅嘉則是不折不扣的上流階層女人,她藉由聰明的婚姻攀上枝頭,不論是作曲家之妻還是外交官遺孀。 兩人在輪船頭等客艙的舞廳相遇,藉由探戈升溫了兩人之間的危險情愫。整個故事訴說著兩人四十多年之間僅有的三段邂逅-重逢,兩人之間鄉處得時間很短,第一段是兩人跟著梅嘉的作曲家老公到阿根廷取材,尋找原始庶民粗鄙的老派探戈音樂。第二段蔚藍海岸的重逢則是馬克思捲入政治事件。第三段重逢則在初識的四十年後,兩人都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此時梅嘉卻要求馬克斯為了她的天才棋手兒子重操欺騙與偷竊的舊業。 從二十歲到六十歲,終其一生只短暫相遇三次的男女,經由一首老派探戈的歌曲牽繫著整個人生。 故事的結構很簡單,很懷舊,字行行間有股讓人化不開的幽幽傷感,作者為了劇情精彩,加了探戈這個元素,一邊閱讀一邊找點探戈音樂聽聽,更能增添閱讀的想像空間。當然作者還加入了棋局、西班牙內戰、海洋等他擅長的時空,和以往的作品不同,除了探戈以外,那些時空因子完全屈居配角,不會干擾到本書的主軸-愛情。 我不知道女讀者會不會喜歡這樣的愛情故事,但我敢打包票,《老派探戈》肯定是本男人愛看的愛情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