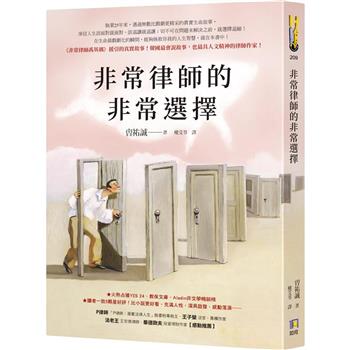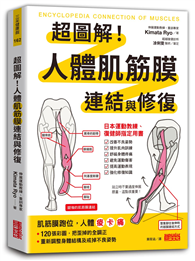莫名成為貴妃的姬小小雖然過著每天遭人挑釁的後宮生活,但憑藉著無人能敵的武功,這日子倒也過得十分隨性。
無聊逗逗眾人之餘,她便上江娘娘的蘭陵宮串串門子、聊聊八卦。沒想到兩個「妃子」的要好卻讓好不容易動了心的皇帝吃起了飛醋,這原因為何大概也只有他自個兒心知肚明……
獨自生悶氣的皇上只好多多「寵幸」江娘娘讓她無暇顧及他人,害得被冷落的姬小小只好又默默開始了後宮的冒險。在打怪的路上她捕獲了一名面容可怖、言談行為極其怪異的女子。姬小小甚麼大場面沒見過,自然不會將她古怪的行徑看在眼裡,女子也被姬小小無厘頭的行為搞得不明所以,感覺自己被黏上了一顆橡皮糖。
但日子久了女子也漸開心房,對著唯一的知心好友吐露了她過往的身分──其實她不是甚麼妖女,她是過去艷冠後宮、又溫柔賢德的蕭賢妃,也是玄墨真正喜歡過的女人……
就、就算玄墨過去喜歡妳,現在,他可是我的人了!
【人物簡介】
姬小小:點蒼山天機老人排行最末的弟子,個性嬌憨活潑,武功強大,卻是個不諳世事的少女。心直口快,亦不懂掩飾做作,對待自己人很是真心。
凌玄墨:真實身分為魏國元帝,亦是眾人眼中逆來順受的傀儡皇帝。然而他早已暗中部屬,準備伺機奪回實權。雖然對小小的行徑也感到頭大,卻發現離不開對方的人竟然是自己,頗有受虐體質。
玄塵:居住於宮中竹林的神秘青年。五官清秀出塵,氣質宛若謫仙,靜謐似水,擅彈古琴。喜歡小小的天真不做作,總是用美食誘惑她來拜訪。
金香玉:玉生香客棧老闆,玄墨的手下,平時女扮男裝,英氣勃勃,舉手投足很有幾分俠士之氣。化名為金玉。
江晚月:蓬萊閣三閣主,身段修長,人間絕色,亦為玄墨手下。為增進內力而修練東瀛異術,卻瀕臨反噬邊緣。
劉鑒雄:魏國攝政王,皇后的舅父,手中擁有全國的六成兵力和一支訓練有素的黑旗軍,是目前真正管理魏國的主事者。
本書特色
★暢銷人氣作家‧二分之一A 繼《家有鹹妻》後最新歡樂力作
★橫掃紅袖添香各大排行榜/一品紅文館必讀佳作!總點擊數超過600萬次!
★知名同人繪師‧瓔珞跨刀封面繪製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逗比姑娘闖君心【卷二】笑鬧驚宮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5 |
二手中文書 |
$ 180 |
小說/文學 |
$ 198 |
古代羅曼史 |
$ 220 |
中文書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言情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逗比姑娘闖君心【卷二】笑鬧驚宮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二分之一A
一枚愛看雜書的女子,是書就行,來者不拒。
聽說寫小說的都是雜家,技藝不精,半桶水晃蕩,故而在某日提筆疾書完成第一本網路小說之後愈發不可收拾。一路寫來已有七八年,喜歡江湖恩仇,喜歡宮闈愛恨,喜歡麻雀變鳳凰,喜歡大女子霸道溫柔男主。
希望我喜歡的,也是你喜歡的,只消有一個讀者還在看我的書,我必將生命不止,寫書不止。
繪者簡介
瓔珞
漫畫家,插畫家。
是一個大部分時間在畫古風爆笑漫畫,小部分時間很開心的畫自己喜歡的唯美古風插畫作者。
缺點是沒有茶和古風音樂就畫不出圖~~
本體是一隻圓圓的小黃雞。
二分之一A
一枚愛看雜書的女子,是書就行,來者不拒。
聽說寫小說的都是雜家,技藝不精,半桶水晃蕩,故而在某日提筆疾書完成第一本網路小說之後愈發不可收拾。一路寫來已有七八年,喜歡江湖恩仇,喜歡宮闈愛恨,喜歡麻雀變鳳凰,喜歡大女子霸道溫柔男主。
希望我喜歡的,也是你喜歡的,只消有一個讀者還在看我的書,我必將生命不止,寫書不止。
繪者簡介
瓔珞
漫畫家,插畫家。
是一個大部分時間在畫古風爆笑漫畫,小部分時間很開心的畫自己喜歡的唯美古風插畫作者。
缺點是沒有茶和古風音樂就畫不出圖~~
本體是一隻圓圓的小黃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