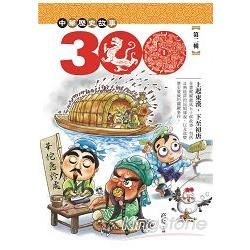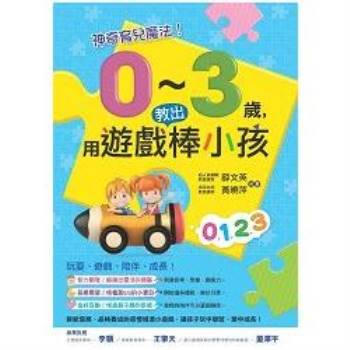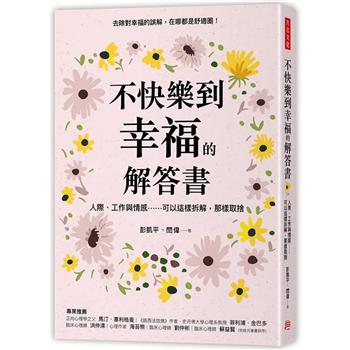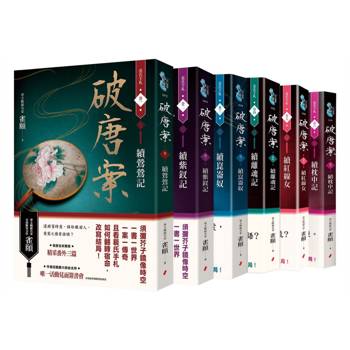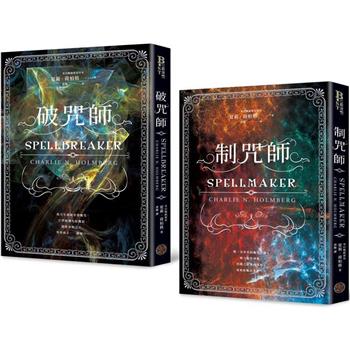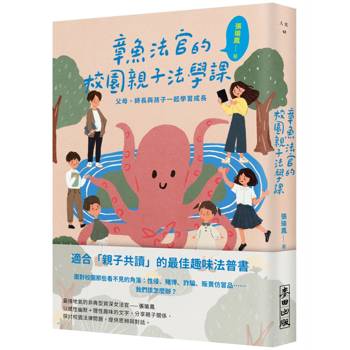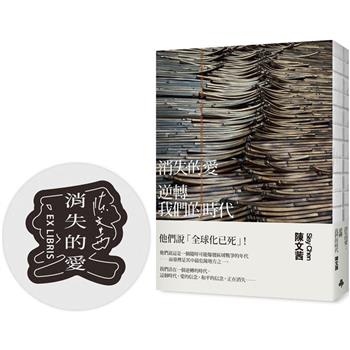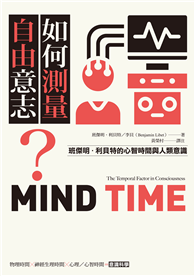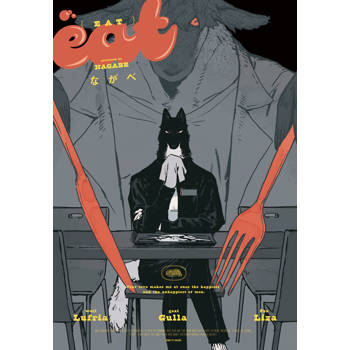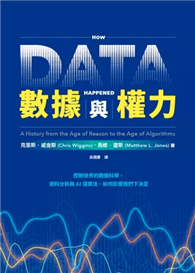外戚專政
東漢和帝之後,天不假皇帝之年,均為幼帝即位,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沒有的怪事。小孩子能懂什麼事?導致大權輪番落入外戚、宦官手中。
西元八十八年,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權落入其兄竇憲之手。直到西元九十二年,年紀稍長的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逼迫竇氏兄弟自殺,竇家宗族全部免官治罪。就這樣,外戚竇氏的勢力全部剷除,宦官得以直接參政。
西元一○六年,和帝去世,鄧太后立劉隆為帝。殤帝劉隆出生才一百多天,還在吃奶,等他長大親政,那還早著呢!劉隆長到一歲多,小命就歸了黃泉。國不可一日無君,鄧太后又立十三歲的安帝劉祜。
鄧太后臨朝,外戚鄧騭兄弟顯赫一時,鄧騭即使打個噴嚏,朝堂也要震一震。鄧騭有鄧太后做靠山,作威作福了十多年。西元一二一年鄧太后去世,二十多歲的安帝血氣方剛,不願做鄧氏傀儡,他與乳母王聖、宦官李閏等合謀,將鄧氏廢逐。
安帝掌權後,吸取了前朝宦官把持朝政的教訓,除了重用宦官外,同時重用皇后的哥哥閻顯等掌管樞要。他想以宦官、外戚互相牽制,以求太平無事,一時間,出現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實際上,外戚、宦官各懷鬼胎,都想伺機將對手攆下臺。
西元一二五年三月,安帝在巡遊途中病死。皇后和她哥哥閻顯祕不發喪,急急忙忙趕回京城立幼童北鄉侯劉懿為君,由閻太后臨朝執政。
閻顯得勢不饒人,把安帝寵信的宦官下獄處死,將王聖母子流放雁門,這下子閻顯成了炙手可熱的權貴。
閻顯獨攬大權的日子最短。同年十一月,北鄉侯劉懿病卒。閻顯知道大事不妙,又採用了祕不發喪的老辦法,屯兵宮中自守。
皇宮裡的事無法瞞得住宦官。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濟陰王劉保為帝,閻顯兄弟沒能逃脫大難,被抓了起來關在獄中死去。十一歲的順帝劉保任憑宦官擺布,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孫程等人好夢不長,第二年八月就因爭功被有司彈劾,被免去官職,遣返自己的封地。西元一二八年,順帝召孫程等人回洛陽,宦官的勢力得以東山再起,西元一三二年正月,順帝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從此以後,梁氏勢力漸漸興起。
東漢時期,外戚勢力最盛的要數梁冀。自西元一四一年被任命為大將軍後,把持朝權將近二十年之久。
西元一四四年,順帝去世,兩歲的沖帝即位。梁太后臨朝,梁冀更是有恃無恐。沖帝也是個短命皇帝,第二年正月便離開了人世。梁冀立即採取行動,立八歲的劉纘為質帝。
梁冀本想將質帝玩弄於股掌之上,沒想到質帝劉纘少而聰慧,看不慣梁冀驕橫跋扈,當著群臣的面說他是「跋扈將軍」。梁冀聽了吃驚不小:小小的年紀就有這麼大的膽,長大了豈不是要吃了我梁冀!梁冀隨即下了毒手,下毒殺害了質帝,並將正準備和自己妹妹結婚的蠡吾侯劉志推上帝位。
這時候,皇太后、皇后都是他的妹妹,他說的話誰敢道聲「不」字?桓帝劉志雖對梁冀甚為不滿,但不敢有任何表示,宮中有梁太后、梁皇后,朝廷有梁冀,他縱有天大的怨氣,也沒有地方發洩。
梁冀專政期間,誰要是敢跟他過不去,那麼那個人的死期將近。有個十九歲的青年,名叫袁著,他見梁冀橫行不法,到皇宮門前向皇帝上書告發。梁冀知道後火冒三丈,派人去逮捕袁著。袁著知道自己闖下了滔天大禍,改名換姓躲了起來。抓不到袁著,梁冀不肯罷休,派人到處搜索,袁著假裝病死,叫家人用蒲草紮了個屍體放在棺材裡入葬。梁冀聽說袁著病死,不禁起了疑心,年紀輕輕的,怎麼說死就死?他派人開棺驗屍,果然有詐,他派人四處搜查,終於將袁著逮住。梁冀下令用刑,將袁著活活打死,袁著的許多親朋好友受到株連,遇害的多達百人。
不僅百姓遭到梁冀的荼毒,就連朝廷官員也不能違背他的意志。下邳人吳樹出任宛縣縣令,臨行前向梁冀辭行。梁冀的親朋好友多在宛縣,所以要吳樹多加關照。吳樹到任後發現這些人都是些貪得無厭、魚肉百姓之徒,於是,連殺民憤極大的惡棍十多人。梁冀得知後怒火中燒,伺機報仇。後來吳樹調任荊州刺史,梁冀請他到府中做客。梁冀設下酒宴,假意為吳樹餞行,暗中命人在酒中下毒。吳樹喝了毒酒,剛出梁府大門就毒發死在車中。
朝廷官員對他無不畏忌,就連桓帝劉志也在他的掌握中。皇帝的近侍都是梁冀的親信,劉志的一言一行每天都有人向他報告。桓帝劉志對他極為不滿,卻又無可奈何。
西元一四八年三月,桓帝隨同梁太后親臨大將軍府。這是何等風光,梁冀更成了朝廷不可一世的人物。桓帝滿腹不快,卻也不敢流露出半點跡象來。
在梁冀專政的二十年裡,外戚的勢力達到頂峰。梁氏前後有三人做皇后,六人為貴人,兩人做大將軍,七人封侯,三人娶公主為妻,女眷中有七人食邑稱君,各級將領多達五十七人。這是東漢時代任何一家外戚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可謂氣焰熏天。
盛極必衰,梁氏也逃不脫這個定律。西元一五○年正月,年老病重的梁太后不再臨朝,還政於桓帝。桓帝終於鬆了口氣,為奪回大權積極作準備。同年二月,梁太后病卒,壓在桓帝頭上的大山終於倒塌。時隔不久,梁皇后去世,梁冀失去了宮中的另一條臂膀。
與梁冀水火不相容的桓帝終於下手了。西元一五一年正月,不知收斂的梁冀帶劍入宮,被尚書張陵彈劾。西元一五九年,桓帝見時機已經成熟,與自己的親信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謀,發動宮中衛兵一千多人,趁梁冀無備突然包圍了大將軍府。
梁冀萬萬沒有想到一直捏在自己手心裡的桓帝會突然發難,頓時嚇得不知所措。過了片刻,他清醒過來,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便和妻子孫壽雙雙懸梁自盡。皇宮衛兵衝了進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到一個時辰,把他家的男女老少殺了個精光。接著查抄梁冀家產,竟然多達三十多億兩白銀,這樣的巨額,相當於朝廷全年租稅收入的一半。
樹倒猢猻散。梁冀一死,梁氏所有的內親外戚一律被捕處死,朝廷大員因受牽連而被治罪的有幾十人,梁冀的舊屬賓客有三百多人被罷了官,梁氏的勢力一下子被剷除乾淨。
剷除了梁氏,官吏百姓無不額手稱慶。不過,之後又出現了宦官專權的局面,東漢政權也走上了沒落的道路。
黨錮之禍
東漢和帝以前,宦官是被人看不起的人物,他們只不過是皇宮裡的奴才,一切都要看皇帝、皇后的臉色行事。
和帝迫殺外戚竇憲,宦官鄭眾參與謀劃,事成後受到重用,被封為列侯。這是宦官弄權的開端,和帝實為始作俑者。
和帝以後,幼帝不斷,掌握朝權的或為外戚,或為宦官。成年後的皇帝與擅權外戚進行奪權,往往依靠宦官勢力,皇帝在奪權取勝後,宦官便挾功自重,形成新的專權集團。在很長一段時期裡,外戚專政與宦官弄權的局面交替出現。
桓帝誅除梁冀,外戚勢力衰微,宦官單超等五人參與謀劃有功,同日封侯。單超等人趁機弄權,組成了強大的統治集團,這就是後世所說的「五侯專政」。
這些宦官不僅把持了朝權,有的甚至娶姬妾、蓄養子,傳爵襲封。他們的親戚依權仗勢橫行鄉里,簡直與盜賊無異。人們漸漸發現,宦官弄權比外戚專政更壞。
那時候,不少官員不滿宦官當權,主張改革朝政罷斥宦官;許多太學生因為宦官專政沒了出路,也議論朝政要求改革。一時間議論紛紛,討論時政,品評人物,抨擊宦官,後世稱之為「清議」。世家豪族這時也行動起來,壯大了反對宦官的聲勢。其中河南尹李膺、太尉陳蕃名氣最大,最有號召力。以郭泰、賈彪為首領的太學生對他倆十分崇敬,太學裡流傳著「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字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仲舉)」的歌謠。
西元一六五年,李膺任司隸校尉。有人前來告狀,野王縣令張朔貪贓枉法,強搶逼殺民女。
張朔是宦官張讓的弟弟。張讓專門負責皇宮內外諸事,被封為列侯,張朔靠著哥哥的權勢,當上了縣令。他稱霸一方,幹盡了壞事,現在犯了法,逃到洛陽躲在哥哥張讓家裡。
李膺帶著公差來到張讓府邸,看到門前有幾名彪形大漢守衛。李膺一身正氣,帶著差役往裡闖。衛士見了司隸校尉,不敢阻攔,只得放他們進去。李膺命差役搜查,終於在夾牆裡搜出了張朔,他斷喝一聲,命差役將張朔帶走。李膺怕節外生枝,連忙對張朔進行審訊。他迅速將案情審清,立即將張朔處死,等到張讓託人前來求情,張朔已經人頭落地。
張讓在宮中聽到弟弟被殺的消息,連忙到桓帝面前哭訴。桓帝知道張朔確實有罪,李膺沒有殺錯人,要是偏袒張讓追究李膺,會引起官吏百姓的共憤。桓帝也沒責怪李膺,張讓反倒碰了一鼻子灰。
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誅殺張朔,震動了朝廷內外。宦官們收斂了許多,不敢再像過去那樣縱容親屬胡作非為。他們在皇宮內裝出循規蹈矩的樣子,節日也不敢邁出皇宮大門。桓帝對此感到很奇怪,將宦官們召來相問,宦官們一齊叩頭哭訴道:「李膺執法嚴明,對我們毫不留情。我們怕他,連門也不敢出。」
李膺的聲名大噪,讀書人對他十分崇敬,許多讀書人都想見一見李膺,一睹他的風采,要是有人受到李膺接見,被視為極其光榮的事,人們稱之為「登龍門」。
第二年,方士張成占卜得知朝廷馬上就要大赦,便縱容兒子去殺人。李膺馬上將兇手抓起來,準備依法懲治。這時候,大赦令頒布,張成洋洋得意的對別人說:「大赦詔令已下,司隸校尉不得不把我的兒子放出來。」
這話傳到李膺的耳朵裡,使他火冒三丈,說:「張成預知將要大赦,唆使兒子殺人,皇上大赦,也輪不到他兒子身上!」他立即下令,將張成的兒子斬首。
這下子宦官們找到了藉口,趁機誣告李膺勾結太學生和名士,說他們大肆誹謗朝廷。桓帝信以為真,下令逮捕黨人。根據宦官開出的黑名單,一下子逮捕了兩百多人。
陳寔是位有名望的太學生,也在黑名單之列,有人勸他趕快逃走,他卻激昂的說:「我一走了之,別的人怎麼辦?我進了監獄,也能給別人壯壯膽。」他來到京城,投案入獄。
宦官對被捕的黨人進行殘酷折磨,在他們的頭頸、手、腳都戴上刑具,稱作「三木」,然後蒙上他們的頭嚴加拷打,要他們承認自己的罪行。
李膺毫不屈服,在審訊時當眾揭露宦官的種種罪行,宦官面面相覷,彷彿他們成了犯人。在這緊要關頭,竇皇后的父親竇武站到了黨人一邊,他和尚書霍諝聯名上書給桓帝,請求赦免黨人。宦官也怕把事情鬧得太大對自己不利,勸桓帝赦免黨人。桓帝來了個順水推舟,將兩百餘名黨人赦免釋放,把他們遣返老家,禁錮終身不得再任官職。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西元一六七年十二月,桓帝去世,竇太后臨朝,立十二歲的劉宏為帝。竇太后執政,竇武得勢,他和陳蕃商量了一番,解除了對黨人的禁錮令,並將李膺等人請出來,繼續擔任官職。
宦官們見李膺等回到京城,立即緊張的活動起來。竇武、陳蕃為了剷除宦官勢力,企圖用武力誅殺宦官。可惜消息走漏了出去,宦官曹節、王甫等人先下手為強,挾持了漢靈帝劉宏,逼迫他下詔逮捕竇武。竇武不願束手就擒,發動駐京的北軍討伐宦官,結果北軍被虎賁軍、羽林軍擊敗,竇武自殺,陳蕃被殺害。宦官們見竇武死了,覺得還不能解心頭之恨,命人將竇武的腦袋割下來,掛在城頭上示眾。宦官們又將逃出去的竇家人全部捕殺,竇武的親信、朝中與竇武關係密切的大臣都慘遭毒手,朝廷內外遇難者多達百人。
第二年,宦官曹節等為清除竇氏勢力,製造了第二次「黨錮之禍」。他們指使爪牙朱並上書,控告黨人張儉和他同郡的二十四個黨人謀反。除了張儉逃脫外,其他的人都被捕獲。接著,曹節奏請靈帝逮捕李膺等一百餘人,幾天之後,便將這些黨人殺害。
宦官們心狠手辣,幾天工夫就殺害、流放、監禁了六七百名黨人,凡有為黨人鳴冤叫屈的,也都抓起來殺害。曹節覺得太學生是心腹之患,將一千餘名太學生全部關押起來。
西元一六九年,宦官又以靈帝的名義下詔,凡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並遠及五族,有官位的一律免官,禁錮終身。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兩次「黨錮之禍」以後,朝廷的大權被宦官完全控制。東漢開始一天天沒落,一步步走向滅亡。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4 |
科學科普 |
$ 211 |
少兒知識家 |
$ 211 |
少兒知識家 |
$ 216 |
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華歷史三百故事(2)
歷史如同人生,關鍵只有幾處,卻精彩十足。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擷取歷史長河中的重要事件,以說故事的方式,敘述300則精彩史實,介紹300位鮮活人物。讓讀者懷著有趣的心情,親切觸摸燦爛的文化,感受歷史的滄桑。不用強記死背,也能建立完整的歷史認知架構。
作者考證大量史料,嚴謹根據史實,再透過巧筆,讓故事裡的人物彷彿重新活了起來,藉著栩栩如生的對話,細膩描繪的場景,帶領讀者跨越時空,親臨歷史現場。
全套書格局恢弘,嚴謹中不乏鮮活,篇篇精彩、字字精煉,希望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感受,並從中獲益。
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分天下,繼之而起的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一段時期。然而,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卻也寫下了最精彩的歷史一頁。在這段時期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諸葛亮七擒孟獲;也有看謝安談笑用兵,運籌帷幄以少勝多,奠定東晉偏安之局。也正是這樣的亂世,讓眾家好漢大展身手,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個人風采。
本書就以這段波瀾萬丈、驚心動魄的歷史為背景,精選出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將這精彩動人的時代如實的呈現在讀者面前。
章節試閱
外戚專政
東漢和帝之後,天不假皇帝之年,均為幼帝即位,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沒有的怪事。小孩子能懂什麼事?導致大權輪番落入外戚、宦官手中。
西元八十八年,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權落入其兄竇憲之手。直到西元九十二年,年紀稍長的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逼迫竇氏兄弟自殺,竇家宗族全部免官治罪。就這樣,外戚竇氏的勢力全部剷除,宦官得以直接參政。
西元一○六年,和帝去世,鄧太后立劉隆為帝。殤帝劉隆出生才一百多天,還在吃奶,等他長大親政,那還早著呢!劉隆長到一歲多,小命就歸了黃泉。國...
東漢和帝之後,天不假皇帝之年,均為幼帝即位,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沒有的怪事。小孩子能懂什麼事?導致大權輪番落入外戚、宦官手中。
西元八十八年,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權落入其兄竇憲之手。直到西元九十二年,年紀稍長的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逼迫竇氏兄弟自殺,竇家宗族全部免官治罪。就這樣,外戚竇氏的勢力全部剷除,宦官得以直接參政。
西元一○六年,和帝去世,鄧太后立劉隆為帝。殤帝劉隆出生才一百多天,還在吃奶,等他長大親政,那還早著呢!劉隆長到一歲多,小命就歸了黃泉。國...
»看全部
目錄
外戚專政
黨錮之禍
黃巾起義
董卓之亂
小霸王稱霸江東
官渡大戰
赤壁鏖兵
華佗行醫
關羽大意失荊州
彝陵之戰
七擒孟獲
五丈原兩軍對峙
司馬氏代魏
晉軍滅吳
楊駿專權遭慘禍
諸侯王爭權大亂
成都王敗失鄴城
東海王奪得大權
匈奴建漢滅西晉
中流擊楫壯志未酬
晉明帝平叛
劉曜醉酒亡前趙
書聖王羲之
淝水之戰
桓溫奪權未果
司馬道子亂朝綱
劉裕建宋代晉
元嘉宋魏大戰
劉劭弒父起禍端
南齊禦魏
北魏孝文帝改制
魏梁鍾離大戰
河陰之亂
侯景叛東魏
潁川大戰
王琳反陳兵敗
陳軍收復淮南
宇文邕滅北齊
長孫...
黨錮之禍
黃巾起義
董卓之亂
小霸王稱霸江東
官渡大戰
赤壁鏖兵
華佗行醫
關羽大意失荊州
彝陵之戰
七擒孟獲
五丈原兩軍對峙
司馬氏代魏
晉軍滅吳
楊駿專權遭慘禍
諸侯王爭權大亂
成都王敗失鄴城
東海王奪得大權
匈奴建漢滅西晉
中流擊楫壯志未酬
晉明帝平叛
劉曜醉酒亡前趙
書聖王羲之
淝水之戰
桓溫奪權未果
司馬道子亂朝綱
劉裕建宋代晉
元嘉宋魏大戰
劉劭弒父起禍端
南齊禦魏
北魏孝文帝改制
魏梁鍾離大戰
河陰之亂
侯景叛東魏
潁川大戰
王琳反陳兵敗
陳軍收復淮南
宇文邕滅北齊
長孫...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舒
- 出版社: 龍少年 出版日期:2015-03-05 ISBN/ISSN:97898656904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2頁 開數:14.8*21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知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