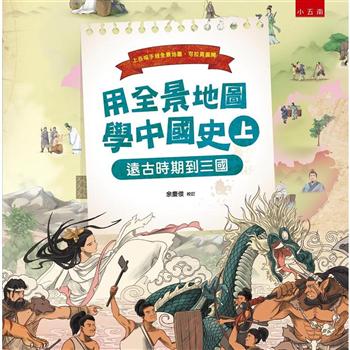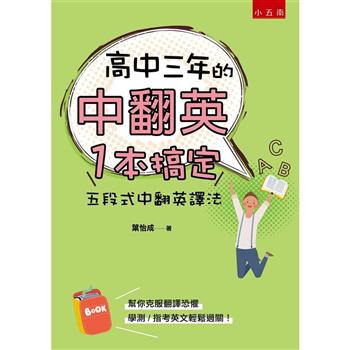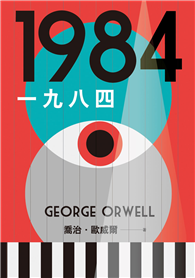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企業風雲的圖書 |
 |
企業風雲-成功啟示錄 作者:薛聖東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4-05-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4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350 |
小說 |
$ 395 |
中文現代文學 |
$ 440 |
大眾文學 |
$ 440 |
大眾文學 |
$ 450 |
小說 |
$ 450 |
現代小說 |
$ 450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50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企業風雲
本書通過主人公任信良出任上市企業──濱洲創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前後的故事,描寫企業經營者於現代商場、官場、情場之中,官商、商商、男女之間的交易與交換,以及在追求成功的中痛苦與迷茫、矛盾與折磨,展開了一場現代商場、官場、情場上的楚河漢界、明爭暗鬥與波詭雲譎。
生與死、榮與辱、正與邪的較量,官與商、商與商、男與女之間的交易與交換,一場又一場陰謀與奸詐寫實上演。
企業風雲,誰主沉浮?敏感深刻的主題,隨著主人公命運的起伏,呼之欲出,令人深思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