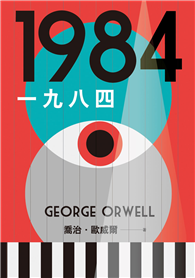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靜靜的紅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50 |
小說 |
$ 395 |
大眾文學 |
$ 440 |
小說 |
$ 440 |
小說 |
$ 450 |
小說 |
$ 450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50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靜靜的紅河
靜靜的紅河,孕育善感的年輕生命,將他推向渾濁而沉痛的現實。生於越南紅河畔的華裔家庭,純潔而敏銳的青年范聖珂,注定要在思索生命意義的青春歲月,遭遇近代東亞的一連串劇變──日軍侵越、八年抗戰、法越戰爭……他隻身從故鄉投向祖國的抗日戰役,在中緬邊競度過地獄般的戰鬥;他帶著額前的傷疤,迎接一無所有的勝利復員。他始終徘徊在愛情、認同、理想的落差與矛盾中,無力掌握身邊人的、情感的、時代的瞬息萬變。隨著理想的破滅與重建,他終於看清那折磨生命、又為生命帶來歡欣的,就是他始終對自由的渴望。
這部原為三部曲的小說,是潘壘最為壯闊、最為切身的第一部作品,以自身顛沛的青春經歷,寫出純潔理想在殘酷現實中的沉淪,更是近代東亞戰爭中極為寫實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