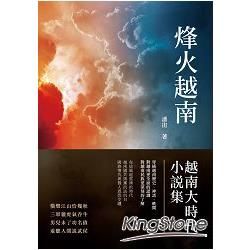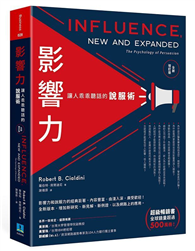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烽火越南:越南大時代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96 |
小說 |
$ 221 |
中文書 |
$ 221 |
現代翻譯文學 |
$ 238 |
社會人文 |
$ 246 |
其他各國文學 |
$ 246 |
Others |
$ 252 |
小說 |
$ 252 |
世界現代文學 |
$ 252 |
小說 |
電子書 |
$ 280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烽火越南:越南大時代小說集
1930年,越南國民黨發動反殖民統治的大規模武裝起義,但未成功;差不多就在同時,越南共產黨在香港正式成立。
起義失敗後的國民黨,元氣大傷,共產黨則不斷發展壯大。留學法國的小說家阮祥三在這時回國,成立「自力文團」,推動現代文學創作,同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暫時停止寫作,投身政治活動,終於成為越南國民黨的領袖。
日本投降,胡志明的共產黨在河內奪得政權,宣布越南獨立,而法國仍不願放棄這一片殖民地,正虎視眈眈企圖重返印支半島。戰火即將重燃,國民黨能否有所作為?阮祥三是該繼續領導國民黨書寫這一段歷史,還是回歸文學、完成他心中醞釀已久的一部大河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