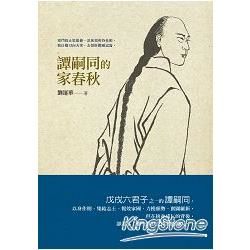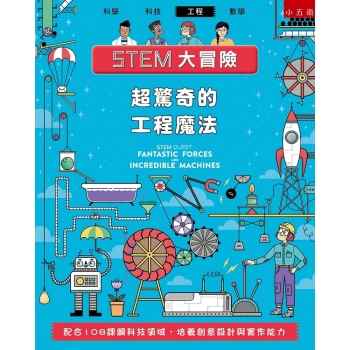一
發源於大圍山,最後注入湘江的瀏陽河,在淮川段拐了一個彎,幾條鋪鵝卵石的街道趴在河岸邊,百多家要死不活的店鋪,除了賣豆腐的六駝背吼幾嗓子,整個瀏陽縣城趕得出鬼來。北正街往右拐彎,就是梅花巷,聽名字便可以猜到那兒的特色,可是,一樣的冷清啊。偶爾有一兩位陌生面孔的男子路過,門洞裡就會閃出花枝招展的女子,拋來一個媚眼,尖起嗓子發幾聲嗲,如果瞄準了目標,還會扭動腰肢,像水蛇一樣纏著不休。這天下午,很少上街的小譚從梅花巷「夜來香」的妓院門口經過,腳步遲疑了一些,被老鴇發現了,迎上前去,笑咪咪地向他招手:「打炮不?」
小譚瞪大兩眼:「打炮?」
老鴇笑嘻嘻地:「肉炮。」
「六炮?!」
老鴇「咯咯」一笑,身後閃出幾名濃妝豔抹、搔首弄姿的女子,發一聲嗲,往他身上靠,終日埋首書齋的白面書生小譚,很少拋頭露面,何曾見過這樣的陣勢,心裡慌亂,撒腿就跑,背後傳來粗魯的叫罵:「傻逼──」
這事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縣城,刺激著人們的神經,給冷清的縣城增添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瀏陽縣不知道十九歲知縣唐步瀛正常;不知道二十歲書生譚繼洵就有些奇怪。
小譚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瞧,他又來了,身穿灰布長衫,手握一本線裝書,目不斜視,步子不緊不慢。他足不出戶,一心向學,極少在外面拋頭露面。雖然在縣城居住的時間很長了,只要他從大街上穿過,立刻就會招來他背後的指指點點──
「呵呵,聞到什麼味兒了嗎?」
「什麼味兒?」
「桐油呀。」
「你是狗鼻子吧?」
「哈哈,哈──」
小譚心裡窩火,不願意與這些粗人爭辯,目不旁騖,加快腳步,有時候被攔住實在沒有了退路,便會昂起頭來吼一嗓子:「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小譚,名繼洵,字子實,號敬甫。目前還是一個窮書生,在取名稱號方面,已經為日後的發達做好了準備,他自個兒的解釋是:未雨綢繆。因此,任憑別人如何譏諷嘲笑,風刀霜劍嚴相逼,苦讀寒窗不動搖。這就是小譚與其他老百姓的區別。
譚氏,在瀏陽縣沒有根,地方誌記載:祖籍福建清流縣,遠祖淵佐明成祖與靖難之師,死於夾河之戰。事定,敘功封崇安侯,故後世以武功顯。四傳宗綸,官湖廣行省總兵官,配平南將軍印。剿九溪蠻有功,久留湖廣,故其子功安、功完留居。功安定居湖廣省長沙縣。又三傳逢其避明季流寇之難,率弟弟及侄兒輩遷居瀏陽縣城,居住在梅花巷,再後來遷居北正街。
從此,譚氏世代以教讀為生,遠離衙門,成了布衣之士,日子也過得清貧。小譚的父親學琴,字貴才,也是一個讀死書的角色,潛心向學,韋編三絕,衣帶漸寬終不悔。他靠一份塾師的微薄收入養家糊口。他以扎實的學養贏得了世人的尊重,連當時的縣太爺都對他禮讓再三。見其家裡兒女眾多,入不敷出,幾次三番動員他入衙門做縣吏,均被婉言謝絕了,直到兒女們一個個長大成人。
他的四個兒子中,老三小譚,在世人的眼裡有些另類,招來了閒人的非議,這使得他心裡很不爽。我兒子怎麼樣?不偷不搶,行為端正,苦讀寒窗,謀取功名,礙你什麼事了嗎?隨著老三的一天天長大,做父親的也感到頭上有壓力了。那些與子實年紀差不多的小夥子,一個個先後結婚成親,有的孩子都可以打醬油了,他還在耍光棍。
老大生兒育女,老二經商掙銀子,老三一心一意讀書,將自己的前途這一寶押在「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上面。當爹的不反對,但是,對這種一條道走到黑的做法,心裡感覺有點懸。天下讀書人知多少,最後能走上仕途的又有幾人?千軍萬馬擠獨木橋,說得難聽一點,叫吊死在一棵樹上,道理再明白不過。
道光二十三年,老三已經滿二十歲了,仍然光棍一條,每天一個勁兒地讀書,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周圍那麼多譏諷的目光,尖刻的言辭,難道對他真的沒有一點兒影響嗎?兒女的教讀婚配,原本是爹娘應該做的事啊。他老伴和他一樣著急,擺在眼前要解決的問題是成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是經常在老三面前叨念:「子實,你爹的話,裝進耳朵沒有?」
老三卻笑嘻嘻地回答:「著什麼急呀,我只要發憤讀書,什麼都有了!爹,娘,你們只管放心吧!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
學琴老倆口及二位哥哥一致認為老三的婚姻大事再也不能耽誤了。行動還得靠一家之主,清貧了一輩子的教書匠譚學琴老先生只好央請媒人物色對象。他家裡雖然過著清貧的日子,但對娶兒媳還是有自己的標準,即一定要同樣的書香門第,也可以解釋為門當戶對。老三長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哦,像這樣的帥哥,又讀了一肚子書。娶媳婦這樣的大事,模樣屬於硬體吧,也不能太差,上要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親戚朋友。然而,作為婚姻當事人,小譚卻能沉得住氣,讀書很安心的,一點也不著急,生活有規律,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而後埋首書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攻讀聖賢書。
在婚姻方面,他不愁,很自信。最上心的,第一個是他娘,第二個是他爹。他們見老三嘴唇周圍的鬍子越來越密,講話的時候嗓子也粗了,更加著急。他們四處打聽誰誰家裡有沒有待字閨中的妹子,還打擾一些很久沒有走動的親戚。俗話說,女大不中留,應該還有潛臺詞,兒子不用愁。很少見為兒子的婚姻這麼著急的父母。學琴先生和他婆娘的不懈努力,終於有了一些眉目。
老二繼墉與瀏陽北鄉豪紳熊美是很要好的朋友。熊美早就知道譚繼洵這個瀏陽縣城的名人,像這樣一個角兒,要想完成其說媒的任務是有點難度。礙於朋友的面子,也只好硬著頭皮勉強答應下來。熊美既然是專門吃這一碗飯的,對周圍一些人家到了談婚論嫁年紀女子的情況熟悉。可是,他連走了幾家,一聽說家裡窮,讀死書,便將媒人下面想講的話全都給堵回去了。熊美思來想去,最後把目光瞄準他堂妹夫徐韶春家裡的長女慶緣。
徐韶春家在瀏陽北鄉爐煙洞,偏僻的大山深處,交通不是很方便。從縣城出來的官道往北至淳口集鎮,而後就是一段約二十里的鄉間小路,連結著徐家祖居的青龍屋場。幾棟氣勢恢宏的瓦房昭示,這個家庭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戶人家。其實徐家的情況和譚家非常相似,曾經也是官宦門第。徐韶春一個從九品的小官,後來被敕封中憲大夫,再後來家道衰落,淪為爐煙洞一普通的農戶人家,靠耕種幾畝薄田的收入勉強維持全家的生活。熊美想到這裡,拍了一下腦門,容光煥發:「絕配啊!」
徐韶春瞭解小譚的家境不怎麼樣,心裡還是有過猶豫。作為父親,哪有不希望女兒嫁入豪門,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但是,他對讀書人還是抱好感的,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他在聽了堂姐夫熊美的遊說之後,腦門發熱,巴掌一拍,痛快地將這門親事答應下來了。當事人慶緣在飯桌上聽到她爹宣佈這個決定時,一口飯也沒有吃,放下筷子走進自己的閨房,躺倒在床上,大放悲聲。
女兒的哭,聲聲入耳,老徐的心裡煩躁,衝女兒緊閉的房門大聲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知道嗎?!」
接下來,就是走程式了。按規矩進行操作,婚娶雙方男女是不可以見面的,漂亮,還是醜陋,個兒高大,還是矬子,全憑由媒人一張破嘴。婚嫁雙方當事人都不知道將要和自己生活一輩子的人長啥模樣,這個懸念要等洞房花燭夜揭下蓋頭才知道。
但是,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男女無論哪一方,如果是形體有殘缺,比如瞎了一隻眼,跛了一隻腳,嗚嗚哇哇講不出一句明白話……上述缺陷中的無論哪一項,則一定要挑明,否則就是不江湖。對於女方還有一項特別的要求,即腳的大小。三寸金蓮為最美,反之,則醜。坊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新娘漂亮麼?升筒裡打得轉身──好!新娘漂亮麼?扇得火燃──醜!
老譚老徐雙方家長審美價值觀基本一致,都是滿肚子的「子曰詩云」,就相貌而言,沒有什麼缺陷需要挑明的。腳的情況,則比較複雜,還得講幾句。徐家有兩個女兒,十六歲的慶緣和十四歲的五緣。她們姐妹,兩歲多的時候,確實也纏過足,後來又放了。一方面的原因,是孩子的哭叫聲令父母動了惻隱之心;二是現實,農家的孩子是要幹農活,如果纏成一雙小腳,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怎麼幹活?這樣的漂亮,農戶人家奢侈不起。
徐家姐妹兒的腳比三寸金蓮大了一些,這是沒有堅持纏足的結果,也是為日後幹體力活做準備。如果一門心思在當官太太,乃至誥命夫人,等於吊死在一棵樹上,懸。
慶緣得知父親為自己在縣城找了婆家。城市戶口,多好,可是她卻心裡犯嘀咕,這是一戶怎樣的人家呢?休看她人小,心眼卻很多,婚姻自己不能做主,心裡忐忑,卻又無法改變。不過心裡還是希望能夠及早瞭解一下婆家,尤其是未來夫婿的情況。爐煙洞距離縣城約六十餘里,不算太遠,只因中途橫亙一座陡峭的蕉溪嶺,往返一趟還真不容易。好在經常幹體力活,區區幾十里路,對她來說,不算啥。
一個女孩子家家,去一趟縣城,拋頭露面,如果沒有重要事情的話,幾乎完全沒有這個可能。聰明的慶緣姑娘也會想方設法從爹嘴裡掏出一點有價值的資訊。可惜,她爹就是密不通風,人活到他這個年紀,閱歷、經驗擺在那兒呢。
譚徐兩家訂婚之後大約三個月,慶緣不知道從什麼管道獲得消息,縣城舉行廟會。機會來了,她向爹娘提出要求,去看熱鬧。爹說:「不行,你一個女孩子,拋頭露面去縣城,成何體統,也不怕人家笑話嗎?你是有婆家的人了,知道不?」
娘幫腔說:「不能去。」
慶緣頂撞她爹:「我一個鄉下村姑,整天幹粗活的料,哪來的『體統』啊?」
他爹生氣了:「你還敢頂嘴,沒有大小!」後面還有潛臺詞:你的書讀哪兒去了。
老徐突然發現慶緣眼角噙著大顆的淚珠,心一下就軟了下來,揚起的手懸在女兒的頭頂,落不下來,看著旁邊的小女兒五緣,說道:「五緣,陪你姐去一趟縣城,記住,不要貪玩,早去早回,聽見沒有?啊,還有,一路小心,不要亂跑,進城以後,你們姐妹不要分開,要一直在一起,聽見沒有?」
五緣笑嘻嘻:「城裡有鬼嗎,爹?」
老徐虎著臉罵一聲:「鬼婆子!」
小弟拱到大姐面前,冒出一句:「有啊,有一隻綠豆子鬼──」
慶緣沒有心情與弟弟開玩笑,含淚點頭答應:「聽見了,爹。」
老徐看著五緣,重點叮囑,問道:「你聽見沒有?」
五緣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我不聽,又不是我要嫁人。」
第二天徐家姐妹早晨上路了。這是她們獨自第一次出遠門,門前一條七彎八拐的小路,走了十多里,踏上通往縣城的官道。姐妹攜帶一個布包,裡面是油紙裹的幾只蕎麥粑粑,餓了吃一口;渴了便伏路旁的水溝邊喝一口,隨處都有山上流淌下來的泉水。縣城其實也就屁眼大的地方,姐妹倆卻為了打聽譚學琴家住哪兒費了很大的勁。不告訴也就罷了,還要反問:「你們兩隻妹子要幹什麼?」
如果在鄉下問路,不但熱情指引,還會客氣一句:「進來歇歇腳,吃碗茶再走吧!」
慶緣不高興了:「城裡人怎麼能這樣呢?」
五緣嘿嘿一笑:「你很快就變城裡人了!」
慶緣撂臉子了:「你高興不是?!」
五緣還是笑嘻嘻地:「我沒有做城裡人的八字。」
姐妹倆正拌嘴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賣豆腐的駝背,五緣緊追幾步,恭恭敬敬呼一聲:「大伯──」
駝背轉過臉來,很吃驚:「你叫我大伯?!」
啊,才二十幾歲吧,慶緣鬧了一個大紅臉,駝背卻笑嘻嘻地自我介紹:「我叫六駝背,兩位小姐,喝水豆腐嗎?剛打出來的,又嫩又甜。」
這個賣豆腐的後生,嘴巴很甜的,雖然駝背,卻不討厭。
五緣連忙說:「啊,不不,我們是問路的,請問有一位叫譚繼洵的,住哪兒?」
六駝背隨便瞄了她們姐妹一眼,愣了愣,說道:「你們找他呀──隨我來吧。」
經過熱心的駝背後生指引,姐妹倆順利地找到了譚家。她們在門口徘徊,沒有路人的時候,趕緊將眼睛緊貼在門縫上往屋內偷窺,觀察的結果,感覺這個家庭的貧寒。慶緣的心情便有些沮喪,心想,如果嫁過來,這樣的家境如何過日子呀?
五緣卻認為結論不要下得太早了,沒有見到小譚本人啊,趁這個機會,一定要看看未來的姐夫到底長成啥模樣。正在此時,只見一名臉皮白淨的年輕人,身著一件分明還綴著補丁的灰布長袍,手握一卷書,目不斜視,從街上而來。
慶緣心裡有些敏感:「莫非他就是……」
年輕人從兩位美女旁邊走過,視若無睹,「吱呀──」一聲推開大門,閃身進去了。
五緣衝姐姐笑道:「姐夫一表人才啊。」
慶緣忍不住流淚了:「我的命不好……」
「我看挺好的呀!」
慶緣歎了一口氣,說道:「你這只鬼妹子,瞧他一副窮酸相,你講他那麼好的話,乾脆你嫁給他好了!」
五緣還是笑嘻嘻地說道:「我不會和你搶老公,妹妹懂味。」
慶緣好像真生氣了:「姐姐遇到了這麼倒楣的事,你還要尋開心,哪有這樣的妹妹?!」
五緣不笑了,也認真起來:「這個小譚我看蠻好,你不要只往壞處想啊,王寶釧苦守寒窯,終於大富大貴。我看這小夥子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將來肯定會金榜題名,高官任做,你將來一定會當上誥命夫人,姐──」
五緣不說話了,一張稚氣未脫的鵝蛋型臉上露出這個年齡段女孩子少見的嚴肅,沉默了好一會兒,突然噗哧一聲笑了。慶緣覺得奇怪,盯著妹妹問道:「有什麼好笑的呀?」
五緣手一指,說道:「你看那個人!」
慶緣順著妹妹的指頭看過去:「不就是賣豆腐的嗎,剛才還問了路……一個好後生啊,可惜駝背了……」
五緣好奇:「他的背那麼駝,還能挑擔子?」
慶緣沒有好聲氣:「你管得真寬!」
五緣從六駝背身上收回目光,神情變得嚴肅起來:「你要要抗婚嗎?姐,這個你可要想清楚後果……算了吧,爹娘把我們從一尺長撫養成人也不容易,還是多體諒……婚姻其實就是撞大運……」
慶緣知道自己的抗爭不會帶來想要的結果。但是,一聲不吭地接受,心有不甘。況且爹娘又不在眼前,盡可以發洩一下,於是氣憤地大聲道:「既然不容易,就不應該把女兒往火坑裡推!五緣啊,你豬腦子嗎?!」
五緣對姐姐的怒不介意,忽然笑道:「你就那麼不看好這個書……讀書人小譚的前程嗎?至少,他也是一個帥哥呀,你不喜歡老公長得帥嗎?」
慶緣雙眉緊蹙,幽幽地說道:「十足的呆子,書呆子!」她一本正經地問道:「那好──五緣妹子,那我要問你了,如果讓你嫁給他,願意嗎?你要說心裡話──」
有這樣的如果嗎,五緣兩眼遠遠地看著譚家虛掩的大門,搖了搖頭,說道:「你要我說心裡話嗎?那我告訴你吧,不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爹娘做了決定,沒有辦法改變。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往好處想,不會像你這樣只往壞處想,你這叫自尋煩惱……」
聽妹妹這麼一說,慶緣的心裡似乎好受了一些,做了一次深呼吸,眼睛看著不遠處河堤上停靠在周家碼頭的一條白帆船。船頭站立一位身著長衫的年輕男子,一時陷入了沉思。五緣湊近,順著姐姐的目光看過去,笑道:「你是看帥哥嗎?」
慶緣默然無語,想著自己的心事。
在回去的路上,姐姐很少說話,走起路來無精打采,妹妹一路上蹦蹦跳跳,沒心沒肺,對什麼都感到新鮮。一會兒蹦到水坑邊摘水仙花,一會兒追趕幾隻蹁躚的花蝴蝶。
慶緣回到家裡,誰也沒有打招呼,徑直走進自己的臥室,躺倒在床上,飯也不吃,腦瓜被那位穿補丁衣的後生占滿了。
縣城回來,慶緣還是沒有死心,還想繼續瞭解譚家的情況,找不到再去的理由,便將心事告訴了弟弟。數日後,弟弟從縣城回來,見了姐姐不說話,直笑。慶緣要生氣了,他才說,未來的姐夫這個人呀,果然是一個十足的書呆子,衣冠不整,終日沉迷書卷,除了讀書,啥也不聞不問。弟弟沒有顧忌姐姐的表情,一邊說一邊比劃,沒有注意到大姐臉色蒼白,一副欲哭無淚的模樣。
五緣推開弟弟,不讓他繼續說下去,添亂。
慶緣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向父母訴說自己的委屈,說到傷心處,珠淚雙流,表示不願意嫁這樣的一個書呆子。老徐不等女兒說完,往吃飯的桌子上使勁拍了一巴掌,厲聲喝斥道:「大膽!既然已經有了婚約,豈可兒戲,我徐府在地方上堂堂正正的人家,你想讓我壞了家族名聲,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她娘也勸說道:「慶緣啊,婚姻是命中註定,由不得自己,你要想開一點,我聽五緣誇這小夥子相貌堂堂,苦讀寒窗,將來金榜題名,你不就夫榮妻貴了嗎?」
慶緣聽母親這麼一說,哭得更厲害了,五緣遠遠地站著,說心裡話,她是同情姐姐的,由姐姐又想到了她自己:「我將來的老公會是什麼樣呢,也是撞大運?」
她不笑了,心情變得沉重起來。
瀏陽所屬的湘贛邊一帶地方,每到年底,大多數人家都習慣在這個時候婚娶。這個習俗的形成,與經濟狀況不無關係。每到年底,一年的收穫歸倉,有錢了,鄉下人家,婚娶是一件花銷很大的事情。
一般來說,訂婚之後,就是擇喜期完婚了,譚家通過媒人熊美表達完婚的願望。可是,只要媒人踏進爐煙洞老徐家的門,慶緣便躲在閨房裡哭泣,不茶不飯,非常抗拒。
徐韶春夫婦見女兒這樣,心裡也有些動搖,埋怨做媒的表兄,不該給他們找一個書呆子做女婿。熊美心裡也不痛快,我做好事,反而落下埋怨。早知道會弄成這樣,當初就不應該答應做媒了。現在,事已經到這個程度了,打濕了的頭髮總歸要剃呀。只好找托詞對譚家人說:「慶緣還小,父母的意思是再推遲一年,如何?」
譚家通情達理,沒有多費口舌,痛快地答應了,小譚對婚姻似乎不是很感興趣,每天的作息制度從來都沒有改變過。不知不覺又是一年將盡,譚家將喜期再一次由媒人送達,慶緣當著媒人熊美的面放聲大哭,不願嫁一個書呆子為妻的決心沒有改變。熊美勸說女當事人:「慶緣呀,你錯了,譚家三公子很聰明,人品不錯,與他接觸過的人都誇他將來肯定鵬程萬里,前途未可限量。目前的家境雖然目前差一點,『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我是你親戚,還會害你不成?」
慶緣不回話,一個勁地哭哭啼啼,老徐拿女兒也沒有辦法,慶緣年紀不大,卻是一個性子剛烈的人。如果她不願意,強迫的話,恐怕會出點狀況,到時候,後悔也來不及。老徐家無奈,只好以女兒還小為理由,又一次要求推遲婚期。
這一推再推,轉眼道光二十七年,慶緣二十一歲了,訂婚已經五個年頭了。如果還不完婚,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了。這年冬季,譚家的喜期一到,老徐口氣堅決答應完婚。婚期一天天臨近,慶緣還是沒有鬆口,只要一提到完婚就哭泣不止。老徐心煩,雙眉緊蹙。
迎娶的那一天,通往縣城的官道上,鑼鼓喧天,長長的迎親儀仗隊抬著花轎在鄉鄰的關注下,朝徐家大屋而來。在大院門口,便點燃了大紅鞭炮,喧鬧聲中,鞭炮炸響的紙屑紛紛揚揚,像是下起了一陣桃花雨。此時,徐韶春一家人卻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慶緣房門緊閉,堅決不從,無論父母及其它親戚如何勸說,就是不肯將房門打開。媒人熊美從外面走了進來,問準備好了嗎?時辰一到,就要起轎了。徐家人坐著發呆,他感覺到氣氛不對頭,忙問是怎麼回事?
徐韶春歎了一口氣:「慶緣這個強東西,她死活不願意嫁譚家……」
熊美再也無法忍受,勃然大怒:「你們當父母的,這麼無能,既然不同意,早幹嘛去?!不肯上轎,晚囉!你們不要臉,我也跟著你們一樣不要臉嗎?譚府會答應嗎?──氣死我了!」
熊美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徐韶春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在爐煙洞,他也是有頭有臉的角色,活這麼大歲數,還沒有人這樣的態度對付。他知道自己理虧,想解釋幾句,嘴唇動了動,半天沒有出聲。熊美還在氣頭上,不待徐家人回話,走到慶緣的房門口,朝緊閉的門狠狠地一腳踹去,不開,又一腳,徐家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熊美踹第三腳之後,門開了,慶緣坐在床沿,哭成了一個淚人。外面的鼓樂一陣緊似一陣,老徐衝到大女兒面前,左右開弓,狠狠地扇了兩記耳光,她還是一動也不動,嘴角流淌殷紅的鮮血。
老徐厲聲喝道:「你願意不願意?!」
慶緣低垂著頭,一言不發。
熊美在旁邊使勁的一跺腳,說道:「我做了一輩子的媒,還沒遇見過這樣的女子!」
老徐又一記耳光打在大女兒的臉上「叭──」吼一聲:「啞巴啦,拿繩子來,捆綁也要把她弄進花轎,我不信這個邪了!」
氣氛壓抑得令人喘不過氣來,慶緣還是坐著不動,老徐衝進雜屋,拿起一根棕繩子,撲到慶緣面前,就要動手,在場的人一個個都驚呆了。熊美使勁跺了一下腳,大聲吼道:「我真後悔做這個媒,沒事找事──」
慶緣她娘忽然發瘋似的用身子護著慶緣,喉頭哽咽地對熊美激動地說道:「對不起你啊,我女兒不嫁了,不嫁了──」
老徐推了他婆娘一個趔趄,吼道:「女兒不嫁,一輩子留在家裡嗎?!」
外面的鑼鼓聲又起,屋子裡的氣氛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老徐突然扔掉手裡的繩子蹲在地上。慶緣的態度還是沒有絲毫的改變。眾人都感到無計可施的時候,五緣突然走到老徐面前,說出的話令大家驚訝:「別逼我姐了,會出人命的,我替我姐出嫁──」
屋子裡一陣騷動,所有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看著五緣。
老徐驀地抬起頭來,看著五緣,驚訝地問道:「你願意嫁譚──」
五緣平靜地說:「是的,我願意。」
熊美愣了片刻,立刻轉怒為喜,長吁一口氣,大聲吆喝:「還愣著幹嘛,快些妝扮新娘呀,起轎的時刻快到了!」
徐家人經媒人這一提醒,又是一陣忙亂。
眾人為五緣著妝的時候,慶緣被晾在一邊,她的情緒漸漸地緩過勁來,似乎有些過意不去,走到妹妹面前,既慚愧又不無擔心地說道:「妹妹,你真的願意嗎?」
五緣點了點頭,不爭氣的眼淚卻奪眶而出,看著姐姐被打得又紅又腫的臉頰,說道:「姐,父母將女兒辛辛苦苦養大,不易啊,你別記恨好嗎?」
「妹妹,姐對不起你……」慶緣喉頭哽咽,大顆地掉淚。
五緣笑道:「你不要這麼說,說不定還是我的八字好呢,譚三公子這個人目前狀況是差一點,但是,他安貧樂道,一心一意讀聖賢書,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夠做到的,將來肯定有出息……吃不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
「哇──」慶緣哭出聲來。
五緣笑道:「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你別哭呀,姐──」
五緣勸說姐姐,自己的笑臉上卻閃著淚光。
臨出門,新娘拜倒在父母面前,說道:「感謝爹娘的養育之恩,爹──娘──從今天起,女兒就是譚家媳婦了,我會做一個婆家滿意的好兒媳的,絕不會給爹娘丟臉──請不要牽掛女兒,祈願二老今後多多保重……」
老徐夫婦淚水漣漣,連忙上前扶起女兒,勉勵她孝敬公婆,伺候老公,做一個好兒媳,一個賢內助。
五緣說:「我知道了,會這樣做,二老只管放心吧!」
五緣又轉向姐姐,懇切地說道:「姐姐,感謝你從小對妹妹的照顧,今後……祝願你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吧!」
弟弟突然抱著五緣哭了,五緣在弟弟頭上撫摸幾下,笑道:「已經是男子漢了,懂事了,今後要聽爹娘姐姐的話,爹娘老了,你要聽話啊,弟弟──」
慶緣想不到事情的發展竟然會是這樣,愧悔交集,說了一句「對不起」,倒在母親懷裡放聲大哭。
五緣猛地揚起頭來,神情堅毅,笑道:「姐姐,你哭什麼呀,將來,我老公金榜題名,飛黃騰達,夫榮妻貴,我當上誥命夫人──到時候,你不要後悔就是……到時候我一定感謝你,好好感謝,姐!」
五緣說這話的時候,淚光閃爍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容,她娘看在眼裡,感到揪心,她理解女兒此時此刻的心情,忍不住伸手在五緣的肩膀上摸了摸,喉頭哽咽地說:「五緣,我的好女兒,委屈你了……」
姐姐流著淚,一臉的歉疚,不斷地重複:「妹妹,姐對不起你……」
五緣走到姐姐面前,舒展兩臂輕輕地抱了一下,笑著說道:「這是我自願的,與你沒有關係,你不要這樣……你記住啊,我將來當誥命夫人了,你不許後悔啊……」
慶緣抑制不住情緒哭出聲來。
很快,五緣被妝扮一新,頭上蓋著紅頭巾,在伴娘、儐相的簇擁下走出房間,走出堂屋,走出大門,往擺放在禾場上的大花轎走。頓時,整個徐家大院鼓樂齊鳴,笑語喧嘩,炸響的鞭炮,像無數隻看不見的手,將紅紅綠綠的紙屑拋到空中,又紛紛揚揚地撒下。
媒人熊美一聲拖長的聲音:「起轎──」
有人接著吆喝:「起轎──」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譚嗣同的家春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譚嗣同的家春秋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以身作則、集結志士、報效家國、力挽頹勢、奮圖維新,
但在捨身成仁的背後,
卻遺落了那些默默支撐著他的人……
※ 從譚嗣同的父輩談起,了解譚家在清末民初這一段時間的家族動盪史。
※ 以父親譚繼洵、妻子李潤的角度去看譚嗣同這個人,不只深入他的革命意志,也深入他死亡之後所造成的影響。
※ 作者擁有深厚的歷史素養,取材真實,以簡潔有趣的筆調講述這一段家庭的春秋。
英雄的身後總有另一群沉默的英雄,那是他們的父母、妻子、師長、管家、家人……
對譚繼洵而言,自己寒窗苦讀一舉登第,最後升為當朝一品官員,不愧為讀書人的典範。唯一擔心的,就是自家身為讀書苗子,卻不肯走讀書人科舉之路的七兒復生。
對李閏而言,為了嫁給如同自己爹爹一樣的讀書人,她離開了青梅竹馬,成為復生的妻子。但是她不能理解,自家丈夫為何願意放棄科舉功名,跟康梁那些朋友走上維新的道路。
一直到最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
時勢造英雄──這些名不經傳的小人物,為了親愛家人的遺志,為了國家,生動地詮釋踏上另一條道路的決意。
作者簡介:
劉運華
湖南省瀏陽市人,大學歷史系出身,先後供職於市政府多家機關,亦為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1983年開始文學創作,曾從事烈士傳編纂工作八年,作李閏、塗啟先、焦達峰、陳作新等傳記刊於《名人傳記》、《傳記文學》、《人民文學》等刊物,中篇小說《譚夫人李閏》報紙連載。先後有400餘萬字各類文學作品見諸《芙蓉》、《羊城晚報》等40餘家報刊,並有多篇為《讀者》、《知音文摘》、《讀友》等轉載。人物傳記更曾被錄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長征出版社等編輯的多套叢書。
章節試閱
一
發源於大圍山,最後注入湘江的瀏陽河,在淮川段拐了一個彎,幾條鋪鵝卵石的街道趴在河岸邊,百多家要死不活的店鋪,除了賣豆腐的六駝背吼幾嗓子,整個瀏陽縣城趕得出鬼來。北正街往右拐彎,就是梅花巷,聽名字便可以猜到那兒的特色,可是,一樣的冷清啊。偶爾有一兩位陌生面孔的男子路過,門洞裡就會閃出花枝招展的女子,拋來一個媚眼,尖起嗓子發幾聲嗲,如果瞄準了目標,還會扭動腰肢,像水蛇一樣纏著不休。這天下午,很少上街的小譚從梅花巷「夜來香」的妓院門口經過,腳步遲疑了一些,被老鴇發現了,迎上前去,笑咪咪地向他招...
發源於大圍山,最後注入湘江的瀏陽河,在淮川段拐了一個彎,幾條鋪鵝卵石的街道趴在河岸邊,百多家要死不活的店鋪,除了賣豆腐的六駝背吼幾嗓子,整個瀏陽縣城趕得出鬼來。北正街往右拐彎,就是梅花巷,聽名字便可以猜到那兒的特色,可是,一樣的冷清啊。偶爾有一兩位陌生面孔的男子路過,門洞裡就會閃出花枝招展的女子,拋來一個媚眼,尖起嗓子發幾聲嗲,如果瞄準了目標,還會扭動腰肢,像水蛇一樣纏著不休。這天下午,很少上街的小譚從梅花巷「夜來香」的妓院門口經過,腳步遲疑了一些,被老鴇發現了,迎上前去,笑咪咪地向他招...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劉運華
- 出版社: 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4-12-24 ISBN/ISSN:97898656966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6頁 開數:16*23 c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