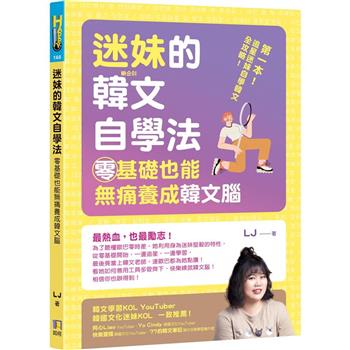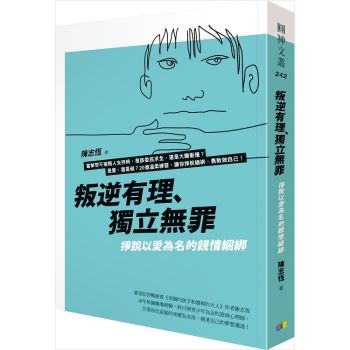一、我們的睡眠,我們的失敗
「勞動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勞一生,可得幸福的長眠。」達‧芬奇(Da Vinci)讚美的是勞動,更是勞動、睡眠和幸福之間的親緣關係。但他最想稱頌的,或許是將上述三者連在一起的曲線、時間和隧道,尤其是那條不斷延宕、朝六個方位升騰的曲線,不可能是野心、陰謀、詭詐、最大的人生利潤,更何況假借勞動才機緣巧合帶來的榮譽金字塔呢?按照巴羅克(Baroque)主義者的美學立場和倫理學觀點,直線「一根腸子通屁眼」 的率真特性,簡直等同於罪惡,因為它太赤裸、太露骨,約等於初次見面就貿然求歡。達‧芬奇,那個被好奇心控制,隨時準備冒險解剖屍體,以求弄清人體結構、不讓畫筆犯下透視錯誤的傑出人物,非常瞭解勞動的性格和品質,洞悉勞動、睡眠和幸福間的親緣關係。依神學大師德爾圖良(Tertullianus)不無輕蔑性的看法,勞動,尤其是被早期賢哲輕視的體力活與手藝活,「總要比馬戲場、劇場和各種競技場中的活動更為高尚。」 因此,達‧芬奇,那本辛勤勞作的百科全書,才願意賦予勞動、睡眠以溫婉的質地。
但是,除了華夏民人傳說中的「小國寡民」階段(我稱之為陰的世界而不是陽的世界) ,以及古希臘人心目中醇厚、恬靜的「黃金時代」(Golden Times),巴爾紮克(Honoré de Balzac)筆下的拉斯蒂涅發出的戰鬥宣言——「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A nous deux,maintenant!) ——卻無疑是一切時代最真實的人生廣告術語,最嘹亮的號角,最催人「無利不起早」的鼓點,也是描寫人之野心最簡潔、最筆挺的「元語言」(metalinguistic),就像有人說過的,我們押的是每一個閃念,但每一次的賭注,卻是整整一輩子。自此,被蹂躪、被異化的勞動,成為我們生命中最晦暗、最黏稠的部分,迅速構成了「拼命」的基本要素、爭取人生「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堅實底座,何況德國社會學家尼克勞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早就從歐洲現實生活的正面戰場上,以四兩撥千斤的輕鬆招式優雅地保證過:人生「對每一個有進取心的年輕人提出的挑戰,極其簡潔地表現在這幾個字中」 。但那個過分迷戀巴黎的花花公子,厭惡德國的德國佬顯然忘記了,「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也是法國結構主義者眼中最簡潔、最經濟、最筆直的人生句式,主、謂、賓齊全,定、狀、補暗含,何況額外還有一個買一送一的感歎詞,為它增添了必不可少的曲線;何況浪漫、頹廢的巴黎,還是這條蜿蜒起伏的曲線自我繁殖和隱藏自身的首都,但它也是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和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拿撒勒(Nazareth)——上帝之子的誕生地。
自此以後,拉斯蒂涅,那個被捏造出來的人物發出的戰鬥誓言,才無時無刻不敲擊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社會垃圾堆上的人」 的卑微靈魂。它讓我們心醉神迷,令我們神情亢奮,鼓勵我們盯著裸體骨頭的雙眼持續放電……總之,它的品貌、氣質、乳房、四肢和腰身,都同結構主義者樂於將人生看作一個長句的做法,吻合到了天衣無縫的程度。但結構主義者的長句人生觀,還是過早暴露出它的宿命論嘴臉:黑格爾宣稱凡存在即合理;自稱厭惡黑格爾、嫌棄形而上學的結構主義,卻主動找出了「合理」「存在」的結構性機制,還為那句人盡皆知的名言,給出了動力學維度上的繁複論證。同黑格爾老套、刻板的德意志面孔相比,結構主義徐娘半老卻又風韻猶存的「三仙姑」做法意味著:我們的人生樣態只能如此、只得如此,奴隸永遠是奴隸,老婆永遠是命中註定的那一個,宛若死亡只願意同它自己相像。長有一張法國面孔的結構主義試圖表明:它一直都是「修飾我們敘述的宿命論公式」——宛若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針對某種令人厭惡的現實境況痛斥過的那樣。而結構,它當真是奇格弗里德‧吉迪翁斷言的,始終「扮演著無意識的角色」,總是傾心於「專制性的形式世界」嗎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幾乎所有結構主義者都選擇性地忘記了其論敵——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警告和奚落。當然,在布羅代爾所屬的「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諸君子看來,布氏鏗鏘有力、作風霸道的言辭,首先是奚落,其次才是警告:「所有的結構都同時既是歷史的基礎又是歷史的障礙」 。但這等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之辭,遠不足以打擊結構主義者自信滿滿的方法論腎臟,因為在他醉醺醺的高潮時分或癲狂時刻,最想要的,就是結構內部的「吊詭」特性。他也樂於宣稱:結構內部左腳給右腳下絆子、右手扇向左臉的喜劇情景,昭示了人生的自相矛盾;有且只有結構內部的「吊詭」特性,才能讓結構主義者在綿遠、悠長、密不透風的語言空間中,重新安排、設置、規劃和重組我們矛盾透頂的人生與生活。或許,這才是結構主義之於我們的唯一真實性,因為它像前東德(民主德國)一樣,總是傾向於建設一種「沒有心臟的軀幹國家」 ,亦即腦子停擺,陽具挺拔,而且陽具將不受腦袋指揮和支配。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夢境以北:失敗主義者手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75 |
散文 |
$ 175 |
社會人文 |
$ 198 |
中文現代文學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5 |
催眠/夢 |
電子書 |
$ 250 |
散文 |
$ 405 |
教育/心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夢境以北:失敗主義者手記
我是個每天都做夢的人,夢境的內容匪夷所思,就像我在本書中描繪過的那樣,超過了我在白天的所有想像。
本書是一個專題性質的隨筆集,探討了夢境的基本特徵,以及人們對夢境的管制。全書旁徵博引,出語犀利、幽默,於嬉笑怒駡之中見出真相。
依我看,人最富有想像力的時刻,只能是在夢中。否則,面對眾多相互衝撞和桀驁不馴的化學元素,一籌莫展的門捷耶夫也不可能輕易發明元素週期表。而按中醫的觀點,做夢是身體虛弱、陰陽不調、剛柔不濟的表現,但我卻明知故犯,將它當作雙倍的人生,當作純粹的享樂:在「夢」中,也能展開白天「夢」想不到的生活——這該是何等奇妙的事情!
作者簡介:
敬文東,男,1968年生於四川省劍閣縣,文學博士,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流氓世界的誕生》、《指引與注視》、《失敗的偶像》、《隨貝格爾號出遊》、《靈魂在下邊》、《詩歌在解構的日子裏》、《事情總會起變化》、《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等。
章節試閱
一、我們的睡眠,我們的失敗
「勞動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勞一生,可得幸福的長眠。」達‧芬奇(Da Vinci)讚美的是勞動,更是勞動、睡眠和幸福之間的親緣關係。但他最想稱頌的,或許是將上述三者連在一起的曲線、時間和隧道,尤其是那條不斷延宕、朝六個方位升騰的曲線,不可能是野心、陰謀、詭詐、最大的人生利潤,更何況假借勞動才機緣巧合帶來的榮譽金字塔呢?按照巴羅克(Baroque)主義者的美學立場和倫理學觀點,直線「一根腸子通屁眼」 的率真特性,簡直等同於罪惡,因為它太赤裸、太露骨,約等於初次見面就貿然求歡。達‧芬奇,...
「勞動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勞一生,可得幸福的長眠。」達‧芬奇(Da Vinci)讚美的是勞動,更是勞動、睡眠和幸福之間的親緣關係。但他最想稱頌的,或許是將上述三者連在一起的曲線、時間和隧道,尤其是那條不斷延宕、朝六個方位升騰的曲線,不可能是野心、陰謀、詭詐、最大的人生利潤,更何況假借勞動才機緣巧合帶來的榮譽金字塔呢?按照巴羅克(Baroque)主義者的美學立場和倫理學觀點,直線「一根腸子通屁眼」 的率真特性,簡直等同於罪惡,因為它太赤裸、太露骨,約等於初次見面就貿然求歡。達‧芬奇,...
»看全部
作者序
後記
從十八歲到現在的二十多年間,和其他門類的寫作相比,雖然也寫過字數不算太少的隨筆作品,但那只是在讀書、求學、教學的間隙,或在寫作所謂「學術文章」需要喘氣時,像個資深票友一樣偶爾為之;仰仗的,僅僅是老農民對待自留地的那股子熱情和執著,從沒拿出整整半年光陰用於隨筆寫作。在接近完成這部小書的時候,才意識到這個暗暗滋生出來的問題,才讓我大吃一驚。我下意識地問自己:當初決定花費如此大塊的時間,到底是怎麼想的?現在,本書已經正式殺青,我只能粗略地估計:也許是一如既往地想改變自己的語言風格吧;要不,就是因...
從十八歲到現在的二十多年間,和其他門類的寫作相比,雖然也寫過字數不算太少的隨筆作品,但那只是在讀書、求學、教學的間隙,或在寫作所謂「學術文章」需要喘氣時,像個資深票友一樣偶爾為之;仰仗的,僅僅是老農民對待自留地的那股子熱情和執著,從沒拿出整整半年光陰用於隨筆寫作。在接近完成這部小書的時候,才意識到這個暗暗滋生出來的問題,才讓我大吃一驚。我下意識地問自己:當初決定花費如此大塊的時間,到底是怎麼想的?現在,本書已經正式殺青,我只能粗略地估計:也許是一如既往地想改變自己的語言風格吧;要不,就是因...
»看全部
目錄
1、我們的睡眠,我們的失敗
2、我們的夢鄉,我們的故鄉
3、夢神,卑微的夢神
4、夢奸犯的誕生
5、占夢術的秘密
6、夢境等級制度
7、聖人之夢
後記
2、我們的夢鄉,我們的故鄉
3、夢神,卑微的夢神
4、夢奸犯的誕生
5、占夢術的秘密
6、夢境等級制度
7、聖人之夢
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敬文東
- 出版社: 釀出版 出版日期:2015-01-28 ISBN/ISSN:978986569666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0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