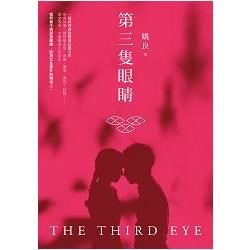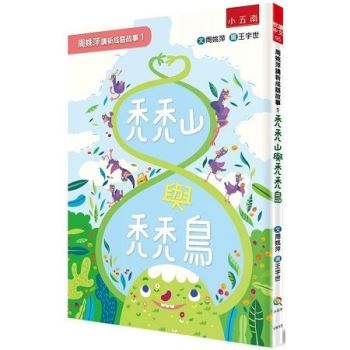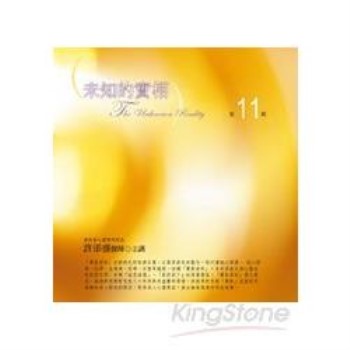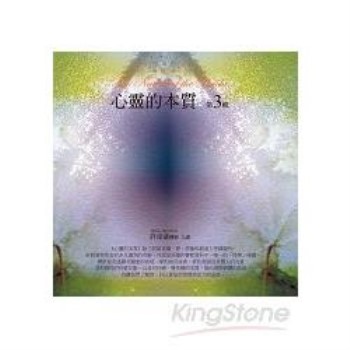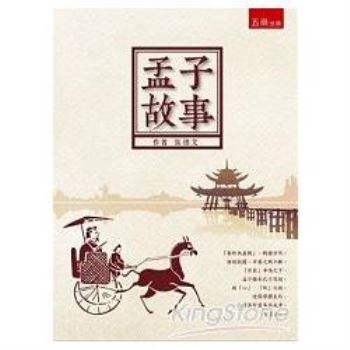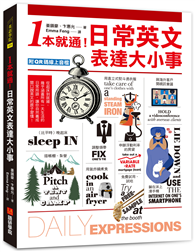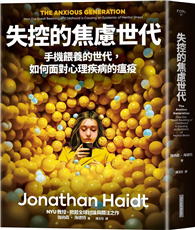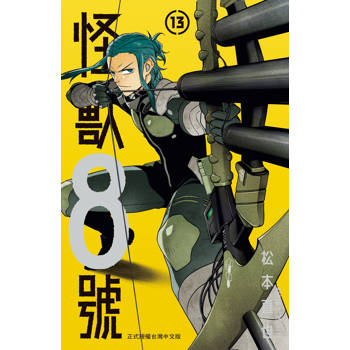後記
我的千山萬水
在流浪的旅途中,倚窗攤開一本書,如同攤開整個世界。
我的朋友去旅行,臨行前,在背包裡常放一本書,而我卻略有不同,便神祕兮兮地放了書,還神經兮兮地放了書稿。
那些書稿,並未成形,是我每日每夜書寫的。
我將它們打印下來,放在背包裡。每當背起它們時,亦如背起整個世界,背起那些千山萬水,讓它們跟著我流浪,自北京而上海而香港而台灣……
我能感受到肩膀上的重量―文字的重量。
其實,我沒有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每天為生活所累,為工作所累,尤其在上海時,腦子一熱,便將工作辭了,我想專心寫作。剛開始那幾天,還能靜下心來好好寫,可寫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患得患失了,開始擔心明天,害怕明天。
想起在上海戲劇學院時,跟朋友一起看戲,看《羅密歐與茱麗葉》,舞臺上耀眼的燈光在我眼前一掃而過。黑暗中,書寫的衝動又在體內翻騰,我好想衝出戲院,跑回住處,將自己鎖在房間裡,把那時的想法、那時的感動一一書寫下來。
可是,我沒有那麼瘋狂,因為身邊還坐著朋友。
在上海待了半年,為生活所迫,我又北上進京了。白天上班,晚上寫小說。因住處離北京大學很近,我幾乎每晚都去北大,自西門而入,走過石拱橋,繞到未名湖,沿着蜿蜒的小路,邊賞著幽暗的路燈,邊看著隱約的博雅塔,一路走到自習室。
我知道,那路燈,就是文學的眼睛。
這本小說,前前後後折騰了五年。
今年元月份,若不是跟台灣這邊簽了合約,我亦不會產生重新修改書稿的想法。那段時間,這個問題常常困擾著我,它像一隻老虎那樣,在後面攆著我,給我以精神上的恐懼,並想把我吃掉。我迅速看了一遍書稿,發現裡面有很多硬傷,便覺得那書稿不足以拿出來付梓印刷,恐對不住讀者,亦怕辱沒文學之殿堂。
我背負我的姓氏和名字太久,那個姓氏是祖宗留給我的,那個名字是父親起給我的。在這種使命感的促使下,我重寫了這部書稿,每寫到快意處,便覺天地之間,山川草木,唯吾與文章耳。
還好,經過千山萬水,這部書稿得以完成。就在完成的同時,我感到輕鬆很多,亦感到沉重很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自己的書在台灣得以出版,懼的是怕這些作品難登大雅之堂。每想到此,常常自責不已,如今面對文章,不敢不恭敬待之。
由於寫作,我身邊的朋友漸漸少了,朋友之間的應酬也逐逐推掉了很多。我把自己藏在書稿裡,藏在自己構思的小說中,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我似乎有一種知識上的傷痛,這種傷痛使得我每天都過不好自己,我總顯得那麼鬱鬱寡歡,好像整個世界都不瞭解我。
突然,我在一本書裡看到一段話,便打消了那種不健全的情緒:「今以一人之身而憂世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也就是說,現今以一人之身而擔憂世道不治,從而流淚不止,這是擔心黃河混濁而哭著希望它澄清,沒有比這樣做更無益的了。
總之,《第三隻眼睛》得以完成了,感謝生活中的過往,感謝過往中的磨難,感謝磨難中的朋友,沒有你們的支持與理解,這本書不可能這麼快完稿。在脫稿之際,我在這裡默默地獻上祝福。
如果沒有機會再去台灣,就讓《第三隻眼睛》替我看看台灣,看看台灣的風土人情。有人曾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情。多少年之後,那《第三隻眼睛》亦是我,他會看到台灣最美的風景,你說是嗎?
我想是的。
二○一三年陰曆九月二十日,北京圓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