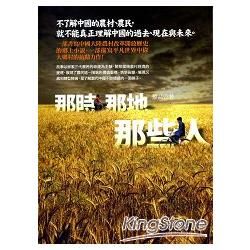不了解中國的農村、農民,
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部書寫中國大陸農村改革開放歷史的鄉土小說,一部描寫平凡世界中偉大鄉村的抗鼎力作!
故事以柳家三代農民的命運為主軸,緊緊圍繞農村經濟的變遷,展現了農民這一階層的價值重構、情感裂變、倫理沉澱和轉型陣痛,是了解當代中國不能錯過的一面鏡子。
《那時‧那地‧那些人》是一部展現中國大陸北方農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歷史發展軌跡的小說。
作品以柳家三代農民的命運為線索,緊緊圍繞農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描繪了跌宕起伏的社會生活。
生動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愛情故事,逼真的權力鬥爭,入微的生活細節,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之成為中國農村改革歷史的生動寫照。
原書名: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