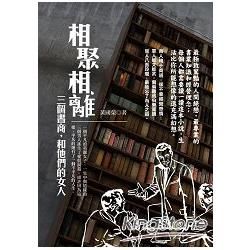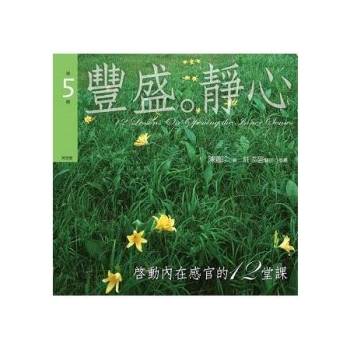第一章 回家
莫望山喊了一聲媽,立即就尷尬在大門口。讓他尷尬的不是他與這家人之間的陌生,而是他媽滿臉的苦笑和難堪。他後悔來到這門口,讓他一時進退兩難。
莫望山上午十點一刻走下火車。爸媽離婚,是他們都重又再婚後,姐姐寫信告訴他的。插隊離開家,回家不再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一趟有一趟不同的心酸。如今,他成了衙前村最後一名知青。他是個男人,不能眼睜睜看著老天爺這麼擺佈他們一家三口的命運,他堅信唯有他回城,才有可能重新創造他和她們母女倆的未來。他回來了,可他已沒有落腳安身的家。他知道媽現在這個家不可能收留他,但他還是決定先來看媽。
他媽現在的一家人正準備吃飯。莫望山從那個伯伯和他的兒子、兒媳、女兒還有孫子的目光
裡看到了自己的落魄,在他們眼裡,他是個叫花子。那位伯伯連請他進屋的話都沒能像樣地說出口,而向兒子和兒媳投去懇求。看老頭那窩囊相,媽的苦笑和難堪便不難理解。那位伯伯沒得到兒子兒媳恩准,勉強地說要不要吃了飯再走。莫望山心裡在笑,他腳還沒跨進門就說走,要不要?問誰呢?是人問的話嗎?看他兒子兒媳那樣,就算桌子上擺的是山珍海味,他也絕不會摸他們家的筷子。媽走出這個家的門,才恢復成他的媽。兒子永遠是媽的孩子,媽一出門就不顧腳下的地只管側著臉盯著莫望山看,好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兒子。媽看到兒子雖然還是理著那種平頭,但人壯了。鄉下不光強壯了他的身子骨,還給他骨子裡注進了不屈的威嚴和兇狠。莫望山看出,他不留下來吃飯,媽是高興的。兒子就是兒子,莫望山可以不計較他們對他是冷還是熱,但他在乎媽在那裡開心還是不開心。「媽,您過得好嗎?」「這把年紀了,還什麼好不好的,過一天算兩個半天。」「您別忘了,您還有我這個兒子呢!」莫望山下意識地把手伸向自己胸前的口袋。他媽說,「兒啊,那時你在哪裡呢?」
莫望山伸進胸脯的手又縮了回來。是啊,那時他又能幫媽什麼呢?這時他也沒法把手伸進口袋去,那裡面是有錢,整四百塊。他們家的積蓄只有五百塊,華芝蘭全給了他,臨走莫望山又抽出了一百塊,華芝蘭和莫嵐還要過日子。他的手指觸到錢時才想起,這錢是華芝蘭讓他帶回來派用場的。看到可憐的媽,想給媽一點,可他一想不能,這錢另有重用,他只好愧對自己的媽。「我算個什麼兒子!」「哪能怪你呢!回城就好,回城就好。」「還不知道知青辦批不批呢。我沒有事,您自己多保重,別委屈自己,有什麼事跟我說,如今我回來了。」莫望山說得母親掉了淚。
莫望山沒一點回家的快樂。窗外這個喧鬧的都市讓他陌生,陌生得叫他不敢相認,陌生得讓他難以融入,這裡的一切似乎都與他無關。這座城市養育了他,給了他十九年幸福的歲月。命運把他帶到了那個衙前村,他給了衙前村十五個春秋,衙前村給了他十五年艱辛。十五年,人生一個相當的生命段落,他幹了什麼?他得了什麼?空空而去,空空而回。他無奈地搖搖頭,搖斷自己的思想。「爸。」莫望山背著背囊走進自家的門,他爸現在的一家剛吃完飯,父親悠閒地坐椅子上剔著牙,隨便應了句,「回來啦。」彷彿莫望山是剛出門去打醬油回來。在廚房洗碗的阿姨聞聲,倒是立即讓那位毫不相干的妹妹給莫望山端來一杯白開水。「是回來看看,還是長住?」父親若無其事地問。「打算回城。」莫望山肚子很餓,但他這時還顧不得肚子。「回城?家裡可沒地方住啊!」莫望山端著水杯,傻著兩眼看父親,他不相信這會是他爸說的話。成千上萬的人一起下鄉的,人家父親傾家蕩產想盡一切辦法,利用一切能利用的關係,把兒女都弄回了城。早回城的房子都分到了,有的還當了官。他自己兒女的事不管,只顧謀劃自己的日子,喜新厭舊,拋棄了媽,又弄了個年輕的。把人家的女兒當親的養,自己的骨肉倒往外推,開口就說沒地方住。他可以不計較那阿姨的態度,也可以不管那位既不同爸又不同媽的妹妹的感受,也體會到自己妹妹和妹夫的難處,可你是爸,我是你親生的兒子,這裡的財產有我的一份!莫望山受不了了。「你還沒有宣布我不是你的兒子!這房子有我的一份!」莫望山忍無可忍,手裡的杯子和話一塊兒落到地上,他轉身衝出了自己的這個老家。
莫望山的心裡好痛,離開衙前村時,他沒法讓莫嵐停止哭喊;華芝蘭在離婚過程中,超乎尋常地平靜,讓他很不安;回來見母親寄人籬下,蒙受屈辱,叫他抬不起頭;自己婚離了,知青辦是不是就能批准他回城還是個未知數。三十四歲的人了,他卻成了沒人管的孤兒。莫望山忍著眼淚衝出門,他好像聽到父親追出門吼他,問他要上哪去!他心裡更酸,眼淚止不住湧出,他不去抹它,任它在臉上流淌,兩腳堅定地朝前走,他沒回頭看身後的一切。其實追出門的不光他爸,還有那個阿姨和那個既不同爸也不同媽的妹妹,還有他的妹妹和妹夫石小剛。火發了,想收也收不回來。莫望山在一家小麵館裡吃了碗陽春麵。莫望山很餓,但吃得很慢。他一邊吃一邊盤算,指望不了天,指望不了地,一切還得靠自己。吃了麵,喘口氣,他直接上了知青辦。當莫望山看到那個院子的大門時,心裡不免緊張起來。這裡他並不陌生,當年下鄉時,他們就是在這裡辦手續的。後來他又來過三次,三次的印象讓他終生難忘。
第一次他領著妹妹莫嫵媛走進這裡,沒有一點準備,只是想碰碰運氣摸摸底,當時已有三分之一的知青以「特困」、「疾病」等種種理由回了城。接待他們兄妹的是位中年男子,態度還算和氣。「你們有什麼特殊情況?」「我們爸媽離婚了。」「離婚算啥特殊?爸媽離婚的多著呢!特困是指特殊困難!」「我和妹妹兩個都在鄉下。」「家裡再沒有兄弟姐妹了?」「姐姐出嫁了。」「還是啊,家裡不是還有子女嘛!」「出嫁了,不在父母身邊,我們兩個應該可以先回來一個吧?」「現在的政策是特困戶和重病可照顧。兩個下鄉算啥特困呢?人家三個四個的都有呢!」莫嫵媛在背後拽莫望山的衣服,莫望山捏住妹妹的手。「我爸沒有人照顧。」「你爸多大年紀?」「五十三。」「幹什麼?」「教師。」「有什麼病嗎?」「病?氣管炎。」「五十來歲的教師,正當年。氣管炎算什麼病?還有你姐嘛!」「姐姐不在家住。」「不在家住也在城裡啊,也不能算身邊沒有人啊,回去吧,好好幹,廣闊天地嘛,同樣有前途。」莫嫵媛用一根食指摳莫望山的手心,她一直躲在哥哥的身後,沒說一句話。第二次莫望山來之前跟別人學了些經驗,聽說一家兩個下鄉可以先回來一個。他提著兩瓶「五糧液」先上了那位接待過他的官員家,此人已經升了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態度還是很和氣,他說是有這個精神,但原則還是先照顧特困戶。莫望山比原來聰明多了,他說妹妹在學大寨的工地上摔壞了腰。副主任問有沒有醫院的證明。莫望山說沒有帶。副主任就告訴他,醫院證明是一定要帶的。莫望山就千恩萬謝地把酒留下告辭,副主任還是客氣讓他把酒帶回去,莫望山當然不能這麼做。莫望山求了同學,同學求了他爸,同學他爸再求了同事,莫望山給妹妹弄到了一張腰椎錯位後遺症的證明。妹妹就順利回了城。第三次是華芝蘭拖著他一起來的。那位副主任已經當了主任,他親自接待了他們夫妻倆。莫望山給主任帶了一些田七、天麻,說是土特產。主任沒有客氣,說土特產他可以收,他認這些東西。整個會見只見華芝蘭說話,主任聽了說事情有些麻煩,在當地結了婚,又有了孩子。現行政策是孩子的戶口隨低不隨高,父母雙方哪一方是農業戶口就隨哪一方,這樣回城等於拆散了家庭,加劇了城鄉、工農之間的矛盾,也影響到黨群關係。
莫望山來到門前,不由得一驚。他睜大眼睛仔細看門牌,沒有錯,愛民街七百四十八號,可牌子不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辦公室」換成了「市體制改革委員會辦公室」。傳達室老大嫂給了他一頭霧水,說可能是撤銷了,也可能是搬家了,具體情況說不準。莫望山給自己的神經放了假,迎著人迎著車馬走上街頭,身邊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全是一片茫茫。他沒有目標,也沒有方向,就這麼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走著,走得鬆鬆垮垮,郎郎當當。不時有人撞他碰他,別人回過頭來罵他,他只當沒聽見。此時,衙前村妻子女兒揪著他心。
夜幕剛剛一抖一抖落地,村子裡便當靜如一池死水。村東周家那隻貓在叫春,饑渴難耐的求愛呼喚,一聲一聲在夜空中嘹亮而尖厲,刺激著村前村後的角角落落。莫望山默默坐在舊竹椅上,把自己按在《今夜有暴風雪》裡。華芝蘭埋頭批學生的作業,只是床上睡得香甜的女兒莫嵐,不斷讓她分心,不時分去她的目光。屋子裡的空氣有些黏稠,稠得有些沉悶。寂靜中只有華芝蘭醮筆劃過紙面的哧啦聲,是對勾,是叉,清晰可辨。除此,間或也夾進莫望山一兩聲翻閱雜誌的聲響和莫嵐的夢囈。「望山,咱們離吧。」華芝蘭沒有抬頭,也沒有看莫望山。「咱們?……」莫望山的目光慢條斯理離開雜誌,把眼睛投到華芝蘭的臉上。「嗯。咱們。」華芝蘭仍埋頭批著作業。「離?」「離。」華芝蘭十分平靜。他們彷彿在商量一件生活瑣事,好比說,望山,把襯衣換下來洗洗吧?噢,換。望山,咱們吃飯吧?噯,吃。望山,咱們睡吧?好,睡。莫望山把眼睛移到華芝蘭的臉上,她眼睛裡閃著晶亮,她的話說得這麼軟綿,鼻子卻在發酸。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相聚相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5 |
小說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相聚相離
最極致驚豔的人間絕戀,最專業的書業知識和經營理念;
每個人都需要讀一讀這本小說,生活比你所能想像的還充滿幻想。
商人精於商道,卻不會經營感情;
軍人能文能武,偏偏難遇伯樂賞識;
官人八面玲瓏,最後忘了為人之道。
一個平凡的美麗女子,一生中與這樣的三個男人產生了愛恨糾葛。或許因為這樣,平凡的她有了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瘋狂愛她的,她只是心存感恩;
欺騙她的,她一生牽掛;
有情無愛的,她卻始終放不下。
十五年前,三個知青在衙前村分別;十五年後,他們又在江都市書業重逢。命運就像是導演,讓這三個男人為了同一個女人,出演了一場人間話劇。
作者簡介:
黃國榮
男,江蘇宜興人。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農民家庭出生,務過農,幹過社教工作隊員,當過兵,做過編輯,任過出版社副社長,專業技術職稱編審。
1978年開始寫小說,發表出版文學藝術創作500餘萬字。
中篇小說《履帶》、短篇小說《山泉》獲全軍文藝新作品奨二等獎;
長篇小說《兵謠》、《鄉謠》獲全軍文藝新作品獎一等獎;
長篇小說《蒼天亦老》獲總政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
長篇小說《鄉謠》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14集電視連續劇《兵謠》獲飛天獎;
32集電視連續劇《沙場點兵》獲金鷹獎,2006年最佳收視率獎、「五個一工程獎」、金星獎。
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發表出版經營管理理論文章10餘萬字。撰寫《圖書編輯學》、《出版經營與管理》教學講義。獲中國出版科研人庫證書,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客座教授。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理事,全國出版物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回家
莫望山喊了一聲媽,立即就尷尬在大門口。讓他尷尬的不是他與這家人之間的陌生,而是他媽滿臉的苦笑和難堪。他後悔來到這門口,讓他一時進退兩難。
莫望山上午十點一刻走下火車。爸媽離婚,是他們都重又再婚後,姐姐寫信告訴他的。插隊離開家,回家不再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一趟有一趟不同的心酸。如今,他成了衙前村最後一名知青。他是個男人,不能眼睜睜看著老天爺這麼擺佈他們一家三口的命運,他堅信唯有他回城,才有可能重新創造他和她們母女倆的未來。他回來了,可他已沒有落腳安身的家。他知道媽現在這個家不可能收...
莫望山喊了一聲媽,立即就尷尬在大門口。讓他尷尬的不是他與這家人之間的陌生,而是他媽滿臉的苦笑和難堪。他後悔來到這門口,讓他一時進退兩難。
莫望山上午十點一刻走下火車。爸媽離婚,是他們都重又再婚後,姐姐寫信告訴他的。插隊離開家,回家不再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情,一趟有一趟不同的心酸。如今,他成了衙前村最後一名知青。他是個男人,不能眼睜睜看著老天爺這麼擺佈他們一家三口的命運,他堅信唯有他回城,才有可能重新創造他和她們母女倆的未來。他回來了,可他已沒有落腳安身的家。他知道媽現在這個家不可能收...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
你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嗎?
你能走進同一時間嗎?
十五年前,三個知青在衙前村分別。聞心源去海防當兵;沙一天被推薦上大學,莫望山成最後一名知青。
十五年後,他們又在江都市書業重逢,出演了一場人間話劇。華芝蘭把大學名額讓給沙一天,沙一天把她肚子搞大又將她拋棄;官運亨通成老市長乘龍快婿,正飛黃騰達妻子反離他而去,啷鐺入獄還疑惑在夢中。
聞心源在部隊遇整編,為搞新聞放棄將軍夢,轉業誤入出版局大門,真誠為人深得沙一天妻子敬愛,德才兼備卻一直未遇上伯樂。
莫望山拯救華芝蘭於絕望,養育沙一天女兒如親生,與命...
你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嗎?
你能走進同一時間嗎?
十五年前,三個知青在衙前村分別。聞心源去海防當兵;沙一天被推薦上大學,莫望山成最後一名知青。
十五年後,他們又在江都市書業重逢,出演了一場人間話劇。華芝蘭把大學名額讓給沙一天,沙一天把她肚子搞大又將她拋棄;官運亨通成老市長乘龍快婿,正飛黃騰達妻子反離他而去,啷鐺入獄還疑惑在夢中。
聞心源在部隊遇整編,為搞新聞放棄將軍夢,轉業誤入出版局大門,真誠為人深得沙一天妻子敬愛,德才兼備卻一直未遇上伯樂。
莫望山拯救華芝蘭於絕望,養育沙一天女兒如親生,與命...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回家
第二章 老友重逢
第三章 以退為進
第四章 一物降一物
第五章 走前人沒走過的路
第六章 在強強不過光陰
第七章 不管白貓黑貓,捉著老鼠的就是好貓
第八章 江都書市
第九章 再尋出路
第十章 書才是里程碑
第十一章 決賽前的運動員
第十二章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第十三章 沙灘上的高樓
第十四章 政治搭台,經濟唱戲
第十五章 人出於眾,人必誹之
第十六章 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
第二章 老友重逢
第三章 以退為進
第四章 一物降一物
第五章 走前人沒走過的路
第六章 在強強不過光陰
第七章 不管白貓黑貓,捉著老鼠的就是好貓
第八章 江都書市
第九章 再尋出路
第十章 書才是里程碑
第十一章 決賽前的運動員
第十二章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第十三章 沙灘上的高樓
第十四章 政治搭台,經濟唱戲
第十五章 人出於眾,人必誹之
第十六章 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國榮
- 出版社: 知青頻道 出版日期:2014-07-04 ISBN/ISSN:97898656991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25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