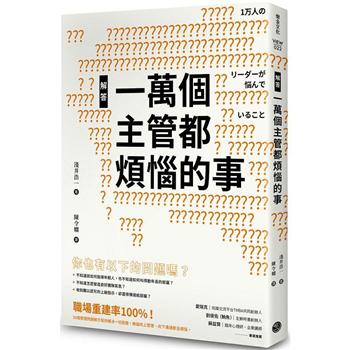柳依紅是個充滿魅力的美麗女人。她有著姣好的外貌、詩人的灑脫和伶俐的口齒。她遊俠一樣行走在當代都市中,對男人有著非同一般的捕獲力,更令男人感到誘惑的是她纖細腰肢上的那一朵嬌豔欲滴的玫瑰。
人前,她是頭頂耀眼光環的著名女詩人;人後,她是在刀尖上舞蹈的黑色玫瑰。她渴望愛情又踐踏愛情,追求理想又玷污理想。她追逐名利,遊戲在幾個男人之間,極力維護著一個巨大的秘密,幾近崩潰,又幾度綻放。滾滾紅塵中,她是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的另類女人,終於有一天,她苦苦維繫的秘密破殼而出……
末日來臨之際,她忍不住捫心自問,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她如同飛蛾撲火般的一生,再次引領我們探尋了人性的高度和深度。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從油菜花到罌粟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39 |
小說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大眾文學 |
$ 315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從油菜花到罌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