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東野圭吾《嫌疑犯X的獻身》共同入選愛倫坡獎年度最佳小說獎
‧獲頒南方獨立書商聯合大獎(SIBA Book Award)
‧入選巴瑞獎年度最佳小說獎
‧日本十大《文庫版最佳翻譯推理小說》選書
‧連續三部作品入選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最佳小說獎,美國當代推理新天王約翰.哈特最新代表作
你可以「重新開始」,但代價是──
親手殺了這個待你宛若父親的男人。
鐵山之家是在北卡羅萊納州山區的一所孤兒院,對麥可和他的弟弟朱利安而言,這是一個黑暗的地獄。自小被遺棄於河畔的兄弟倆,從來沒有遠離過麻煩,特別是朱利安。飽受欺凌的他忍無可忍殺了其中一名長期欺負他的院童,為弟弟頂罪的麥可遠走鐵山之家,兄弟倆的人生從此踏上不同的道路……
十餘年後,麥可成為紐約黑幫的頂尖殺手,但當他遇到美麗又純真的艾蓮娜,教會他愛的意義與力量,他所努力建立起來的人生就全被弄亂了。他希望能有一個全新的開始,希望有機會跟艾蓮娜建立起一個家庭──那是他和朱利安從來未曾擁有過的。但事情由不得他決定,要退出黑幫沒那麼簡單……
他願意重回地獄,以求讓她平安。
進入地獄,然後焚身歸來……
麥可決心保護他所愛的人,偷偷帶著艾蓮娜──她對麥可過往的犯行毫無知情,也不知道麥可為她惹來的危險──回到北卡羅萊納州,到他出生的地方,去找他失散多年的弟弟。而此時收養弟弟的參議員宅第內發現一具淒慘屍體,死者是在鐵山之家欺凌朱利安的那夥人之一。朱利安會是兇手……?
重重的欺詐和暴力,將會無情地帶領他回到他一生努力逃離的地方:鐵山之家……
當代最銳不可當的文學奇才約翰‧哈特,創造了麥可這位特立獨行的豐富角色,當他宛如暗夜的孤獨幽靈般巡遊在黑白兩道,所有人性的殘酷和善良、背叛和恐懼也將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而麥可要對抗的不只是兇手,更是自己的信念,也讓暴亂殺戮中閃現一絲的愛與善,彌足珍貴!
名人推薦
如果你渴望鮮活、完美、生動,讓你充滿同情的小說,那你絕不能錯過約翰.哈特的作品!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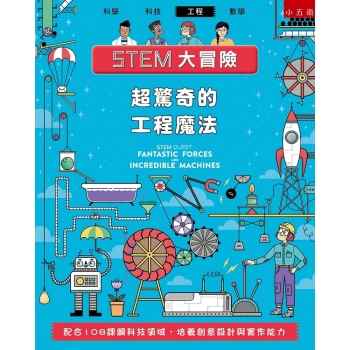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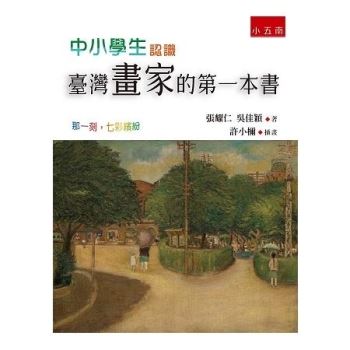








當人生有了「不能說的真相」,有時心存懷疑更能讓人繼續活下去,因為知情反而容易使人崩潰。 原本以為「鐵山之家」的劇情只是充斥著濃厚黑幫冷冽、殘酷與暴力的氛圍,或一個殺手老哥如何解救那殺人老弟脫離犯罪的老梗題材,沒想到溫暖與感動的結局卻讓人心頭一熱。高度的懸疑引領著讀者隨著馬克一步一步揭發事情的真相,處處看到人性的善惡、命運之神的愚弄、親情與愛情的掙扎。閱讀完有著一股異於其他小說奇特又強烈的感覺,劇情從頭到尾在闔上的那一刻,前後看似毫無關係,仔細回想卻又發現彼此緊湊而連貫,尤其轉折處的精彩更是筆墨無法一次說明詳盡。 一開始馬克被黑幫窮追不捨的迫殺與逃亡,經過努力保護愛人與親人,到最後意外揭開了自己神秘的身世,再回到一切故事的原點—「鐵山之家」,處處緊扣著主題。而馬克從一個超級「殺手」變成嗅覺敏銳的「偵探」,看似冷血、殺人不眨眼的他卻有保護愛情的溫柔與捍衛親情的堅定與犧牲,一人主導並支配著整個故事步調的節奏,也不得不佩服作者在整部作品架構上的精采巧思與用心,為讀者徹底帶來一場與眾不同又大呼過癮的閱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