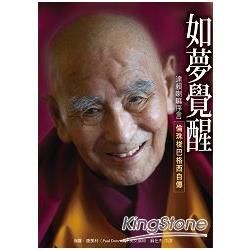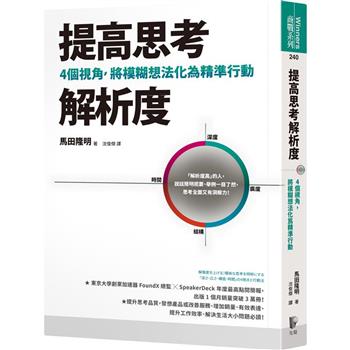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這位我已認識超過五十年的學問僧——倫珠梭巴格西,正是一位如此具格具德的老師。梭巴格西做為一位學者和學者的老師,同時也是好幾百位西方學生的佛教導師與帶領者,以及自身更是純淨僧人傳統的持有者等等的貢獻,他一直都是圖博佛教文化的典範代表。我在拉薩接受格西學位考試的最後階段中,他是少數被選來在我辯經時向我提問的最優秀學僧之一。」 ——達賴喇嘛序言
如果我們用心去體會領略梭巴格西在追求證悟過程的持戒安忍精進苦行,就能得知他如何能以自在的禪定智慧布施給與他有法緣的隨學弟子,即使他肩負把藏傳經院教理佛法傳入西方世界的艱辛使命,他一樣能自力任運展現證明解脫行道成就的究竟真實。
作者簡介:
倫珠梭巴格西,1923年生於博圖藏區香縣。十歲時進入甘丹秋廓寺受沙彌戒,十八歲前往拉薩進入色拉寺傑學院藏巴康村受教,年紀尚輕時就開始教授佛法。1952年被選派為第四世康壟祖古的親教師,1959年完成拉然巴格西學位考試前,被選為達賴喇嘛考格西時的七位辯經對手之一。同年因中共入侵圖博,逃到印度,1962年被圖博流亡政府授予第一級拉然巴格西學位,隨後達賴喇嘛指派他帶領三位年輕轉世仁波切到美國紐澤西學習英文。1967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佛學研究所邀請他前往任教,使他成為美國西藏佛學研究的主要推動者,指導出許多的佛學博士。他於1997年以榮譽教授的身分退休,繼續出版有關圖博文化和宗教的專書。梭巴格西在麥迪遜市外附近創建了鹿野苑佛教中心,由於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講經邀請,梭巴格西的足跡遍及全球,是少數在圖博接受完整佛法教育而仍然住世的偉大學者,備受國際尊敬推崇的解行並重三學兼優現代高僧。
譯者簡介:
翁仕杰,台灣嘉義縣人,1962年生,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畢業後,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佛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西藏佛學八年。專長西藏佛學、當代西藏研究及宗教社會學。前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推動執行台藏宗教文化交流與人道援助工作多年。現專注翻譯佛教典籍,並於相關佛教機構教授藏傳佛法。擔任達賴喇嘛2009年訪台公開演講的中文翻譯。著有《台灣民變的轉型》一書,譯有《綻放心中的蓮花》、《四聖諦》、《喜樂泉源》、《剋毒孔雀》、《穿越生死》、《達賴喇嘛教你認識自己》、《在工作中悟道》、《挖到空》、《開心:達賴喇嘛的快樂學》、《度母:解脫自在的秘密》、《逆境中更易尋快樂》、《智慧的階梯》、《如夢覺醒》等書。
推薦序
【中譯者導讀】
任運安忍於善德法智的自力現證解脫行道
這篇導讀的題目看似冗長而艱深,也許你會問為何不用幾個明顯易懂鏗鏘有力的字做標題就好,反而要把這一連串佛法專門術語堆疊在一起,連讀起來都有點拗口呢?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本書的副標題「倫珠梭巴格西自傳」的意譯:藏文的「倫珠」是任運成就的意思;「梭巴」是指安住忍耐;「格西」就是大家熟知的善知識,意指擁有善德及佛法智識的修行者;「自傳」當然就是自述的行傳,然而這裡所說的行傳並非是一般人的生平紀錄而已,而是描述已被公認為大師的作者本人依自身修學之力而現證的解脫行道。我認為這個標題可以做為認識倫珠梭巴格西仁波切一生行誼的總括綱要,你只要讀完這本書,應該也能自然而然感同身受。
本書是作者倫珠梭巴格西在他八十幾歲時回顧自己一生修學歷程所敘述的傳記。解脫行傳(Namthar)在圖博文學的類別中有其特殊性,通常都是大師的弟子依親身所見,加上廣泛蒐集可信聽聞而寫成的傳世記事,等同於漢傳佛教中的高僧傳。在藏傳佛教的傳統中,由他人寫作的解脫行傳著重出生、入道、證悟、弘法、圓寂等神異非凡事件的描述,有時難免有基於深切信仰的誇大描述,難以顯現傳記主角的內心覺受與觀點。但是由於自傳是作者自述自著,不只在客觀事實上比他人寫作的傳說要有更高的可信性,而且也包含了作者自顯的心路歷程,除了是記載某一段重大歷史事件的史料文獻外,也可作為相應於其所信仰的宗教真理之外顯行為與內在開悟的見證,而且具有鼓舞讀者走入正確修道方向的教授功能。倫珠梭巴格西這本自傳《如夢覺醒》就是蘊涵上述諸多價值的一本現代聖者自述行傳。
現年已達九十二歲高齡的倫珠梭巴格西仁波切是我的佛學指導教授與根本上師。我於1991年進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佛學博士班研究所就讀,由於選擇攻讀藏傳佛教,自然就成為梭巴格西的學生。其後八年親炙了格西既親切又嚴謹的身教言教,在他從頭教起誨人不倦的持續指導之下,才使我對藏傳佛教的博大精深有所領略,尤其對格魯派解經釋論的理性嚴謹學風的了解,更是從格西樸實謙遜言行一致的悲智中得到最直接的印證。透過格西睿智耐心的逐步傳授,讓我從原本對藏傳佛教的一無所知,慢慢體會到這個古典經院教理傳承的浩瀚無邊。
由於文化背景和先前學術訓練的差距,我這段到西方取經的求學經驗是一個顛簸辛苦的過程,在過完摸不著邊際的第一年新生震撼教育後,我也曾萌發轉學的念頭,但由於格西沒有放棄我這個資質魯鈍的學生,因而我從一位格西在大學指導的研究生,被他攝受為親近的入室弟子,進而後來回國後有機會把他的純淨寶貴教法以中文譯著傳入漢地來,這真是我個人這一生最可貴的善緣和最大的福報。因此這次有此榮幸再把他此生自現的解脫行傳譯成中文,我心中充滿難以言喻的感恩之情,同時也有誠惶誠恐的任重道遠之責,所以我也曾經躊躇不前,不敢以快筆將格西先前在圖博苦學苦修後來勞心勞力把佛法傳到西方的先鋒開創法業迅速譯完。我試圖把翻譯他這本自傳的工作,當成是我更加深入認識我的根本上師一生修行歷程的體悟之旅,是上師慈悲地再給我一次修習上師瑜伽的機會。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心中總是有一個念頭:既然這本自傳是他走向解脫的精神旅程,在已述說的故事情節之下,必然埋藏有待深入探索的證悟印記,以及許多他沒明說的隱微深義。其實動筆的困難之處不在文字的翻譯,他所講述的故事內容也很清楚明瞭,沒有任何神祕隱晦之處,從他有記憶以來的童年依時間順序講到他的現狀,最後還交待了他自己在圓寂以後對未來的期望。但這些表述的言詞背後隱藏的深意是什麼?他所敘說的故事反映了他多少內心的證悟?這些都是我們不能視之為當然的依文單面認定。就如格西自己在自傳中所言:「看起來這裡的美國人也只相信他們雙眼親身所見的事物,如果自己沒看過,那就一定不存在,我們圖博人不這樣看。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我們一直都可以看到存在於這世界上的每件事物,這世界上有許多事物是我們無法看見的。」這段話也適用於了解格西的一生。我們能從格西自述的生平故事中看到了什麼深刻的啟示?然後又有多少被我們輕忽錯過的面向?
所以為了掌握梭巴格西自傳的深層意義,我們不能光以現代主流實證科學思潮,只視這本傳記為一位到西方傳法的圖博聖僧所撰述的人生紀錄,可以做為在研究藏傳佛教現代弘傳史時引用參考的某一種客觀史料,或是把這本具有另類趣味的書當做富含異國風情引人入勝的精神旅遊文學讀本,雖然本書的確具有這種功能與價值,這也是格西顯現人間性的其中一個面向。
梭巴格西在本書中曾自謙說他不是一位偉大的瑜伽士,也非偉大的修行者,但是他喜歡教導佛法,他很高興能跟有興趣學習佛法的人們分享微薄的佛法知識。其實正因為有這種謙遜與奉獻的態度,才正足以證明他已證悟實現了佛法的本質。格西說他的老師教導他過去印藏佛教偉大修行者的故事,這些聖者是獻身宗教善德生活的典範,他從這些故事中學到了竭誠奉獻和謙遜才是構成真實宗教修行生活的核心本質。所以用佛法的修道理論去了解梭巴格西的一生不啻是最適合的觀點,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進入梭巴格西做為一位藏傳佛教高僧所具有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去了解他的一生,才能更貼近他那和而不同且圓融自在的高超聖潔人格特質。
根據世人對宗教的認識,神聖與凡俗是兩種存在於世間的基本範疇,人們信仰宗教進行修道所求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超凡入聖,這也是修學佛法的最終目的。由於聖人與凡夫在修道上屬於不同的向度與層次,因此在佛教的教理論述與修行體制中,出家為僧都被認為是由凡轉聖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徑,特別是在首重出家主義的藏傳佛教中,成為僧人不但是個人向上流動的追求,同時也為社會所讚賞和期許,進而可以取得圖博文化最高價值的地位。佛法乃是痛苦輪迴的唯一究竟解脫之道,這早已是圖博人千年以來根深蒂固的認識與信仰,所以有幸出家修行被圖博人視為無上的福報,這用格西在本書一開頭所說的話就可以證明:「直到大約十歲以前,我經歷了許多不幸,諸如意外事故、疾病以及好幾次差點死掉的經驗。但是在我開始過修行的宗教生活以後,情況就有所改變。當我進入佛寺後,馬上就變得更健康更快樂,而且開始出現各種新契機,這對一個像我這樣當時出生於圖博鄉下的普通人而言,真是不可思議難以想像的事情。」
這種依戒、定、慧三學為學習主題的僧院教育是藏傳佛教繼承偉大的印度那爛陀學風的延續,圖博從八世紀初建立桑耶寺以來,經過一千多年千錘百鍊的累積發展,到了二十世紀梭巴格西出家時,大型佛教寺院已經是典章兼備的完善高等教育機構,尤其以格魯派三大寺的嚴格聞思修訓練最為著稱。進入寺院修學佛法,經由精進苦行積聚福慧資糧,進而成為顯密融通的聖僧大成就者,是圖博人最嚮往推崇的人生目標,這當然也反映了僧院體制與佛教文化在圖博歷史與社會中所佔有的至高地位。因此以僧院體制所規範安排的修學次第來理解梭巴格西的修道過程,就能精準地把佛教的教理論述和教學體制融通為一體,了解由凡入聖是一個漸進轉化的修行過程,而寺院教育的目的就在於提供發心修行者最佳的學習環境。
梭巴格西於1923年出生於後藏日喀則附近的香縣,是一對務農中年夫婦的獨子。格西說他從大約十歲左右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僧人,一直向父母要求去佛寺出家。每當他拜訪完佛寺回家後,在和村子中的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時,他會扮演寺院糾察師的角色,要求其他小孩的言行舉止要像僧人一樣,他甚至去找了一些紅色或黃色的布做成某種僧袍穿在身上。其實這已經顯現他決心入道修行的徵兆,基於過去生純淨出世修行的習氣,他對世俗在家生活完全沒有興趣,心中想的就只有想要出家為僧,這是他的純淨出離心。他父親支持他的決定,隨後他在藏區香甘丹秋廓寺出家,以他的舅舅為寺院根本師,此是他入道的開始。以下我以大事紀的方式摘要整理梭巴格西的出家修道的重要里程碑:
一、1933年十歲發心出家,先在地方性的香甘丹秋廓寺受沙瀰戒,接著背誦祈願經文,然後開始學習基礎因明的辯經方法,因為成績優異,十八歲時被推薦到拉薩的色拉寺深造。
二、1941年進入色拉寺傑學院的藏巴康村學習,於三年後過二十歲成年時受比丘戒,修習藏傳佛教各教派通學的顯教五部大論,由於品學兼優獲聘為康壟仁波切親教師,加上出類拔萃的辯經表現得到小明學者與大明學者的榮譽,進而快速被拔擢到將會取得第一等拉然巴格西的拉然班中,並於1959年達賴喇嘛的格西考試中,榮獲代表色拉寺傑學院向尊者提問的辯經人選。
三、1959年三月底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在達爾豪西難民社區居住三年。1962年圖博流亡政府首次舉辦的格西考試中得到第一等拉然巴格西的第一名,同年成為被達賴喇嘛派往外國的第一位格西,抵達紐澤西州的美國喇嘛佛寺學習英文。
四、1967年受邀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教授藏文,也是第一批在西方世界大學中教授藏文與藏傳佛教的圖博學者之一,其後升任佛學研究所的教授,更是在美國無西方博士學位而擔任大學教授的第一位圖博人,1969年在麥迪遜市成立甘丹大乘佛教中心,舉辦首次結夏安居暑期佛學課程,1979年首次邀請達賴喇嘛到威斯康辛大學訪問,1980年購地成立鹿野苑佛教中心,1981年邀請達賴喇嘛在威斯康辛麥迪遜舉行首次西方世界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1997年退休成為榮譽退休教授,2004年開始出版最詳盡的五大冊《菩提道次第》英文注解,2009年邀請達賴喇嘛為其住持的鹿野苑寺新建大佛殿開光,迄今仍然繼續出版英文佛學著作。
上述梭巴格西的四個主要修道階段,若以居住地點做區分,則分別是藏區、衛地、印度和美國。若以僧人的身分做區分,則是沙彌、比丘、格西及大學佛學教授兼住持。如果我們對他在四個階段的主要修行活動內容加以分析,則和修道論中的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及無學道的五道架構不謀而合,因此以四個修道階段來看待格西的一生的證道歷程,似乎擁有一定程度的相應相契:
一、第一個遠離世俗生活的沙彌身分階段正好是他在出家母寺香甘丹秋廓寺的預備期,在這個階段中他主要的訓練是遵守僧人戒律、背誦祈願經文和學習基礎辯經方法,相應於資糧道的修學內容。
二、第二個持俱足戒的比丘身分階段是在色拉寺學密集經辯論及專注禪修的精進期,由於他是非常傑出優秀的學問僧,所以早在二十多歲還是就讀於中觀班的學生時,就成為其他年輕僧人和一位小轉世祖古的老師,相應於煖、頂、忍、世第一的加行道訓練過程。
三、第三個取得第一等那然巴格西的階段,恰好是從圖博逃到印度成為難民的時期,在這個原本支持他修學的傳統政教體制全面崩解又在異國辛苦重建的過程中,是一段破除恆常實有自性見的深刻洞見以及親證性空即緣起的無二體悟,相應於見道位的空性現證。
四、第四個以佛學教授及佛寺住持角色在美國弘傳藏傳佛法的階段,是累積純淨福智功德與地道證量持續增上的弘法期,梭巴格西把純正嚴謹的藏傳佛教教理哲學傳入西方世界最高學府中,訓練出二十幾位佛學博士,開創美國藏傳佛學研究的新法脈,並且出版了多本重要根本論典的傳世著作,相應於修道位的法行事業。
除了用這個五道的修行架構概略點出梭巴格西這一生的重要修行成就以外,我還想從本書格西自述的內容中挑選出他在不同階段中重要經歷的內心感受,做為他本人證悟境界的佐證。由於這是他自己親口所說的話,因此不會有過度詮釋的疑慮,而且聽起來更有親切的感受。
梭巴格西談到他最早的一位上師根莫朗老師對他的影響,幫助他成為一位守規矩的認真學生。格西的舅舅在夏天和秋天常常得為了寺院的事務出差,他就變成孤家寡人,雖然年紀尚小,但是必須自理生活。由於從根莫朗老師給他個人的教導和忠告中學習,他的生活態度虔敬嚴謹,鍛鍊培養出很強的自制力。他會自動去找一個安靜無人的地方讀書背誦經文,並且把僧房和自己都照顧得很好,所以每當舅舅回家時總是很滿意。他說:「我的舅舅利用他離家的時間考驗我,但我證明自己是一位負責而勤奮的人。這讓他對我產生信任感。雖然我那時候年紀還很輕,十八歲左右而已,但我舅舅覺得我有能力照顧好自己。我確信這有助於他做出送我去色拉寺的決定。」
由於梭巴格西在甘丹秋廓寺聽聞色拉寺中有許多位出身母寺的大格西,這些有卓越成就的高僧是大家羨慕尊敬的榜樣,所以他在年紀尚輕時就心嚮往之,立志自己也要成為一位三大寺的高階格西。他了解自己去色拉寺深造是要過嚴格的修行生活,是為了受更高深的經論教育而成為大修行者,不是為了世俗性的舒適或利益。他說:「在色拉寺中並不存在任何世俗生活所希冀欲求的東西。從大多數人的角度而言,我們的食物、衣服和生活條件也許看起來都非常不舒適,事實上應該說是很可憐的。但是我們生活的重點在於佛法,日日夜夜我們都致力於佛法的活動,這是出家過著僧人生活的目的。我們從這些事情中得到很多的滿足,甚至從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覺得這樣。我們的衣服不見得乾淨,食物也只是普普通通,品質也沒有很好,我們喝的酥油茶也只比熱開水要好一點而已。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很不容易,甚至連燒個開水也要費一番功夫。但是投入宗教修行而得到的快樂與喜悅,使我們度過難關。」
三大寺的教育重點強調哲學義理的學習,但這只是寺院生活中訓練的一部分而已,學僧從事研讀經論和辯經等這些事情的同時,也必須致力於淨除障礙和增長功德。格西指出這些研讀經論之外的修行也具有極大的意義,在法園中和同學進行嚴謹的辯論是累積智慧資糧的因,精巧的祈願、供養和修法則是累積福德資糧的因。還有遵守嚴格比丘戒律的要求,並不是一件需要有糾察師隨時在旁邊緊迫盯人才能做到的事。他說明僧人守戒的動機乃是:「出於奉獻忠誠之心才遵守規則的,而不是由於害怕被處罰的緣故而遵守。要緊緊盯住寺院內每個人的行為是做不到的,我們沒有警察,紀律只能從內而生。」梭巴格西坦言沒有任何的別人可以替我們自己修行,他一再強調僧人彼此努力競爭以獲得良好的教育,並不是為了得到學位、名聲和特權而已,而是努力增長修行上的進步。他說畢竟這才是過清淨出家寺院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圖。
這種安忍於解脫行道的強烈自覺,始終留在梭巴格西的心中。當格西成為康壟仁波切的親教師後,他再也不需要擔心修學資糧不足的問題,拉章會提供他日常生活中的所需。但是他卻沒有因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慶幸自喜。他心中反而會有這樣的省思:「我的生活變得舒適了,但是那些謙遜、簡樸和靈性的美好感覺卻改變了。這不必然是一件壞事,但是當然有所不同了。從某個方面來看,我先前過的艱辛樸實生活比較令人感到滿意欣慰,在那段辛苦的時間中,我可以把我所遭遇的困難當成一種修習安忍與出離心的方式,而得以增長功德福報。」但是他也很誠實地承認他真的不能講說他希望回去過先前較簡樸的生活,但卻對那一段時間的生活產生一種更大的敬意。他是以歡喜的心情回顧那段時間,而不會認為那是可憐痛苦的經歷,由於已經過去了而覺得高興。這種生活上的改善甚至讓他對他舅舅施予的恩惠產生更大的感激之心,由於有了舅舅從小的栽培,才讓他後來的順境變成可能。
因為梭巴格西自己的優異表現而成為色拉傑學院的精英學問僧,所以他在1959年被傑學院的住持院長選為達賴喇嘛格考試提問者之一。格西回憶說:「對我而言,這真是一次很殊勝美好的經驗。被選為尊者的考試提問人是一種很大的榮幸,但同時也是一件很嚇人的事情。我不想在所有的大學者面前出糗,當然更不想在達賴喇嘛尊者本人面前出糗。」格西和尊者的辯論科目是般若學,他要向尊者提問有關佛種姓的問題。格西解釋說大乘佛教認為眾生都有成佛的潛能,但那個潛能通常都睡著了,但可以經由研讀經論和修學法義而被喚醒,這就是所謂的「喚醒佛種姓」。幾年以後,當梭巴格西為了被尊者派去美國的事情去達蘭薩拉見達賴喇嘛時,尊者提醒他,這就是格西當年在尊者考試時問他的問題,尊者說由於當初格西問了他這個問題,所以格西必須前往美國去喚醒美國人的佛種姓。
在1959年3月10月圖博人民起義抗暴之後,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梭巴格西也和康壟仁波切逃出了圖博,這段爬過喜瑪拉雅山的驚險旅程真的如九死一生那樣的危急,大家可以在本書中讀到詳細的過程,我在此就不再贅述。等到梭巴格西最後安全抵達印度後,他們要面臨前所未見的艱辛難民生活。格西記得他們剛被安置在阿薩姆難民營的狀況,他說印度人沒收了所有的他們帶來的東西,然後給他們穿上很薄的印度式衣服。每個人都穿同樣的白色衣服,不管是僧人或俗人,男人或女人,通通都沒分別。由於他們剛剛從圖博出來,格西無法不記得那種氣憤難過的心情,他說:「在圖博,除了穆斯林會穿白色襯衫、褲子和戴小圓帽外,你決不可能看到圖博人這樣穿。現在我們看到每個人都穿同樣的白襯衫和白褲子,你就無法知道誰是僧人,誰是喇嘛,誰是官員了,甚至幾乎無法分辨誰是男人,誰是女人。我們迷失了,我們覺得很想哭。現在我們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力,我們受制於別人。我們的衣服被拿走了,我們的東西也被拿走了。」
印度和圖博官員告訴他們,現在已經流亡在外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可以舒服過日子,必須努力生存下去,食物配給只是幾個月的時間而已,在那之後,就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了。格西說他們不知道會被送往何處,而且也不知道到那裡後要做什麼。未來一切不可知,當下只有很可憐的感覺。所以格西感慨地說:「當我現在回顧那段日子時,似乎這些都不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感覺像是一場夢一樣,好像不曾真正發生過。有時候,我心中會懷疑,我現在的生活是一場夢,還是真實的?也許我人正在拉薩做夢,夢到這一切這麼多的事情。」
後來梭巴格西在達爾豪西的圖博難民社區待了三年,一邊繼續教導康壟仁波切,一邊準備他自己的拉然巴格西考試。在1962年格西雙喜臨門:一是他獲得拉然巴格西的第一名,是流亡印度後的第一位大格西;二是他被達賴喇嘛派去美國,陪同三位年輕喇嘛學習英文並且繼續教導他們佛法,成為第一位被尊者派到外國弘法的格西。這是當時人人羨慕的福報,儘管如此,由於由於格西謙遜的個性,一開始他還拒絕這項殊榮的任命。後來由於格西的上師赤江仁波切的鼓勵勸進,他才勉為其難的接受。他覺得自己的出身只是藏區香縣的一個貧窮人家,在大家都在過苦日子的時候,他可以得到至高的學位成就和遇到稀有的幸運機緣似乎是意外之事,格西相信這是他的業力使然。格西說:「不管我們遭遇苦難、問題或幸運的福報,這都是我們先前所做行動的結果。如果有一些壞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會責怪我自己,而非怪罪神明或別人。我是經由努力用功才得到我的職位,跟我的家庭出身或社會地位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我有福報的究竟原因當然是業力所決定的。我相信這完全是由於業力的關係,我才沒有被這些情況的後果直接影響到,我總算每次都躲得過。我幾乎好像一支羽毛,被風四處吹來吹去,最後終於被吹到很遠的地方去。事情真的就是如此,我並沒有做任何的計畫。」
梭巴格西於1962年到了美國以後,先在紐澤西待了一段時間,那時候他住在佛寺裡面,和在圖博時居住的環境一樣。後來在1967年剛到威斯康辛大學時,他不能再住在佛寺中,所以覺得完全迷失了。他追憶自己當時的心情:「對我而言,大學是一種全新的經驗……我就像一群黑烏鴉中的一隻白烏鴉,在校園中走動的所有學生和老師中,有一個與眾不同穿著紅色僧衣的人,但絕大多數人都只是對我感興趣,而且他們樂於助人,學生和其他大學中的工作人員幫助我很多事情,系上的秘書也同樣幫了我許多忙。」
在進入威斯康辛大學教導佛學後,他吸引了許多對藏傳佛教有興趣的年輕西方學生。這些美國學生都是剛開始接觸藏傳佛教的新手,所以格西只給像菩提道次第的基礎教導,儘管他們喜歡格西講解的一般顯教共同道,但是他們也同時在找尋一些更高深的特別教導,還有一些已經在別處得到這些灌頂和教授的學生,他們也想要從格西身上得到這些灌頂和教導。格西說他的學生給他許多壓力要他傳授灌頂,但格西從來沒做過,也從來不曾給過密宗的教導。格西語重心長地解釋:「他們只想要得到某些大灌頂,忽視事實上這些灌頂意味著必然要受這些嚴格的戒,他們只是對灌頂有好奇心。為了要接受密宗的灌頂,修行者必須受菩薩戒和密戒,這些戒比別解脫戒更高深和更嚴格,而別解脫戒本身就已經很嚴格了。但是不管如何,即使不是那麼嚴肅認真的學生也都受了全部的戒律。由於這個理由,我從來就不曾太強調灌頂和密法的教導。」
因為許多人對密宗有錯誤的理解,把禪修觀想對境的佛菩薩本尊當成像萬能的神一樣,好像只要向佛菩薩祈求會自動賜福,令他們滿願。梭巴格西也提到常常有人視他為擁有神通魔法的上師,以為只要向格西祈求,他們的問題就會自動消失。格西坦白承認:「這些年當人們來找我解決他們的問題時,我似乎沒有他們所要找的東西,他們對於我能提供給他們的東西不感興趣。如果有人前來尋找魔法療方,我會試圖告訴他們佛陀的教法,但他們都不會留下來很久,但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為了導正他們的誤解,格西不斷強調在修行佛法時一定要具備的基本正確態度,佛教的祈願和其他宗教的祈願有不同之處。他勸誡我們說:「當我們在做這些祈求時,並非向某一位神請求替我們做這些事情,而是在陳述自己要增長修行的渴求心,如此我們才有親自幫助其他眾生的能力。我們請求已開悟的聖者支持、引導和鼓舞達成這個目標。佛教允許我們請求其他開悟者幫忙,但我們要了解,究竟而言,覺悟只能靠自己達成,而且每個人都可以開悟。我們不相信不必經由自己努力而有可以幫助我們達成覺悟的他者之存在。」
梭巴格西是用以身作則的方式向學生展現,修行是必須靠自己精進努力完成的事。就連已經是一位已被大家公認是高僧聖者的他還是時時刻刻毫不懈怠。他跟我們分享他的修行秘密:「當我在旅行和教書之外的時間中,我儘量把更多時間用在修行上。當我同時在大學和鹿野苑佛教中心教導佛法時,我可用來實修的時間所剩不多。在我退休後,我完成了格魯派所推崇尊敬的三大密宗本尊傳承的閉關修行:密集金剛、勝樂輪金剛和大威德金剛。這是非常寶貴難得的機緣,我衷心感激能有機緣完成這些修行。」
梭巴格西回顧自己一生與眾不同的修行歷程,有了如下的省思:「雖然我後來所遭遇的處境和我原本只是一位色拉傑學院的學問僧時所想像的很不同,令人好奇的是以花時間從事實修這方面來看,我並未遜色多少。如果中國人沒到圖博來,我會擔任下密院的重要僧職,也許甚至成為甘丹墀巴,那麼我就不會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密集的修行。墀仁波切也告訴過我,雖然追求學問僧的成就很重要,但是增長實修的證量也一樣重要。我很幸運我這一生夠長壽,可以讓我活到有更多時間可以實修的階段。如果事情不是像這樣發展的,我真的又能得到多少的成就呢?」
格西以證道者的親身經驗指出,大家在學習了解佛法時必然會遇到一些很困難的地方,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容易就了解空性,但空性並非是佛陀唯一教導的佛法,佛陀還給了其他很實際可行的教導,簡單到每個人都能了解。格西引用龍樹菩薩在《寶鬘論》中說:「除非能夠完全清除愛執自我的見解,不然應該修行布施、持戒和安忍。」雖然只有經由直接證悟空性才能根除錯誤的我見,格西建議我們在修習空性見的同時,也應該修習這三種功德,這才是正確的修行。
因此為了延續弘傳純淨的佛法,梭巴格西認為他所創建的鹿野苑佛教中心是一個可以提供修行者修學佛法的地方,這是他到西方傳法的重要使命。他想確保大家對藏傳佛教的興趣不只是一時的興趣而已,然後就消失不見了。格西感嘆:「我不想看到在美國的藏傳佛教變成這樣。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創造一個堅固傳統基礎,即使它規模很小,但是至少會為那些未來想要認識藏傳佛教的其他人保留一些基礎。」格西繼續說:「圖博在幾世紀以來抗拒了現代化和世俗化,在圖博境內有比幾乎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更多的僧院和尼院,這些寺院中心是我們宗教文化的核心,它們是人們可以來這裡一生獻身於宗教修行的地方,但是在家人也一樣從這種狀況中得到利益,因為他們也可以從這些僧人學者和老師身上得到教導。」
「願除苦良藥,一切安樂源,教法得護持,長久住世間。」寂天菩薩所寫的這首偈頌是梭巴格西常常引用的祈願文,格西解釋這首偈頌的意義是:「為了使教法延續和興盛,人們對佛法的敬重、興趣和物質財力支持必須持續,一定要有讓人們可以接觸到佛法的地方存在。這些教法不可能只存在虛空之中,必須有人們支持佛陀的教法才能延續下去。」
梭巴格西在本書《如夢覺醒》的最後一段為自己一生的經歷做了以下的回顧與交待:「我今天必須肩負起考慮這些事情的職責是一件很難令人置信的事。當我離開我的藏區老家時,我從未夢想過我的一生會把我帶到何處去,我在離開圖博時實際上是一無所有的,我身上有的東西就只剩一個杯子。後來由於因緣的發展,我最後有這麼多東西:這塊土地、這間房子、這座佛殿,還有好幾百位忠心追隨的學生。在我去世之前,我要確保所有的這些東西都將繼續用於利益他人,這是我的用意。」他接著留下悟道的證詞與對未來的祈願:「我們都無法知道為何我們會走到現在的處境,或預知再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然而我們卻可以經由當下修習善心善行而掌控自己的未來。透過覺知省察自己的心識,就有可能為未來的善果播下種子,這不只是為了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別人。不管我有的功德何其少,我都要全部迴向給此地和全世界的佛法,使之得以繼續長存,進而減輕一切地方所有眾生的痛苦。」這是一位任運安忍於善德法智的自力現證解脫行道聖者一生修行的最後教誡與期望。
如同龍樹菩薩在《釋菩提心》中所言:「無明至老死,緣起十二支,依因而起故,許我如夢幻。十二支流轉,輪迴於三界,離此諸眾生,無有業果現。如同鐘鼓聲,苗由緣聚生,外物緣起相,許如夢幻化。諸法由因生,終無有相違,因由因空故,由此證無生。」已得無生法忍的聖者對自己一生如幻緣起的示現自然會有「如夢覺醒」的體悟,這是現證空性的梭巴格西對自己修道證道傳道歷程所下的了義註解,我們可以依此證悟的印記回溯格西如何結合法智教理哲學於解脫實修行道中,從而任運安忍於自度度他自利利人的純淨善德。
達賴喇嘛尊者在本書的序言中稱讚梭巴格西說:「這位我已認識超過五十年的學問僧——倫珠梭巴格西,正是一位如此具格具德的老師。梭巴格西做為一位學者和學者的老師,同時也是好幾百位西方學生的佛教導師與帶領者,以及自身更是純淨僧人傳統的持有者等等的貢獻,他一直都是圖博佛教文化的典範代表。」能得到達賴喇嘛如此真心的肯定推崇正是反映了格西一生行持戒定慧三學的至高成就。
如果我們用心去體會領略梭巴格西在追求證悟過程的持戒安忍精進苦行,就能得知他如何能以自在的禪定智慧布施給與他有法緣的隨學弟子,即使他肩負把藏傳經院教理佛法傳入西方世界的艱辛使命,他一樣能自力任運展現證明解脫行道成就的究竟真實。格西做為一位備受尊敬的德高望重現代聖僧,恰恰示現了《般若攝頌》中佛所教導的菩薩悲智行誼:「世間荒途飢饉疾,見而不懼披鎧甲,後際恆勤盡了知,塵許不生厭倦意。菩薩行持如來智,知蘊本空且無生,未住等持悲有情,期間佛法不退失。」為了使佛法僧永存於世間,我們祈願菩薩永住世間。
翁仕杰
【中譯者導讀】
任運安忍於善德法智的自力現證解脫行道
這篇導讀的題目看似冗長而艱深,也許你會問為何不用幾個明顯易懂鏗鏘有力的字做標題就好,反而要把這一連串佛法專門術語堆疊在一起,連讀起來都有點拗口呢?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本書的副標題「倫珠梭巴格西自傳」的意譯:藏文的「倫珠」是任運成就的意思;「梭巴」是指安住忍耐;「格西」就是大家熟知的善知識,意指擁有善德及佛法智識的修行者;「自傳」當然就是自述的行傳,然而這裡所說的行傳並非是一般人的生平紀錄而已,而是描述已被公認為大師的作者本人依自身修學之力而...
作者序
【達賴喇嘛序言】
當今整個西方世界對佛教的興趣正方興未艾且廣為流行,佛教因而遭逢了新文化與新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經由對佛陀教法具有深廣了解的學者與修行者來傳承佛法,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這是維護佛法的純淨性與正統性的唯一方式。這位我已認識超過五十年的學問僧--倫珠梭巴格西,正是一位如此俱格俱德的老師。梭巴格西做為一位學者和學者的老師,同時也是好幾百位西方學生的佛教導師與帶領者,以及自身更是純淨僧人傳統的持有者等等的貢獻,他一直都是圖博佛教文化的典範代表。我在拉薩接受格西學位考試的最後階段中,他是少數被選來在我辯經時向我提問的最優秀學僧之一。
在我的鼓勵之下,他在1962年前往美國。由於隨後機緣的發展,他受邀到威斯康辛大學教書,成為美國大學中首先教授西藏語言的少數老師之一。在其後擔任教授超過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他教導出了許多位當前美國佛學研究的學者。這位遠從圖博來的人得以晉升到西方學術成就的最高層級,最主要是基於他個人在圖博所接受的僧院教育和自身所俱備的功德之緣故,這正是我之所以要恭賀表揚梭巴格西的理由。
我希望這本記錄梭巴格西模範生活的引人入勝記事,能使感興趣的讀者更深刻了解並且感恩他所成就的一切,同時也能更加認識和體會圖博佛教僧院教育所具有的價值。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
2012年9月20日
【達賴喇嘛序言】
當今整個西方世界對佛教的興趣正方興未艾且廣為流行,佛教因而遭逢了新文化與新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經由對佛陀教法具有深廣了解的學者與修行者來傳承佛法,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這是維護佛法的純淨性與正統性的唯一方式。這位我已認識超過五十年的學問僧--倫珠梭巴格西,正是一位如此俱格俱德的老師。梭巴格西做為一位學者和學者的老師,同時也是好幾百位西方學生的佛教導師與帶領者,以及自身更是純淨僧人傳統的持有者等等的貢獻,他一直都是圖博佛教文化的典範代表。我在拉薩接受格西學位考試的最後階段中,他是少數被...
目錄
達賴喇嘛序言 7
【中譯者導讀】任運安忍於善德法智的自力現證解脫行道 9
英文編輯序言 31
導言:圖博簡史 36
在老家的生活 51
早年的記憶 60
甘丹秋廓寺的歷史 70
剛出家時 76
我的親戚儀軌師 81
在甘丹秋廓寺的修行生活 86
小僧人最早的兩位法師 91
日常僧眾集會與功課 94
離寺出走 98
完成基本教育 102
我舅舅和他在佛寺中的職位 106
寺院的生計 110
甘丹秋廓寺的教學體制與上課時間 115
教理教育的體系 119
學問僧的地位 125
學問僧的教育 127
我的老師根莫朗 132
第一次接受時輪金剛的灌頂 134
決定去色拉寺 139
取得父母的允許 145
去色拉寺的旅程 148
色拉寺的歷史 154
進入色拉寺傑學院藏巴康村 159
甘丹墀仁波切 164
洛桑秋丹格西 168
昂望瑞色格西 172
昂望根敦格西 175
倫珠塔給老師與清淨的寺院生活 178
出家僧侶的生活 183
糾察師的演講 192
色拉傑的教育課程 201
在色拉傑讀書和教書 204
色拉寺的辯經體制 209
在「疆」舉行的冬季學期 218
被選為小明學者的榮譽 222
被選為大明學者的更高榮譽 228
不同等級的格西學位 234
格西學位的授予 238
上下密教院 247
瑞庭攝政事件和其他的麻煩 251
被任命為親教師 264
找時間修行 268
帕崩卡仁波切和他的遺產 272
從其他大喇嘛處所得到的教導 279
在帕崩卡仁波切拉章閉關修金剛瑜伽女 285
成為親教師的得失之處 291
達賴喇嘛親政與第一次流亡 294
倫珠塔給師父被任命為色拉傑住持 299
逐步的轉變 302
第十世班禪喇嘛 307
與達賴喇嘛辯經 310
1959年圖博抗暴起義 315
決定離開色拉寺 322
流亡的開始 326
短暫的喘息與離開圖博的漫長旅程 331
扺達印度 340
開始過難民的生活 346
從阿薩姆到達爾豪西 354
學習過流亡生活 361
努力延續圖博文化 366
計劃去不丹一次 370
達賴喇嘛的一封信 375
那些未能逃出圖博的人所面臨的處境 381
去美國 384
在紐澤西的新生活 391
開始在美國教書 396
創辦佛學中心 403
達賴喇嘛首次訪問麥迪遜 408
第一次在美國所舉行的時輪金剛灌頂 411
回到圖博 420
見到班禪喇嘛及師父塔給仁波切的圓寂 423
最近幾年的狀況 429
未來 440
達賴喇嘛序言 7
【中譯者導讀】任運安忍於善德法智的自力現證解脫行道 9
英文編輯序言 31
導言:圖博簡史 36
在老家的生活 51
早年的記憶 60
甘丹秋廓寺的歷史 70
剛出家時 76
我的親戚儀軌師 81
在甘丹秋廓寺的修行生活 86
小僧人最早的兩位法師 91
日常僧眾集會與功課 94
離寺出走 98
完成基本教育 102
我舅舅和他在佛寺中的職位 106
寺院的生計 110
甘丹秋廓寺的教學體制與上課時間 115
教理教育的體系 119
學問僧的地位 125
學問僧的教育 127
我的老師根莫朗 132
第一次接受時輪金剛的灌頂 134
決定去色拉寺 139
取得父母的允許 145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