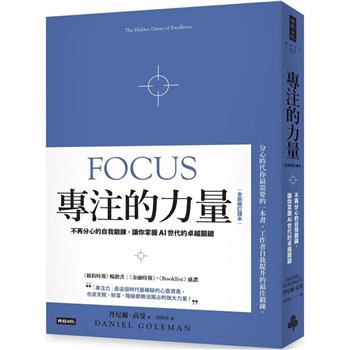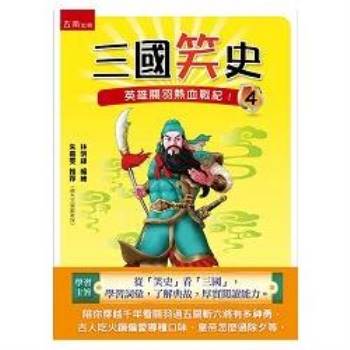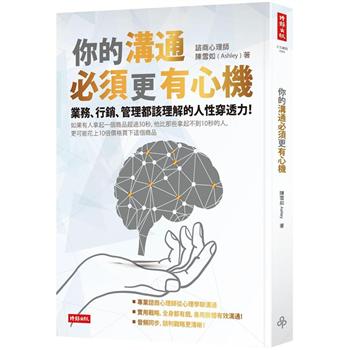小神棍魏陽雖對堪輿風水、靈異卜卦張口即來,
但實際上對於陰陽鬼神,他卻是完全不相信的。
算得上「家學」淵源的他,
又怎麼會不知道這些古怪騙術的原理?
他一心只想在「界水齋」這塊招牌之下,
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孰知從不信邪的他,
竟在路上遇到了天師收妖的現場!
一場車禍撞上的,不僅僅是一隻披著人身的「黃冑」,
更是魏陽二十多年來堅信的無神論!
只是這天師武藝高強,年輕英俊也就罷了,
竟單純耿直如同一個幼兒?!
不僅如此,這小天師還認得他從小就戴在身上的「符玉」,
和他失去記憶的童年,似乎還有著讓人不安的牽扯……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過路陰陽 上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過路陰陽 上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