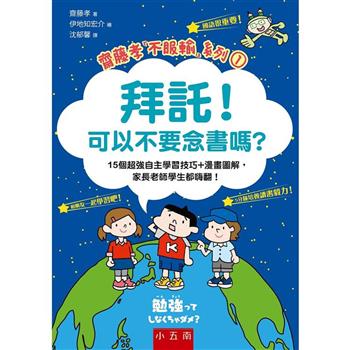大明成化年間,以弱冠年紀,在殿試拿下二甲第一的唐泛,
不留在翰林院爬資歷,反而自願至順天府擔任推官。
他個性外圓內方,聰明絕頂,
任何看來毫無破綻的案件,
在他細心觀察、審慎推敲之下,
總是會找到蛛絲馬跡,一舉破案。
原以為以他的年紀,
在這從六品小推官的位置上大概要坐很久,
卻不想竟遇上勳貴武安侯家的謀殺大案,
甚至牽扯進東廠、西廠與錦衣衛的明爭暗鬥之中。
可對唐泛來說,
沒有什麼事,是比查明事實,讓兇手伏法更重要的!
就算是面對冷酷無情的錦衣衛北鎮撫司總旗,隋州,
亦或其名可止幼兒夜啼的西廠廠公,汪直,
他都能周旋其中,借勢借力,
將案件的真相一一揭發出來!
本書特色
吃貨推官V.S.廚娘(打叉)冷面錦衣衛
大明成化年間的推理案件耽美傳奇!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成化十四年 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BL/GL |
$ 255 |
華文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成化十四年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