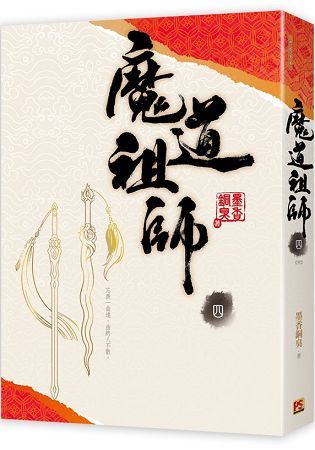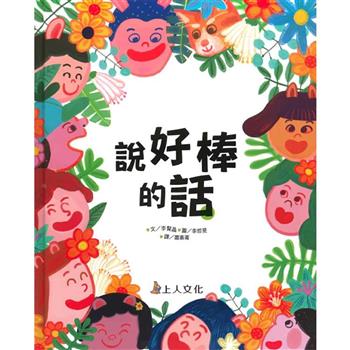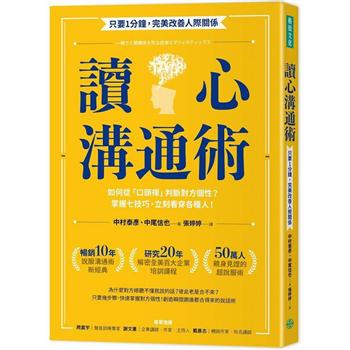三
至寅時,抵達雲夢。
蓮花塢的大門前和碼頭上燈火通明,映照得水面金光粼粼。過往,這碼頭很少有機會一下子聚集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船隻,不光門前的守衛,連江邊幾個還架著攤子賣宵夜小食的老漢都看呆了。江澄率先下船,對守衛交代幾句,立刻有無數名全副武裝的門生湧出大門。眾人分批次陸續下船,由雲夢江氏的客卿們安排入內。歐陽宗主終於逮到了兒子,邊低聲教訓邊把他拽走了。魏無羨和藍忘機走出船艙,跳下漁船。
溫寧道:「公子,我在外面等你。」
魏無羨知道,溫寧不會進蓮花塢大門的,江澄也絕不會讓他進,點點頭。藍思追道:「溫先生,我陪你吧。」
溫寧道:「你陪我?」他完全沒料到,十分高興。藍思追笑道:「是啊,反正眾位前輩進去是要商議要事的,我進去也沒什麼作用。我們繼續聊。剛才咱們說到哪兒了?魏前輩真的把兩歲小兒當成蘿蔔種在土裡過?」
他雖然聲音小,但前邊那兩位可是耳力非凡。魏無羨腳底一個趔趄。藍忘機的眉形彎了一下,很快恢復。等到這二人背影消失在蓮花塢的大門之後,藍思追才繼續低聲道:「那小朋友真可憐。不過,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含光君也曾經把我放在兔子堆裡過。他們其實在有些地方上還挺像的……」
邁入蓮花塢大門之前,魏無羨深深吸了一口氣,藉此平復心緒。可進門之後,他卻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激動。
也許是因為太多地方都翻新過了。校場擴大了兩倍,一座連一座的新築飛簷勾角高低錯落,比以往更有氣勢,也更顯得榮光。但是,和他記憶中蓮花塢的樣子相比,幾乎面目全非。
魏無羨心中悵然若失。以往那些老屋,不知道是被這些華麗的新築擋在了後面,還是已經被拆掉了。
畢竟,它們真的是太老了。
校場上各家門生又開始列方陣,盤足打坐,繼續休養,恢復靈力。折騰了快一天一夜,這些人都已經疲憊至極,必須要喘口氣了。江澄則帶領眾位家主和要人名士們入屋內大廳,試劍堂,再議昨日之事。魏無羨和藍忘機隨之而入,有人微覺不妥,但也沒法說什麼。
剛進內廳,還未落座,立刻有一名客卿模樣的人上前來,道:「宗主。」
他湊到江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江澄皺眉道:「不見。有什麼事日後再說,沒看現在是什麼情況嗎?」
那名客卿道:「我說過了,但那兩名女子說……她們就是為昨天的事而來的。」
江澄道:「對方什麼來頭?哪家的女修?」
那名客卿道:「哪家都不是,也不是女修,屬下能肯定,她們都是身無靈力的普通女子。都是今天到的,她們還帶了一批名貴的藥材來,但沒說是哪位家主送的,只說有要事告訴宗主,屬下聽她們所言非同小可,怕怠慢了,現在將她們人安置在客居,藥材也還沒入庫。驗查過了,沒有不妥的咒術。」
並非是誰想見雲夢江氏的家主都能見到的,而且還不肯告知來歷,而且還是兩名一無靈力、二無家世的普通女子。不過帶上了一批名貴藥材,負責接待的客卿便絕不敢怠慢了,哪怕不看重禮的分上,單衝這份蹊蹺都不能忽視。江澄道:「諸位,請自己隨便坐。容江某失陪片刻,去去便回。」
眾人紛紛道:「江宗主客氣。」
然而,江澄並未去去就回,而是半晌未歸。屋內有客置之不理已是失禮,何況眼下還是非常情況,所有人都在等著商議要事。過了小半個時辰,江澄仍未出現,不少人都開始不安或不滿。正在此時,江澄終於回來了。他去時神色如常,回時卻神色冷肅,步履如飛,而且帶來了兩個人,是兩名女子,應當就是登門拜訪的那兩人。眾人原本以為就算是兩個普通女子,能攜重禮拜訪,也應當非同凡響,誰知這兩名女子年紀都已不輕,眼角嘴角的細節裡均顯老態,而且一個低眉順眼,惴惴惶恐,一個滿身風塵不說,臉上更是被劃了五六刀,刀痕陳舊,形容可怖,可謂是令人倒盡胃口,大失所望,開始心裡泛起嘀咕,江澄為什麼把這樣兩個女人帶到試劍堂來了,而且還給她們指了廳堂中心的位置。
江澄面色陰沉,對那兩名戰戰兢兢坐下的女子道:「妳們在這裡說。」
姚宗主道:「江宗主,你這是?」
江澄道:「此事過於駭人聽聞,江某不敢貿然,細細盤問,所以耽擱了些時間。諸位請靜一靜,聽聽這兩位的話。」他轉過去,道,「妳們二位誰先說?」
那兩名女子面面相覷,那名一身風塵之氣的女子膽子較大,起身道:「我先來吧!」
她隨隨便便行了一禮,道:「我要說的,是一件大約十一年前的舊事。」
聽江澄口氣,眾人皆知這女子要說的絕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紛紛暗想十一年前發生過什麼事。那女子道:「我叫思思,本來是個做皮肉生意的,也算是紅過一陣吧,十幾年前找了個富商想嫁了,誰料到富商老婆是個厲害的,找了一群大漢,帶刀劃了我的臉,我就變成這樣了。」
這女子說話毫不知害臊,也不知拐彎抹角,聽得一些女修舉袖掩口,一些男修頻頻皺眉。思思道:「我的臉變成這樣,日子就跟之前不一樣了,誰都不肯看一眼,更別說做我的生意了,原先的館子把我趕了出來。我又不會幹別的,但又到處都接不到活,就跟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姐妹一起搭夥,她們的客人要求不高,有什麼活帶我一份,我把臉遮起來也能湊合。」
說到這個分上,有些人受不了了,目光裡的鄙夷已赤裸裸地流了出來,有人不明白江澄為何要讓眾人聽這女子當眾說這種腌臢醜事。家主們則沉住了氣,等她說下去。果然,她這便說到重點了。思思道:「有一天,我們同一條巷子裡的姐妹們突然接到了一筆生意,點了我們二十多個人,用馬車接我們去一個地方。我那些老姐妹講好了報酬,在車上都高興死了。我卻覺得不對勁。說直白點,大家都要麼上了年紀人老珠黃,要麼就是我這種樣子的,付那麼多錢,還是先付的,天底下有這麼便宜的事?而且來找我們的人還神神祕祕鬼鬼祟祟,來了就直接都帶上車接走,沒讓其他任何人知道。怎麼瞧也不像安了好心!」
其他人也是這麼想的,原先鄙夷的心思已被好奇心代替,思思道:「馬車到了地方,直接把我們帶進了一個院子下車。我們所有人都從沒看過那麼高、那麼大,那麼金碧輝煌的房子,全都被晃瞎了眼睛,氣都不敢出。有個少年靠在門口玩兒匕首,看到我們便叫我們進去,他關了門,進到房子裡,好大的屋裡只有兩個人,一張大床上的錦被裡躺著個男人,瞧著有三四十歲,像是病得半死不活,看到有人進來了,只有眼珠子還能轉。」
「啊!」
試劍堂中,忽然有人發出恍然大悟的驚叫:「十一年前?!這是……這是……!」
思思道:「事先有人叮囑過我們該怎麼做,就是一個一個拿出我們的看家本事去伺候裡邊床上躺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我還以為是個多威猛的漢子,沒想到是個癆病鬼。這人哪禁得起伺候?只怕是伺候沒兩下他就要一命嗚呼了,哪有這種急色死鬼?而且他們這麼有錢,肯定不是請不起年輕貌美的,為什麼非要請我們這種又老又醜的?我爬到他身上去了還在想這個,忽然好像有個年輕男人笑了一聲,我嚇了一跳,這才發現床邊有一道簾子,簾子後面還坐著個人!」
所有人的心都被緊緊牽住,思思繼續道:「我才發現這個人一直坐在簾子後面,他一笑,床上這個男的忽然掙扎了一下,把我掀開,滾下了床。那個人笑得更厲害了,邊笑邊說話。他說,父親,我給你找來了你最愛的女人,有很多個,你高興嗎?」
這句話雖是從思思嘴裡說出來的,但眾人心頭都毛骨悚然,浮現出了一張面帶微笑的臉。
金光瑤!
而那個床上的半死男人,一定就是金光善!
金光善之死,在眾家之中一向是個公開的祕密。金光善一生風流得幾近下流,處處留情處處留種,他的死因也與此相關,堂堂蘭陵金氏家主,身體衰弱之際還堅持要與女人尋歡作樂,終於死於馬上風。這說出去實在不怎麼體面。金夫人痛失獨子與兒媳後,原本就鬱鬱不樂了幾年,以為丈夫死前還不忘鬼混,最終混丟了命,也活活被氣得病倒,不久之後便撒手人寰。蘭陵金氏四處遮掩鎮壓風聲,然而眾家早心照不宣。面上哀慟嘆惋,實則都覺得他活該,就配這麼個死法。誰知今日,他們卻聽到了一個更加不堪入耳,醜陋至極的真相。倒抽冷氣之聲在試劍堂裡此起彼伏。
思思道:「那中年男人要喊要掙扎,卻渾身沒力氣。剛才引我們進來的那個少年又開門進來,一邊嘻嘻笑,一邊把他拖上床,拿了一根繩子,踩著他的腦袋把他五花大綁了,對我們說,繼續,就算他死了也不要停。我們誰見過這種陣仗?嚇個半死,但又不敢違逆,只好繼續。到第十二個還是十一個的時候,那個姐妹忽然尖叫,說他真的死了。我上去一看,果然沒氣了。可是,簾子後面那個人說,沒聽到嗎?死了也別停!」
歐陽宗主忍不住道:「金光善再怎麼說,也是他的親生父親,若這件事是真的……這也太……也太……」
思思道:「我一看這人死了,我就知道完了,我們肯定也逃不掉了。果然,完事後,我那二十多個老姐妹,全都被殺了,一個不留……」
魏無羨道:「那為何單單留下了妳?」
思思道:「我不知道!我當時苦苦哀求,說我不要錢了,我絕不會說出去,誰知道他們真的沒殺我,把我帶到一處居所關了起來,一關就是十一年。最近我才偶然被人救了,逃了出來。」
魏無羨道:「誰救的妳?」
思思道:「不知道,我也從沒直接見過救我的人。但那位恩公聽了我的遭遇之後,決定不願讓這個道貌岸然的敗德之徒繼續欺騙眾人,就算他如今一手遮天,也要將他所做之事都披露出來,給被他害了的人討個公道,讓我那二十多個可憐的姐妹九泉下安息。」
魏無羨道:「那妳所言之事,有什麼證據嗎?」
思思猶豫片刻,道:「沒有。但我要是講了一句假話,教我屍身爛了連張席子都沒得捲!」
姚宗主立刻道:「她細節說得這般清楚,絕對不是撒謊!」
藍啟仁眉頭緊蹙,轉向另一名女子,道:「我似乎見過妳。」
那女子一臉惶恐,道:「應該……應該是見過的。」
旁人一怔:這思思是一名野娼,該不會這女子也是吧?藍啟仁怎麼會見過她?
那女子道:「樂陵秦氏舉辦清談會的時候,我時常伴隨我家夫人左右。」
「樂陵秦氏?」一名女修道,「妳是樂陵秦氏的使女?」
有更眼尖的女修直接喊出了名字:「妳是……碧草,秦夫人的貼身侍女碧草!對嗎?」
她說的秦夫人是指秦蒼業的妻子,也就是金光瑤之妻秦愫的生母。這女子點頭,道:「不過現在我已經不在秦家了。」
姚宗主大是興奮,拍案而起,道:「妳是不是也有事情要告訴我們?」
碧草紅著眼眶,道:「我要說的事,發生得更早一點,十二三年前。」
「我服侍我家夫人多年,是看著我家娘子長大的,夫人一向對愫娘子關心有加,但在愫娘子即將成親的那段日子,夫人卻一直心情不好。她天天晚上做噩夢,白天有時也會突然以淚洗面,我以為是女兒要嫁人了,她心中捨不得,一直安慰她說,愫娘子要嫁的那位斂芳尊金光瑤年輕有為,又是個溫柔體貼,專一不二的男子,她會過得很好的。誰知夫人聽了之後,看上去更難過了。」
「婚期將近的時候,有天晚上,夫人忽然對我說,要去見愫娘子未來的夫婿,而且是現在,要我悄悄陪她。我說,您可以召他來見您啊,為什麼要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地去見一個年輕男子?教人知道了指不定要傳得多難聽呢。可夫人卻態度堅決,我只好跟著她一起去了。但是到了之後,她卻讓我守在外面,不要進去。所以我什麼也沒聽到,不知道她到底和金光瑤說了什麼。只知道過了幾天,愫娘子成親的日子定下來了,夫人一看到帖子就暈了過去。而等到成婚之後,夫人也一直悶悶不樂,生了心病,病得越來越嚴重。臨終前,她還是撐不住,把所有的事情都和我說了。」
碧草一邊流淚一邊道:「斂芳尊金光瑤和我家愫娘子,他們哪裡是什麼夫妻,他們根本是一對兄妹呀……」
「什麼?!」
就算此時一道天雷在試劍堂內炸響,也不會比這一句有更大的威力了。魏無羨的眼前浮現出秦愫那張蒼白的臉。碧草道:「我家夫人實在是太可憐了呀……金老宗主那個東西不是人,他貪戀我家夫人相貌,一次在外醉酒後強迫她……夫人哪裡抵抗得了,事後也不敢聲張,我家主人對金光善忠心耿耿,她怕極了。金光善記不清愫娘子是誰的女兒,我家夫人卻不可能忘。她不敢找金光善,知道愫娘子傾心金光瑤,掙扎很久,還是在大婚之前悄悄去找了他,吐露了一些內情,哀求他想辦法取消婚事,萬萬不可釀成大錯。誰知……誰知金光瑤明知愫娘子是他親妹子,卻還是娶了她呀!」
更可怕的是,不光娶了她,兩人還生了孩子!
這可當真是一樁驚天的醜事!
眾人討論的聲潮一浪比一浪高。「秦老宗主跟隨了金光善多少年啊,竟然連自己老部下的妻子都要染指。這個金光善!」
「世上終歸是沒有不透風的牆……」
「金光瑤要在蘭陵金氏站穩腳跟,就非得有秦蒼業這位堅實的岳丈給他助力不可,他怎麼會捨得不娶?」
「論喪心病狂,他真是舉世無雙!」
魏無羨低聲對藍忘機道:「難怪他當初在密室對秦愫說,『阿松必須死』。」
試劍堂中,也有其他人想到了阿松,姚宗主道:「如此看來,我斗膽猜測,他的兒子恐怕根本不是別人暗害的,而是他自己下的毒手。」
「怎麼說?」
姚宗主分析道:「近親兄妹所生之子,十之八九會是痴呆兒。金如松死時剛好才幾歲,正是幼子開蒙的年紀。孩子太小時旁人看不出來什麼端倪,可一旦長大,就會暴露他與常人不同的事實了。就算不會懷疑到父母的血緣上來,可若是生出一個痴呆兒,旁人都未免會對金光瑤說三道四,指指點點,說是因為他帶了娼妓的髒血才會生出這種孩子之類的風言風語……」
眾人大感有理,道:「姚宗主真是犀利!」
姚宗主又道:「而且當時毒害金如松的人剛好是反對他建瞭望臺的那位家主,哪有這麼巧的事?」他冷笑道,「反正,無論如何,金光瑤都不需要留著一個很可能是白痴的兒子。殺了金如松,栽贓給反對他的家主,然後以給兒子報仇的名義,光明正大地討伐不服他的家族——雖冷酷無情,卻一箭雙鵰。斂芳尊真是好手段啊!」
忽然,魏無羨轉向碧草,道:「金鱗臺清談會那晚,妳是不是見過秦愫?」
碧草一怔,魏無羨道:「當晚在芳菲殿內,秦愫和金光瑤有一番爭吵,她說她去見了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了她一些事,還給了她一封信,這人絕不會騙她,說的是不是妳?」
碧草道:「是我。」
魏無羨道:「這個祕密妳守了這麼多年,為什麼忽然決定要告訴她?又為什麼忽然要公之於眾?」
碧草道:「因為……我得讓愫娘子看清她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原本我也不想公之於眾的,但是愫娘子在金鱗臺上莫名自殺,我一定要揭露這個衣冠禽獸的真面目,給我家夫人和我看著長大的姑娘討回公道。」
魏無羨笑了笑,道:「可是妳難道沒有想過,告訴她之後,會給她造成什麼樣的打擊嗎。還是妳真的不知道?正是因為妳先去告訴了秦愫,她才會自殺啊。」
碧草道:「我……」
姚宗主不滿道:「你這話我可不同意了,難道隱瞞真相才是對的?」
立即有人幫腔:「怨不得旁人啊,唉,金夫……秦愫還是太脆弱了。」
幾名年長的女修則道:「秦愫真可憐啊。」
「當初我還羨慕她呢,心說真是命,出身好,嫁得也好,金鱗臺的不二女主人,丈夫一心一意,誰知道,嘖嘖。」
一位夫人狀似超然地道:「所以這些看上去很美的事物,背後往往都是千瘡百孔的。根本沒什麼好羨慕的。」
魏無羨心道:「恐怕秦愫正是因為無法忍受旁人這些聽似同情憐憫,實則津津樂道的碎語閒言,所以才選擇自殺的吧。」
他低頭看了看,忽見碧草手腕上戴著一只翡翠金環,成色極佳,絕不是一個使女能戴得起的東西,笑笑,道:「鐲子不錯。」
碧草連忙拉了袖子,低頭不語。
聶懷桑愣愣地道:「可……可今天送這兩位到這裡來的人……究竟什麼來頭啊?」
姚宗主道:「何必糾結這些!不管是誰,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是一位義士,絕對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頓時附和聲聲:「不錯!」
魏無羨卻道:「救了思思姑娘的這位的確不簡單,有錢又有閒。不過,義士?這可未定。」
藍忘機道:「頗多存疑。」
若是魏無羨說這句話,沒幾個人會理,可說話的人是藍忘機,眾人頓時收斂聲息。藍啟仁道:「何處存疑?」
魏無羨道:「那可多了。比如,金光瑤如此心狠手辣,為何殺了二十人,卻單獨留下一個思思?現在人證是有了,但物證呢?」
他一直發出不同聲音,在一片群情激憤中顯得格格不入,有些人已怫然不悅。姚宗主大聲道:「這便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聞言,魏無羨微微一笑,不再說話了。
他知道,現在沒人聽得進去他的話,也沒人會仔細考慮他的疑惑。再多言幾句,旁人說不定又要開始針對他了。若是在十幾年前,他根本不會理會旁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你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可如今,魏無羨已經沒什麼興趣非出這個風頭不可了。
於是,廳內眾人一浪高過一浪的聲討開始了:
「沒想到這人如此忘恩負義,喪心病狂!」
「忘恩負義」和「喪心病狂」這兩個詞十幾年來幾乎是和魏無羨捆綁的,乍一聽他還以為又在罵自己,須臾才反應過來。罵的人是同一批,罵的詞還是同一種,罵的對象卻換了一個,略不習慣。
緊接著,另一人道:「當初金光瑤就是靠討好赤鋒尊和澤蕪君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否則他一個娼妓之子,何以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他竟然對赤鋒尊下毒手!澤蕪君現在還在他那裡,只盼萬萬不要有什麼閃失才好!」
原先他們都不相信聶明玦之死、分屍之事、以及亂葬崗群屍圍攻與金光瑤有關,現在卻忽然都相信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魔道祖師(四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9 |
二手中文書 |
$ 248 |
BL/GL |
$ 257 |
小說/文學 |
$ 261 |
小說 |
$ 297 |
大眾文學 |
$ 297 |
大眾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魔道祖師(四完)
墨香銅臭年度最具話題性的超強人氣之作!
◎額外收錄繁體版獨家番外
重生於世的一代魔頭,非但沒有再掀腥風血雨,
竟還和正派人士一起調查疑案,鏟妖除魔?!
更驚人的是,他和這位正派人士還一起往斷袖的道路上奔去……
自亂葬崗歷劫歸來,魏無羨首次回到蓮花塢,
原是滿懷興奮地向藍忘機介紹自己的成長之地,
可滿腔的懷念之情,卻在江澄的一通發作下被消融殆盡。
兩人因此離開蓮花塢,前往雲萍城,
欲調查當初於金光瑤密室中所發現的那份房契地契,
然始料未及的是,該處竟是一間觀音廟!
金光瑤又有何陰謀?
且廟中大陣意圖鎮壓的,究竟是何物?
而決定在破陣前先行休養生息的兩人卻都沒料到,
他們之間早在蓮花塢時就開始越發曖昧的氣氛,
在同住一間房後竟膨脹至危險邊緣,
甚至是,一發不可收拾──
本書收錄番外〈家宴〉、〈香爐〉、〈惡友〉,以及實體書番外〈朝暮〉。
作者簡介:
墨香銅臭(ㄒㄧㄡˋ)
低齡迷信少女,知名表情包博主。
美食界泥石流,拍照手抖帕金森。
打字慢如狗,填坑看心情
……都是騙人的。
其實喜歡在午後喝一杯清茶眺望遠方,打開心愛的筆記本寫詩。
……不不不這更是騙人的。
好吧,其實,我只是一個寫文的。
嗯。
TOP
章節試閱
三
至寅時,抵達雲夢。
蓮花塢的大門前和碼頭上燈火通明,映照得水面金光粼粼。過往,這碼頭很少有機會一下子聚集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船隻,不光門前的守衛,連江邊幾個還架著攤子賣宵夜小食的老漢都看呆了。江澄率先下船,對守衛交代幾句,立刻有無數名全副武裝的門生湧出大門。眾人分批次陸續下船,由雲夢江氏的客卿們安排入內。歐陽宗主終於逮到了兒子,邊低聲教訓邊把他拽走了。魏無羨和藍忘機走出船艙,跳下漁船。
溫寧道:「公子,我在外面等你。」
魏無羨知道,溫寧不會進蓮花塢大門的,江澄也絕不會讓他進,點點頭。藍思追道:「...
至寅時,抵達雲夢。
蓮花塢的大門前和碼頭上燈火通明,映照得水面金光粼粼。過往,這碼頭很少有機會一下子聚集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船隻,不光門前的守衛,連江邊幾個還架著攤子賣宵夜小食的老漢都看呆了。江澄率先下船,對守衛交代幾句,立刻有無數名全副武裝的門生湧出大門。眾人分批次陸續下船,由雲夢江氏的客卿們安排入內。歐陽宗主終於逮到了兒子,邊低聲教訓邊把他拽走了。魏無羨和藍忘機走出船艙,跳下漁船。
溫寧道:「公子,我在外面等你。」
魏無羨知道,溫寧不會進蓮花塢大門的,江澄也絕不會讓他進,點點頭。藍思追道:「...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墨香銅臭
- 出版社: 平心工作室 出版日期:2016-12-12 ISBN/ISSN:978986571079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6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