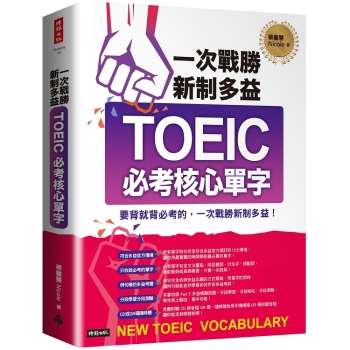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秋日烈陽萬丈,李衍秋駐馬太和殿外,暮風翻飛,吹起兩道旗幟。
「吾皇萬歲!」黑甲軍排山倒海,單膝跪地。
謝宥與蔡閆慢慢趕來,李衍秋卻停著,出了會兒神,剛才有那麼一剎,他似乎感覺到了什麼。
「辛苦了。」李衍秋說。
黑甲軍如潮水般散開,讓出一條路,李衍秋進了正殿內,江都皇宮幾經風雨,如今重作修繕,足比西川還要豪華。太監上前,為李衍秋解下斗篷,李衍秋便沿著走廊過去。
鄭彥、郎俊俠也到了,李衍秋經過東宮外,往裡頭瞥了一眼,見郎俊俠正坐在走廊下吹笛子,李衍秋經過,他也不起身行禮。
「這一路上也累了。」李衍秋也不理會郎俊俠,只是朝蔡閆說道:「去歇歇吧。」
蔡閆跟在後頭,說:「明日一早就是吉辰,還得祭天,叔也早點休息。」
李衍秋答道:「家雖然換了,藥還是免不了要喝,你安心。」
蔡閆便與東宮一眾僕役恭送李衍秋離開。
長秋宮內,牧錦之正在鏡前描眉,衣裳釵粉也送到了,正在一箱一箱地開著查驗。
「什麼人又招惹陛下了?」牧錦之從鏡中看著李衍秋,眉頭一揚,笑吟吟地說。
「並沒有什麼人招惹我。」李衍秋站在牧錦之身後,答道:「皇后這火眼金睛,卻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牧錦之放下釵子,隨口道:「太子門客一事,今天已吩咐下去了,科考後便當選些人,供太子細細地挑去。」
李衍秋彬彬有禮道:「倒是承皇后費心。」
夫妻二人話不投機半句多,李衍秋說完便又走了出去,牧錦之從鏡中白了他的背影一眼。
李衍秋回到自己的寢宮中,朝著宣室殿外的晴空。
鄭彥正在廊下坐著,讓人開箱,找他的酒。
「鄭彥。」李衍秋眉頭微皺:「你怎麼還在這兒?」
「太子嫌棄我,陛下。」鄭彥彬彬有禮道:「有烏洛侯穆在,臣也不必去遭白眼了,大家兩不相見,豈不是更怡然自樂些?」
「我一見烏洛侯穆,心中就有把無名火。」李衍秋也和和氣氣地朝鄭彥說:「四大刺客,個個歪瓜裂棗,如今看來,竟是最不得志的武獨,比你們還要周正些。總奇怪是不是武獨給你們下了什麼毒,一個兩個的,現在都變這副模樣了。」
這話是連鄭彥也罵進去了,李家兩兄弟,一個鋒芒畢露,一個綿裡藏針,鄭彥早已摸清李衍秋的脾氣,知道他怒了。
鄭彥馬上說:「陛下恕罪,臣這就到東宮去。」
鄭彥離開後,李衍秋才長長嘆了口氣。
「陛下,該喝藥了。」宮女捧著藥上來,李衍秋隨手接過,喝了,隨手朝院外一扔,琉璃盞一聲輕響,摔得粉碎。
◎
「哇——!」段嶺終於到了新家。
相府特地撥給武獨與段嶺一間院子,與正府一巷之隔。較之先前在西川那僻院,新家大了許多,四房兩進,一面照壁,還有後院供他們養馬,又安排了一名主事、兩名僕役伺候。
院裡有假山,有一個池塘,池塘後頭種滿了竹子,邊上還有桃樹,細水淙淙淌入池中,從彎彎曲曲的渠再流淌出去,竹管架在院牆上,是從丞相府中引來的。
「相爺請兩位回來後先住著。」那主事的說:「洗洗一身塵,今夜便為兩位接風。」
「都回去吧,不必伺候了。」武獨在前院朝那主事說。段嶺正在房中左看右看,新家錦被屏風,窗影橫斜,令他想起了瓊花院,連擺設布置都是青瓷,還有一間書房給他讀書用。
主事小心地將武獨扶進來。
「是。」主事似乎料到武獨會這樣說,只站在院中,卻不離開。
段嶺想了想,朝主事說:「武爺家裡有江湖機密,且毒物太多,怕無意中傷了你們,所以不必留在院中。若有吩咐,我自當過去相府裡傳,都回去吧。」
主事這才點頭,朝段嶺與武獨躬身,告辭。
沒有外人在才方便說話,否則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還有錢!」段嶺在隔壁說:「二百兩金子呢!」
段嶺在潼關已將寶藏一事報給了牧曠達,如今一座金山,也不知牧曠達要如何處置,但若拿來花銷,買座城也足夠了,這點賞賜也算不得什麼。
不過段嶺還是挺高興的,至少不必再頓頓吃餅了。
武獨在房中坐著,說:「想吃什麼,我出門買去。」
段嶺說:「你坐著,別動了。」
段嶺抱著被子過來,讓武獨挪了挪,在他的床上又放了個枕頭。
武獨看著段嶺,說:「你睡這房,我睡地上,就在床下,就守著你了。」
「不怕我半夜下床喝水一腳踩死你嗎?」段嶺笑著說。
武獨想起這話正是幾個月前自己說的,突然覺得好笑,兩人都笑了起來。
武獨說:「我來吧。」
「你聽我的話行不?」段嶺認真道。
「行行。」武獨答道:「總得派我點事做,我受傷了,又不是廢了。」
武獨這麼被段嶺照顧著,實在不安,倒不緣自段嶺身分,只因自己長這麼大,從來也不曾有人這麼待他。
「那你洗個澡吧。」段嶺朝武獨說。
武獨抬手,嗅了下自己的衣袖,滿臉通紅,段嶺便出去傳人打水過來洗澡。
小廝們抬著個大桶過來,放在角房裡,一輪一輪地添熱水,兌冷水。
「我自己洗。」武獨忙道。
「快脫。」段嶺說,拿著武獨換下的衣服,到後院去,扔進盆裡,打水泡著,回房去找乾淨衣服。這次牧曠達吩咐對了人,方才那主事辦事極其細心妥貼,居然忘了賞他。
不多時,段嶺就帶著乾淨衣服來了,捋了袖子,給武獨洗澡。武獨手上還纏著繃帶,不能沾水,一手在身上搓來搓去,見段嶺進來,倏然一張帥臉紅到脖子根。
段嶺按著武獨,給他洗乾淨全身。從那天夜裡受了傷,武獨就沒洗過澡,此時左手擱在桶邊,露出健壯的肩背,任段嶺搓揉。
「別掉進來了。」武獨說:「別別別,別朝下摸!」
洗澡桶大得很,段嶺半個身子探進去,武獨感覺到段嶺確實是認真地在給自己搓洗,奈何他的手一直在身上摸來摸去,摸得他快要受不了。
段嶺說:「把腿抬起來點。」
武獨忽然覺得段嶺有趣,玩心忽起,一手抱著段嶺,把他扯了進來,「嘩啦」一聲,濺得洗澡桶周圍全是水。
段嶺怒道:「你!」
段嶺全身濕透,武獨臉上發紅,笑著說:「你洗吧,我不洗了。」
段嶺說:「你身上太髒了,別動。」
段嶺解開自己的單衣,脫掉濕透的衣服褲子,赤著身體,騎在武獨的大腿上,突然他的心底湧起一股莫名的滋味。每一次與武獨肌膚相觸,都不曾有過現在的感覺。
段嶺的臉也紅了,彷彿回到小時候那天晚上,從窗格裡看到郎俊俠的身體的那一夜。然而對著武獨,他的心跳卻更激烈,彷彿有什麼極其新鮮、刺激的滋味,就躲在一層紗後頭,隨時等著他。
「怎麼不說話了?」武獨倒是回過神來了,一手懶洋洋地架在桶沿上,另一手拍拍段嶺白皙的肩背,奇怪地看著他。
「沒……沒有。」段嶺緊張道。
那一刻,武獨似乎也感覺到了什麼,眼裡帶著笑意。
段嶺「嗯」了聲,埋頭用布巾搓洗武獨的胸膛。
房外傳來腳步聲,兩人的動作同時一頓。
「喂,兄臺,你是不是還欠我一杯酒啊。」鄭彥的聲音懶洋洋地道。
段嶺嚇了一跳,他從未見過鄭彥,還以為是丞相府的人闖進院裡來。武獨卻一手摟住了段嶺的腰,把他拉向自己。
鄭彥腳下不停,推開了角房的門,就在這時候,武獨抱著全身赤裸的段嶺,讓他伏在自己身前,把頭埋在肩上。
鄭彥進來時,見武獨正抱著個少年,兩人一起洗澡。
「鄭彥!你究竟有沒有眼色!」武獨不耐煩道:「給我滾出去!」
鄭彥哈哈大笑,笑得夠嗆,忙關上門,說:「你繼續,勿要怪我勿要怪我,實在是沒想到。」
武獨答道:「外頭等著去,少廢話。」
鄭彥的腳步聲遠去,段嶺這才抬起頭來,方才與武獨全身裸著,彼此靠在一起。他感覺到彼此心臟狂跳,且各自那物,都脹得硬挺起來。
兩人相對喘息,武獨做了個「噓」的手勢,示意繼續洗。段嶺嚥了下口水,為武獨搓洗了下頭髮。
「好了。」段嶺小聲說,快步出來,差點在地上滑倒。
「小心。」武獨忙伸出一隻手,摟著段嶺的腰,讓他站直。
段嶺飛快地擦乾,穿上長褲,臉上紅暈褪去,扶武獨出來,給他擦身,擦到他胯下時,乾布碰到他筆挺雄壯的那物,兩人又脹紅了臉。
武獨裹上外袍,傷好得差不多了,已能走路,只是有點踉蹌,便穿上木屐,一步拖一步地從廊前過,經過鄭彥面前,到主房裡去找東西。
「這麼快?」鄭彥說:「該不會是被我嚇出來的吧。」
武獨朝鄭彥罵了句髒話,段嶺在角房裡嚇了一跳,第一次聽到武獨罵髒話。不一會兒,木屐聲響,武獨又叩叩叩地慢慢過來,遞給段嶺乾淨衣服,示意他換上。
收拾停當,小廝過來將浴桶收走,武獨頭髮仍濕漉漉的,裹著一襲浴袍,赤著腳,靠在榻上,抬起左手,讓段嶺換藥,這才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招待鄭彥。
「傷還沒好,你喝酒,我喝藥。」武獨漫不經心地道,並舉起藥碗,象徵性地朝鄭彥敬了一敬。鄭彥哭笑不得,自言自語道:「這幾日聽兩次這話了。」
武獨自然知道鄭彥從哪兒來,見著了什麼人,並未多問,也不為鄭彥介紹段嶺,就當沒這回事。鄭彥等了半天,觀察段嶺,嘴角微微揚了起來,朝武獨一揚眉,意思是不介紹認識認識?
武獨不耐煩道:「有這麼多囉唆,你究竟是來做什麼的?」
「我叫王山。」反而是段嶺主動道:「鄭兄,你好。」
鄭彥打量段嶺,倚在地上的案前,說:「你讓我想起一個人。」
武獨與段嶺都是不約而同地一頓。
「倒是與你未來丈母娘,有那麼一兩分神似。」鄭彥突然哈哈大笑。
武獨登時惱羞成怒,大喝道:「給我滾!」
「丈母娘是誰?」段嶺問。
「去把斷腸草拿來。」武獨冷冷道。
鄭彥忙擺手,示意不開玩笑了,朝段嶺解釋道:「淮陰侯的夫人,端平公主。」
一個念頭在段嶺心裡打了個轉,段嶺笑著說:「哪裡像?」
鄭彥抬起一手,在自己嘴角處稍微比劃了下,段嶺明白到是說自己的嘴角。
武獨冷冷答道:「老子對那姚箏實在是說不出地膈應,你少給我提她。」
「什麼時候進東宮去?」鄭彥懶懶道:「今日太子還正說起你來著。」
聽到這話時,武獨以手指輕輕地捏了捏段嶺的手,示意不必擔心。
「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武獨答道:「烏洛侯穆跑了,自然想起我來,看來你伺候得不大行吧,鄭彥。」
「沒跑,回來了。」鄭彥答道:「遷都前一日回來的。」
武獨雖詫異,仔細一想,卻也是意料之中。
「失寵了?」武獨問。
鄭彥搖搖頭,說:「不清楚,看上去沒有。」
「那廝究竟是什麼出身。」武獨說:「我一直想不通,先帝當年怎麼會任由此人跟隨在身邊。」
段嶺心裡怦怦地跳,知道武獨這話是幫自己問的,鄭彥與淮陰侯姚復交好,說不定知道一些朝廷未有的情報。
果然鄭彥答道:「烏洛侯穆是鮮卑姓,且是國姓。」
武獨沉默不語,手裡玩著個杯子。
「我從淮陰侯處聽到過,這無名客的一些過往。」鄭彥又說:「鮮卑烏洛侯國,百年前為我大陳三戰所敗,舉族遷往鮮卑山深處,大多隱姓埋名,改行當上獵戶。近二十年前,陳、元兩國在鮮卑山有一場小規模混戰。」
「長林之役。」段嶺說。
「對,正是長林之役。」鄭彥有點奇怪段嶺居然會知道,卻不發問,反而是段嶺主動說:「我在相府的奏摺裡看到過這場仗。」
這話倒不是一時性起,先前在相府讀書,先生便讓他與牧磬就長林之役做過分析文章,那一戰打得極其慘烈。
「他是牧磬的伴讀。」武獨隨口道:「莫要欺負讀書人,鄭彥,讀書人肚子裡壞水多得很。」
鄭彥「嗯」了聲,說:「確實,讀書人不好惹,不小心得罪了,別人還要做文章,千秋萬世來罵你。」
段嶺笑了起來,鄭彥接著道:「長林那一戰,陳與元將鮮卑山當作了戰場。所剩無幾的烏洛侯國族裔,在元軍打進來,陳軍撤出去,陳軍再反撲,元軍再撤的反覆游擊戰中,死了太多的人。烏洛侯穆那一年似乎只有八歲。」
「他的村子毀了嗎?」段嶺問。
「興許。」鄭彥說:「後來鎮命將軍秦兆麾下有一武功高手,名喚黎辛的,撤軍後救下了烏洛侯穆,將他帶到魯南教導,收為弟子。秦將軍寫過一封信予淮陰侯,告知此事。只提到一名孩童,並未說到名字,是以多年來,大家都不知烏洛侯穆的真名。」
「我只知道他被喚作無名客。」武獨說。
「是。」鄭彥給自己斟了杯酒,又說:「再後來,上梓之戰中秦兆殉國。過得數年,黎氏的淬劍臺一夜間被屠滅滿門,門下弟子盜青鋒劍而走。白虎堂派人前去追殺,你也知道的。這廝東躲西藏,最終得先帝庇佑,納入麾下。先帝手中擁有鎮山河,但凡白虎堂出身的刺客,都不可忤逆鎮山河持有者,乃是祖訓。」
「有烏洛侯穆在。」武獨說:「我是不會進東宮當門客的,他們也瞧不起我。」
鄭彥突然笑道:「時隔幾日,如今見你,卻是變了個人一般,莫不是有家有室,該知沉穩,不再冒冒失失了。」
武獨說:「鄭彥,武爺雖然不能毒死你,但讓你三個月說不出話,還是不難的。」
鄭彥按著一膝,懶懶起身說:「沒勁吶——什麼時候進宮去走走?」
「有傷在身,行動不便,不送了。」武獨淡淡道:「隨緣吧,沒事莫要勤來了,免得拖我下水。」
鄭彥同情地說:「你堅持不了多久,何苦呢?」
武獨認真道:「我說,不送了。」
鄭彥只得點點頭,笑笑出去。段嶺看武獨,武獨點頭,段嶺便起身將鄭彥送到門外,鄭彥騎上馬離開,奔霄卻等在大門外,顯然是鄭彥帶回來的。段嶺便將牠牽進後院馬廄裡頭安頓好,拍拍牠的頭。
「他是替太子探口風來的。」段嶺朝武獨說。
「你知道?」武獨詫異道。
段嶺點頭道:「應當是太子讓他順便將奔霄牽過來。」
武獨沉吟不語,倚在房中側榻上,氣定神閒的,眉頭卻微微擰著。
段嶺始終有些事想不明白,一路上也沒有問武獨,如今鄭彥提到郎俊俠,便又將一些往事翻了出來。父親囑咐的話,上京城中偽裝成車夫的他,在國家危難之時,帶回了一個假太子,打亂了牧曠達的布局……那天在酒菜裡下的毒,將自己拋下江去,卻在潼關重逢之時,陰錯陽差地留了自己一命,更不惜與賀蘭羯死鬥,顧全自己安危。
「我記得在你剛救我回來那會兒,說過我中的毒是寂滅散。」段嶺問:「那是什麼東西?」
「一種寂滅之毒。」武獨答道:「中毒之人,將不能說話,不能思考,渾渾噩噩,如同殭屍一般,猶如假死。若不在十二個時辰內餵下解藥,餘生便將成為行屍走肉。」
段嶺心中猛地一抽,說:「那他也許不想殺我。」
武獨看了段嶺一眼,答道:「也許,但也很有可能想將你變成毫無思想、僅奉他命令列動的一具屍體,留著你,來日興許還有用。」
「這種毒是哪兒來的?」段嶺不禁奇怪道。
「古時有人用這藥控制君主或官員。」武獨說:「譬如說,某位封疆大臣勢力廣闊,一手遮天,不能就死,便以寂滅散暫時控制住,到得目的達到後再處理屍身。」
有解毒的機會,也就證明郎俊俠並非真想斬草除根,至少在那一刻不是。段嶺曾經不只一次想過這個問題,會不會是郎俊俠的毒,只是為了保護他,投毒後扔進江中,翌日再來救?但這想法實在也太一廂情願,若再相信郎俊俠,自己只能用愚蠢來形容了。是以這些時日,他從未朝武獨詢問過。
「他在潼關,是不想殺我的。」段嶺又說。
「殺了你。」武獨說:「潼關必亂。從那夜見你我在一處後,這廝便已留意於你。咱倆去潼關,顯然是執行任務,未曾判斷清楚,再對你下手,不僅徒令人生疑,更容易破壞牧相的計畫,有時候,他們與牧家還是需要共同進退。」
「他有兩次機會可以殺我。」段嶺皺眉道:「卻都沒有下手,一次在秦嶺孤峰上,一次在潼關的城牆。」
武獨開始不高興了,卻不敢對段嶺發火,敷衍地「嗯」了聲。
段嶺是大陳……不,自古以來最有眼色的太子了,他觀察武獨,知道武獨不喜歡他對郎俊俠開脫式的分析,便不再繼續下去了,找了藥來,給武獨的腳踝上藥。腳傷已好得差不多了,再過些時日,便可行走無礙,只是要飛簷走壁,還須得再休息一段時日。
「你生氣了嗎?」段嶺問。
「什麼?沒……沒有。」武獨不自在地答道。
段嶺一邊給武獨腳踝上藥,一邊撓他的腳心,武獨忙道:「別鬧!」
段嶺還在整他,武獨臉上發紅,卻拿段嶺沒辦法,更不敢揍他,只能靠在榻上大叫。最後實在沒辦法,翻身一把抓住段嶺,把他壓在自己身下,單手抓住他兩隻手腕,兩人哈哈哈地鬧。
段嶺忙道:「不玩了!不玩了!」
「還敢不敢?」武獨鎖住段嶺手腕,在他耳畔低聲道:「莫要逼武爺教你好看。」
段嶺看著武獨,兩人臉上都帶著紅暈,段嶺眼裡帶著笑意,彼此更覺心神蕩漾。這時候武獨放開了段嶺,讓他坐好,一時間兩人都有點訕訕,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幸而外頭敲起門來,武獨便道:「誰?」
段嶺忙去開門,牧磬卻自己闖了進來,叫道:「王山!等得我好苦!你究竟做什麼去了!」
段嶺再見牧磬,心裡仍是開心的,忙上前與他抱了一抱,突然想到武獨說過自己薄情的話,忍不住瞥武獨,見武獨也在看他,那表情收在眼中,自己都覺尷尬。
「去潼關了。」段嶺看了眼武獨,武獨才說:「進來吧。」
雖是牧府,但側院中武獨才是一家之主,得了武獨允許,牧磬才脫鞋進來。
段嶺擺放案几,給牧磬燒水泡茶,依舊是給武獨先喝。牧磬倒是不介意,笑呵呵的,朝段嶺說:「他們說武獨受了些傷,只不知你明天來不來念書,讓我先等著,我忍不住了,就先來看看你。」
「這些日子裡怎麼樣?」段嶺問。
「別提了——」牧磬叫苦不迭,說:「悶出個鳥來。」
段嶺看看武獨,武獨說:「王山明日起便去與你讀書,一切照舊。」
「今夜來不來見我爹?」牧磬問:「爹就讓我來問問你。只是家宴,人不多,也不喝酒。」
段嶺看武獨,知道始終躲不過,回來還是得朝牧曠達匯報清楚。
武獨答道:「本該去見見他,耽擱這一天,丞相不怪罪,自然要去的。」
牧磬突然有些奇怪,覺得武獨出了一次門回來,變得客氣多了,再不像從前眼睛長在頭頂上,答話全是「哼」「唔」等語氣。
「那我去說一聲。」牧磬說:「入夜在邊閣裡頭等你。」
段嶺又要起身送客,牧磬卻擺擺手示意不必送了,逕自出去。
「我猜牧相今夜定會盤問我許多事。」段嶺說:「就怕問太多了露馬腳。」
武獨擺手道:「不用擔心,包我身上,我替你答。」
武獨一手撐著榻下來,段嶺去找衣服給他換上,相府特地準備了上好的袍子,果然人靠衣裝,武獨身材好,且長得高,換上蜀中上錦裁就的新袍,繫上武袖,整個人感覺都不一樣了。段嶺則穿著深藍色的袍子,如同一塊美玉般光彩照人。
還少個腰墜,段嶺看著武獨的腰間,心想,並抬眼看他,哪天得回了玉璜,便該將那另一半「錦繡河山」繫在他身上。
「怎麼?」武獨目不轉睛地,只在段嶺身上瞥。
「沒什麼。」段嶺笑道:「走吧。」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相見歡(三)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大眾文學 |
$ 237 |
BL/GL |
$ 255 |
華文 |
$ 255 |
小說/文學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相見歡(三)
《錦衣衛》、《金牌助理》作者非天夜翔最蕩氣迴腸,俠骨柔情之作!
他是從卑微之地出身的落難王子,
在亂世之中艱難生存。
然而終有一天,他將回歸。
一曲相見歡,串起多少恩怨情仇,多少戰亂別離。
他名王山。
在牧相府裡,在潼關戰場,在江州皇宮,
在恢復真實身分之前。
誰都不知道,堂堂太子,
不僅成為刺客小廝,丞相門生,
居然還考了科舉,中了進士。
被人取代了的滋味,原本該是極痛苦的,
可他身邊有了武獨。
與他兩情相悅,帶他遊山玩水,和他朝夕與共,
讓他茫然無措的心,從此安定下來。
但對取代了他的「太子」來說,
他的存在,只會讓人坐立不安。
當他為了收回父親的領地,自願前往鄴城任太守時,
從皇宮奔馳而出的影衛,將陰謀的手,
悄悄伸向戰雲密布的邊城……
作者簡介:
文青一枚,酷愛旅行,寫作與電影,講故事的人,沉溺於童年的幻想者,我有許多故事講給您聽,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世界,歡迎您來到我精神的樂園,一張門票,帶您踏上與現實截然不同的奇妙之旅。
作品有:《武將觀察日記》、《飄洋過海中國船》、《國家一級註冊驅魔師上崗培訓通知》、《錦衣衛》、《金牌助理》等。
個人微博:http://weibo.com/u/1743310520
TOP
章節試閱
第二十一章
秋日烈陽萬丈,李衍秋駐馬太和殿外,暮風翻飛,吹起兩道旗幟。
「吾皇萬歲!」黑甲軍排山倒海,單膝跪地。
謝宥與蔡閆慢慢趕來,李衍秋卻停著,出了會兒神,剛才有那麼一剎,他似乎感覺到了什麼。
「辛苦了。」李衍秋說。
黑甲軍如潮水般散開,讓出一條路,李衍秋進了正殿內,江都皇宮幾經風雨,如今重作修繕,足比西川還要豪華。太監上前,為李衍秋解下斗篷,李衍秋便沿著走廊過去。
鄭彥、郎俊俠也到了,李衍秋經過東宮外,往裡頭瞥了一眼,見郎俊俠正坐在走廊下吹笛子,李衍秋經過,他也不起身行禮。
「這一路上也累...
秋日烈陽萬丈,李衍秋駐馬太和殿外,暮風翻飛,吹起兩道旗幟。
「吾皇萬歲!」黑甲軍排山倒海,單膝跪地。
謝宥與蔡閆慢慢趕來,李衍秋卻停著,出了會兒神,剛才有那麼一剎,他似乎感覺到了什麼。
「辛苦了。」李衍秋說。
黑甲軍如潮水般散開,讓出一條路,李衍秋進了正殿內,江都皇宮幾經風雨,如今重作修繕,足比西川還要豪華。太監上前,為李衍秋解下斗篷,李衍秋便沿著走廊過去。
鄭彥、郎俊俠也到了,李衍秋經過東宮外,往裡頭瞥了一眼,見郎俊俠正坐在走廊下吹笛子,李衍秋經過,他也不起身行禮。
「這一路上也累...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非天夜翔
- 出版社: 平心工作室 出版日期:2017-07-24 ISBN/ISSN:97898657109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寬 14.8 cm × 長 21 c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