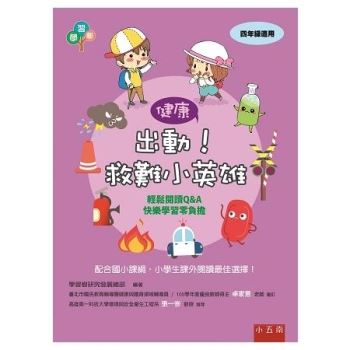他為河北太守。
武獨則為河間校尉。
兩人一文一武,為大陳鎮守邊關,
抵禦來自元兵的攻擊。
而帶領元兵的,是他自小的玩伴,拔都。
在明知他真實身分的情況下,
這不愛洗澡,沉默寡言的質子,
竟一心想擄他在身邊,甚至不惜以退兵相誘!
與此同時,幼年曾有一面之緣的遼國年輕帝君耶律宗真,
不僅慨然借糧,還與段岭聯手,共退大元洶湧來襲的騎兵!
而真相不會被永遠掩埋,
他的身分,正一點一滴的,被有心人揭發開來。
本書特色
《錦衣衛》、《金牌助理》作者非天夜翔最蕩氣迴腸,俠骨柔情之作!
他是從卑微之地出身的落難王子,
在亂世之中艱難生存。
然而終有一天,他將回歸。
一曲相見歡,串起多少恩怨情仇,多少戰亂別離。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相見歡 四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中文書 |
$ 237 |
大眾文學 |
$ 237 |
BL/GL |
$ 255 |
華文 |
$ 255 |
小說/文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相見歡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