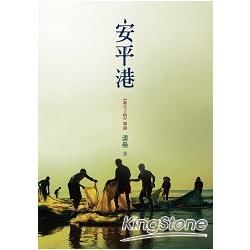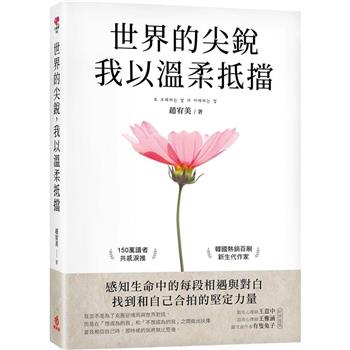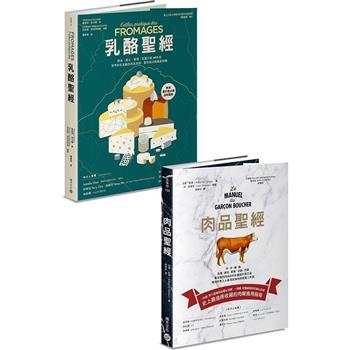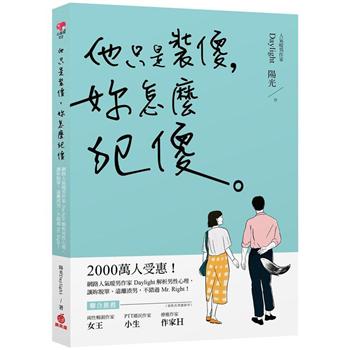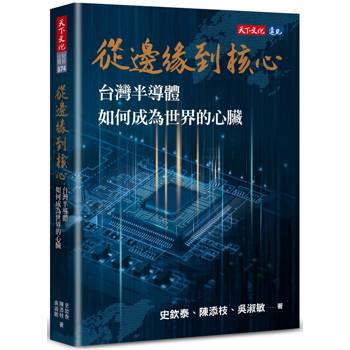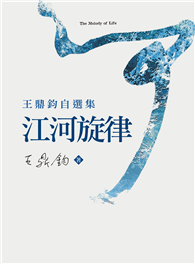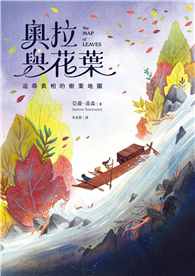外省青年秦宇,隻身來到台南安平。在這個只說閩南語的漁村裡,唯有暴躁的「金發號」船長蘇大傳願意接納他以一個外來旱鴨子加入討海人的行列。
孰料蘇大傳遭逢船難,生死不明;秦宇則在這段期間陰錯陽差的愛上了蘇大傳從小單戀的林秋子,成為獨當一面的船長。
幾個月過後,蘇大傳離奇現身,這三個人的愛恨情仇,將在寧靜的漁村掀起什麼樣的風暴……
討海人的世界,只有魚,是命定的追求。
一部早期台灣討海人的生活誌、電影〔情人石〕的劇本原型──潘壘長篇小說《安平港》,刻畫五十、六十年代的南台灣漁村生活:素樸的生活風貌,壓抑的社會氣氛,以及外來者對在地村落的衝擊;歧視與被歧視,男女之愛與兄弟義氣,種種衝突,終將在安平小鎮濃濃的人情味裡,獲得消解與平靜。
作者簡介:
潘壘,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生於越南海防市。一九四九年來台,獨資創辦台灣光復後第一本文學雜誌──《寶島文藝》月刊。一九五二年起,全心投入小說創作,出版了《紅河三部曲》、《魔鬼樹》、《歸魂》、《狹谷》、《安平港》等二十三本暢銷著作,為台灣五○年代的文壇巨擘。其中多本著作被改編為電影登上大銀幕;長篇巨著《魔鬼樹》更在一九七二年被華視改編為連續劇,紅極一時。
一九六○年代進入「中影製片部」編導組,自此投身電影界編寫劇本。一九六三年受邀進入香港「邵氏」,是邵氏四大文藝導演之一,更被譽為保守年代最勇於創新的作家導演。七○至八○年代已編導過四十三部電影,合作過的演員有唐寶雲、鄭佩佩、王羽、李烈、柯俊雄、張美瑤、龍君兒、胡燕妮、胡茵夢等港台兩地知名巨星演員。
一九六二年以《一萬四千個證人》獲得第一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同年再以《颱風》一片代表台灣參加「亞洲影展」,揚威海外;一九六四年以《情人石》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入圍肯定。其他電影代表作還有《金色年代》、《蘭嶼之歌》、《毒玫瑰》、《落花時節》、《新不了情》、《紫貝殼》、《天下第一劍》等片。
二○一四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了《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訴說這位縱橫文壇、馳騁影壇的傳奇人物!
潘壘身為作家兼導演,其創作的小說或電影,不論在哪個年代都堪稱跨時代的經典之作!
章節試閱
一
愁悶的,南臺灣的八月,在安平漁區漁夫們近乎焦渴的等待中過去了。
這年的雨季,斷斷續續的,拖延著;如同這年淡季的景況一樣,使他們愈加感到難耐。在六月的下旬開始,半數的漁船已經上塢了,他們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修補和添置網和漁具;在這些閑散的日子裏,除了收採他們在內灣和運河沿岸用人工養殖的牡蠣,間或亦有些漁船出海作業;但,每當他們回航靠近內港運河路漁會的碼頭,將一小筐漁獲物從舵前的小艙裏提出來,帶著有點靦腆的神態將它擱在磅秤上,等到驗收員用一種揶揄的聲音喊出那個可憐的數目時,他們偷偷的互相望了一眼,還沒等漁會的拍賣人(龔金發或者是郭成文)喊價拍賣,便隨手接過那張小小的檢量單,匆匆的走開了。
然後,他們到妙壽宮前面場子上的麵食攤棚裏坐下來,一面大口大口的喝著公賣局釀製的廉價太白酒,一面用粗黑的手指在板桌上計算著這次出漁的所得:先扣掉柴油耗量、漁冰;再除開船主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及百分之○‧五的保險費……
於是,將餘下的數目再按出漁的人數分攤。
「每份二十三塊五角!」
這個數目顯然是有些令人難堪的,假如在冬末和春二三月的烏魚汛蝦汛,也許僅夠繳付一次出漁的保險費;可是,他們沒有絲毫懊惱和怨懟―對於天氣和季候,他們永遠是虔誠的―接著,他們粗野地抹去板桌上的字跡,隨手拿起酒杯,笑著詛咒起來:
「伊娘!總比悶在屋子裏好些!」
那些晚上,他們麕集在延平街(舊名市仔街,是這兒唯一像樣的街道)菜市場附近的茶室和彈子房裏,辯論著安平為甚麼不開一家酒家之類的問題;或者在玩五色紙牌。而海興里的小伙子們,則裝模作樣的在他們的「海頭社」票房裏走著臺步,拉起嗓子在唱著臺灣腔的京戲―雖然他們用重金聘來的那位湖南籍教戲的琴師不斷的矯正他們的發音。
至於那些上了一點年紀的漁夫,大多躺在屋前的竹椅上納涼,或者帶著孩子們到那兩家小得像鴿子籠似的戲院子裏,在條櫈上自由自在的支著腿,看那種像默片時代一樣,外加臺灣話解釋的電影……
總之,這種鬆散的生活使他們厭倦,彷彿除了向海、自然和他們自己的命運搏鬥之外,生命便了無意義―當然,他們是永遠不會了解這些的。對他們而言,這祇是一種本能,在這種本能裏面包含著環境的感染,和祖先在血液裏遺傳的一點神秘的力量,使他們永遠那麼癲狂而執拗地,在海與死神的手中,搶奪那在他們認為是具有無上價值的―魚!
這是絕對的,魚,在漁村的價值上,在漁夫生命的意義上,就是一切,包含著一切。
所以,儘管是在淡季裹,儘管上次出漁的結果是怎麼使他們難堪,但等到那種失望和怠倦漸漸在一個新的,比上一次更激烈的衝動中淹沒之後,他們又帶著那種頑強而傲慢的笑意出海了。於是,他們又帶著沉鬱的神色回來……
二
現在是九月的上旬,絕望的季節已經過去了。
由於接近「三牙」「烏口」魚汛,安平漁港驟然騷動起來。造成這騷動的另一個原因,是月初以時速廿五公里掃過本省西南海面的「麗泰」颱風,在恒春、高雄、紅毛港及沿海各地漁村所造成的災害。這幾天安平的人們在熱心的談論著:報載各地的災情,「大安」「金瑞滿」等近二十條失蹤漁船的下落。雖然在這次風災裏,他們亦有損失,但和那些地方比較起來,他們不得不深深的為自己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遭遇過颱風的經驗,不難想像出那種悽慘可怕的情形。
這次颱風過後,接連著好幾天的壞天氣。就在那些比較謹慎的漁夫們等待那風尾過盡再出海時,蘇大傳的「金發號」和其他幾條由年輕的伙子們操作的漁船,已經搶先出海夜間作業了。
所以第二天的一早,好些年老的漁夫便圍集在漁會外面拍賣市場的棚簷下,談論著這件事。他們一致的認為,這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這些時候的浪潮和氣流是變幻無常的;雖然他們也承認這是個捕魚的好機會。
他們繼續談論著,用一種善意的詛咒責備著這幾個「忙著去投胎」的小伙子們。後來,他們憶起他們年輕時的那些日子……
林金水孤孤獨獨的站在棚柱旁邊。他始終沒有參加那些老漁夫們的談話,只是靜靜的站著,凝望著右角的運河口,陷入一種紛擾的思想裏。
從外貌上看,他似乎比他的年齡更蒼老;雖然才四十七歲,頭髮已經半禿了,臉上的皺紋,像是佈滿著一條條粗細不等的繩索,那雜亂而叢密的鬍髭之中,隱蔽著兩片厚而濶大的嘴唇,那依然是很堅固的上門牙,微微有點外露。看來,他的神情十分疲乏,以致那雙黃渾的眼睛裏蒙著一層陰翳。他站著,左手支著一把半舊的黑布雨傘,他那寬大的肩背證明他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身強力壯的漢子―或者就說是一個能夠吃苦耐勞的漁夫。當然,他現在也是,只不過在臺灣光復後的第三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後,他便突然失去了這種勇氣和感到自己已經衰老了;直至現在,在他的心靈裏,依然將這件事引為一種恥辱。每當寂寞的時候,他便細細的回味著那些現在讓他感到悲痛的往事,然後再濾過那些悲痛,找尋一些慰藉。而這種慰藉,卻是在他痛愛的獨養女兒的身上所找尋不到的。
除了座落在金城里︵安平最富庶的區域︶的一棟水泥磚房,他擁有兩條漁船和三甲多虱目魚塭。他惟一異於普通船主的,就是他不到自己的船上去操作―安平沒有兩條漁船以上的大船主。隸屬這個漁區裏的一百二十多艘小型動力漁船,有半數以上是漁民私有的;而擁有一條漁船以上的船王,除了自己親自操作,則將另一條租與其他無船的漁民。
當昨天晚上聽到他租給蘇大傳的漁船「金發號」搶先出海的消息之後,他失眠了一整夜。一個奇怪的思想永遠纏繞著他,使他無法讓自己平靜下來。如果說這是為了他的漁船的話,不如說是為了蘇大傳比較真確。
現在,他完全沉耽在那個不幸的回憶裏:對於這事情發生的時間,他已經有點糢糊了,他祇記得,那個時候他還年輕。就如同現在這些伙子們一樣,對海無所畏懼,他和蘇大傳那已死去的父親―蘇火塗同在一條船上,那是他們合資建造的漁船,在經過無數次「有意的冒險」之後,突然,有一次不幸來了……
他驀然從回憶中軟弱而痛楚地垂下頭,半晌,他用瘖啞的音調低喊道:
「也是在這個時候,也是在一次颱風之後……」
那個奇怪的思想緊跟著又來了。
他忽然像是受著驚嚇似的急忙抬起頭,悽惶地向四周張望著。
「金水,」那個渾號叫做「蝦背」,年紀在七十開外的謝天來蠕動著他那乾癟而鬆弛的嘴唇,打趣地問道:「怎麼,你怕你的船會……飛掉啊?」
「哦……」林金水纔回過神,對方已經怪聲笑起來。
「你少擔這個心事吧!」老人勸慰道:「大傳這小子是甚麼手腳,你還不放心?」
林金水連忙搖搖頭,吶吶地應著:
「沒……沒這回事。就是您的話呀,大……大傳這小子的手腳,就和他爹一樣―不過,就……就是有點蠻!」
「蠻?」蝦背詭譎地眨眨眼。「你當年也不老實啊!你還記得﹃老金發號﹄嗎?」
「記得記得,忘不了!」
在片刻的沉思後,謝天來用慨嘆的聲音說:「安平就是安平,輩輩都出一兩條好漢!」
「您也是好漢之一呀!」林金水緩和地笑笑。
「當然!」說著,老人隨即心灰意懶起來。「唉!到底是老了―就算是推上十年八年吧,那個敢叫我一聲﹃蝦背﹄?我不打掉他的牙齒才怪呢!」
「他們是叫您﹃謝伯﹄呀。」
明白對方的心意,老人感激地笑了,然後解嘲地反著手去拍拍自己那佝僂的背脊,說:
「其實,也很像―不是嗎?」
林金水沒回答。就在他一時想不出什麼恰當的話語去安慰這位老漁夫,而感到尷尬不安時,前面內港的入口忽然有人大聲叫嚷起來:
「他們回來啦!」
人們隨即從沿岸那些低矮而黝暗的屋子裏走出來,擁到堤岸邊去,甚至那些正在熱烈地談論著「風尾」問題的老漁夫們,也停止了他們的談話,走出棚簷。
只有林金水依然屹立不動。他震顫了一下,低下頭;霎時間,他連重新抬起頭的力量都完全失去了。
一
愁悶的,南臺灣的八月,在安平漁區漁夫們近乎焦渴的等待中過去了。
這年的雨季,斷斷續續的,拖延著;如同這年淡季的景況一樣,使他們愈加感到難耐。在六月的下旬開始,半數的漁船已經上塢了,他們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修補和添置網和漁具;在這些閑散的日子裏,除了收採他們在內灣和運河沿岸用人工養殖的牡蠣,間或亦有些漁船出海作業;但,每當他們回航靠近內港運河路漁會的碼頭,將一小筐漁獲物從舵前的小艙裏提出來,帶著有點靦腆的神態將它擱在磅秤上,等到驗收員用一種揶揄的聲音喊出那個可憐的數目時,他們偷偷的互相望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