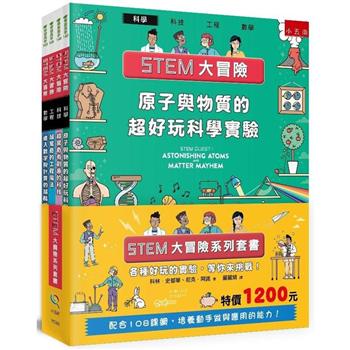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藝術大師的苦樂人生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 408 |
社會人文 |
$ 422 |
中文書 |
$ 422 |
藝術人物傳記 |
$ 432 |
藝術家傳記 |
$ 432 |
藝術設計 |
$ 432 |
美術 |
電子書 |
$ 480 |
藝術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藝術大師的苦樂人生
本書輯入了作者近十多年來所撰寫的知名藝術家和民間工藝高手的生平傳記。傳主所涉及的藝術領域,涵蓋戲劇、繪畫、書法、篆刻、微雕、文博、收藏等門類。文章以紀實文學的手法,如實記錄了大師們為追求藝術完美,孜孜不息、磨礪精進的執著精神,及所作的突出貢獻,並以他們絢麗多彩卻又坎坷多舛的人生經歷,回望了近幾十年中國的社會狀況與政治風雲。文中的故事、情節乃至細節,均為作者深入採訪、多方印證所得,內容翔實對於研究中國政治史、法制史、戲劇史、繪畫史、篆刻史具史料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