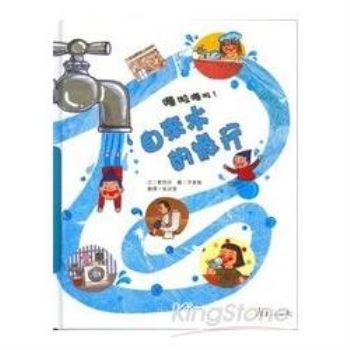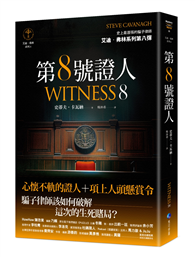《金色年代》,是我確定自己的一部寫實的作品。
如果我現在已經拔起了泥足,認識甚麼叫做「小說」,甚麼叫做「故事」的話,
那麼我祇能這樣回答自己:
「那是因為你已經懂得觀察,懂得思想,懂得生活。」
──潘壘
平凡故事裡,有著不平凡的愛──潘壘第一部以「平凡人」為主角的寫實小說!
《金色年代》,是我確定自己的一部寫實的作品。
如果我現在已經拔起了泥足,認識甚麼叫做「小說」,甚麼叫做「故事」的話,
那麼我祇能這樣回答自己:
「那是因為你已經懂得觀察,懂得思想,懂得生活。」
──潘壘
這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但錯誤的愛,卻往往比恨更令人難堪。
金家與錢家,不僅在字面上有關連,更是私交甚篤的世交;
自從錢先生在五年前去世後,錢太太對獨子錢聖謚的溺愛,更是到了超乎常態的地步。
她千方百計,就是想要撮合自己的獨子與金家千金的婚姻,
但屬於青春的各種彆扭、徬徨、與不安,
從來就不若寫好的劇本般完美。
這是一個發生在平凡人身上的故事,
在一個象徵信賴、溫暖、與愛的偉大時代,
平凡的小人物,投身到這個年代裡,
為了自己光輝燦爛的將來而努力。
這就是屬於他們的金色年代。
作者簡介:
潘壘,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生於越南海防市。一九四九年來台,獨資創辦台灣光復後第一本文學雜誌──《寶島文藝》月刊。一九五二年起,全心投入小說創作,出版了《紅河三部曲》、《魔鬼樹》、《歸魂》、《狹谷》、《安平港》等二十三本暢銷著作,為台灣五○年代的文壇巨擘。其中多本著作被改編為電影登上大銀幕;長篇巨著《魔鬼樹》更在一九七二年被華視改編為連續劇,紅極一時。
一九六○年代進入「中影製片部」編導組,自此投身電影界編寫劇本。一九六三年受邀進入香港「邵氏」,是邵氏四大文藝導演之一,更被譽為保守年代最勇於創新的作家導演。七○至八○年代已編導過四十三部電影,合作過的演員有唐寶雲、鄭佩佩、王羽、李烈、柯俊雄、張美瑤、龍君兒、胡燕妮、胡茵夢等港台兩地知名巨星演員。
一九六二年以《一萬四千個證人》獲得第一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同年再以《颱風》一片代表台灣參加「亞洲影展」,揚威海外;一九六四年以《情人石》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入圍肯定。其他電影代表作還有《金色年代》、《蘭嶼之歌》、《毒玫瑰》、《落花時節》、《新不了情》、《紫貝殼》、《天下第一劍》等片。
二○一四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了《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訴說這位縱橫文壇、馳騁影壇的傳奇人物!
潘壘身為作家兼導演,其創作的小說或電影,不論在哪個年代都堪稱跨時代的經典之作!
章節試閱
一
這是金祖灝金先生擧家由港遷臺的第三天,錢家從一大早就開始忙亂起來;自從錢先生在五年前去世之後,這簡直是罕有的現象。
這五年來,在這棟座落在中山北路三段的假三層花園洋房裏面,幾乎連稍為大一點的聲音都沒有發生過。錢太太摒絕一切應酬,甚至連大門也難得邁出一步。汽車當然賣掉了,但並不是為了錢,而是錢太太怕聽汽車的喇叭聲,它會使她想起錢先生從公司裏回家來的情形。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覺得,丈夫的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太突然了,從發病到死亡,祇不過短短的半個月。她後悔在他中風之前沒注意他的體重和飲食。她後悔—總之,她後悔自己以前做的每一件事情。因此,她的悲痛就如同這些記憶一樣永恆。從那一天開始,她便將「半」個心靈貢奉到觀音菩薩的面前;去追悔,去尋求在這現實生活中她再也得不到的慰藉;而將另「半」個心靈,去愛護她那個已經二十二歲的獨子聖謚。
當然,按情理說,丈夫去世了,對於藉以傳宗接代的命根子倍加愛護是必然的事,但,她的愛和關切卻超乎常態:在她的眼中,他—錢聖謚愈來愈小了,小到像距離成年自立還有數不完的日子似的;她把他當作一個走路會跌倒的孩童,她注意他的衣著飲食,探究他的感情,忖測他的思想,幾乎連他的呼吸也得細細的數過。
可是,對於那個剛考進臺灣大學的女兒錢子蓉,她卻完全忽略了。彷彿這個家裏,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似的;雖然在這個大院宅裏面,除了下女阿美和一個叫做老袁的廚子之外,再沒有別的人。
現在,錢子蓉將她那輛唸中學時騎到現在的紅色女跑車從車間裏推出來,準備到學校去。錢太太正好在門口和老袁商量備辦的菜式,於是順口叮囑她下午早點回家來幫忙。
「我還能幫些甚麼忙?」錢子蓉無精打采地反問。
「甚麼忙?」錢太太有點生氣地說:「你就不可以陪金伯伯和家碧表姐他們談談啦?」「唔,還有那位姨太太!」女兒冷冷地補充一句。
錢太太正要責備她,她已經跳上腳踏車,使勁的踏走了。錢太太楞了一下,然後打發走廚子,再回到屋裏去。
「說話沒分沒寸的,越來越不像樣了!」她祇是這樣一想,便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由她去,反正我和她說不上三句話—女大不中留,一點也不錯!」
這時,她纔看見阿美提著掃帚從樓上下來。
「我不是關照過你,樓上慢一點打掃的嗎?」她向梯口走過去,壓下嗓門呵責。
「大少爺都已經起來了!」
「他這麼早起來幹甚麼?」她問阿美,但對方沒有回答,而她也像是並不打算盤究下去似的,擡頭望望梯口。
阿美翻翻眼睛,走開了。錢太太好一會兒纔回轉身體,她環視著這個光亮潔淨的柚木地板大客廳,纔想起自己正忙著安排今天晚上為金祖灝先生洗塵的宴會。
「阿美!」她叫道。
下女來了,她又一時想不起要吩咐她甚麼,於是擺擺手,煩燥地說:
「你去忙你的吧,想起來了我再叫你—哦,大少爺的早點弄好了,就端來給我。」
阿美走開後,她忽然覺得現在自己對甚麼事情都那麼生疏,少少幾個客人就弄得手忙腳亂;她真不明白以前那些熱鬧的日子自己是怎麼應付過來的。
她忽然感到軟弱而疲乏,便摸著旁邊的沙發坐下來。但,適纔那個思想仍然攪擾著她:她記起當他們從上海到臺灣,剛搬進來時的情形;她還記得傢俱的擺法,後來,這個客廳便充滿了人聲笑語,一次接著一次的飲宴……
牆角的落地琴鐘響了,她醒覺過來。
「哼!」她苦澀地笑了笑,「這還有甚麼好想的!」
她知道自己這些感觸,完全是由金家引起的。
金家和她們錢家,非但字面上有關連,而且還是親戚。在大陸上,兩家共過事業,都發了點財;後來大陸淪陷了,錢先生比較有見地,搬來臺灣。而金祖灝金先生呢,先是留戀不捨,結果幾乎傾家蕩產,後來總算給他設法逃到香港。憑著以前的一些關係,再加上他的頭腦靈活,三幾年功夫,竟然將家業又重新撐起來。
這一點,錢太太對這位金胖子(這是熟朋友們慣常稱呼他的名字)佩服之至。不過,也有一點是使她大為不滿的:那就是金胖子並沒有將元配夫人—錢太太的表姐從內地接出來。這還不說,還在香港討了小的。據那天她在機場見到的,那位金太太的年紀很青,比家碧大不了幾歲,看打扮就知道不怎麼正派。
「倒是家碧這小鬼長大了!」錢太太愉悅地向自己說:「我還記得,她比聖謚小兩歲,比子蓉大兩歲,今年也滿二十啦……」
這就是她這幾天心裏的一點秘密。她覺得,以她的聖謚去配金家的家碧,是最門當戶對不過了。她記得以前他們兩家人時常開他們的玩笑;再說,金家祇有這麼一個女兒,而她的聖謚也是獨子,以兩家的關係和財力,她看不出半點說不攏的理由。而且,這事情如果成功了,那麼自己手頭上的錢,總算找到了穩妥的出路,比放在銀行裏生息好得多。對於金胖子的頭腦,她是絕對信任的。
所以那天當她突然收到金祖灝先生要來臺灣謀發展的信之後,便馬上回電表示歡迎。照她的意思,三樓反正空著,金家來臺之後,最好先住在一起,熱點鬧,等到找好屋子再說。那曉得金胖子橫說豎說總是不肯,說是怕打擾了她,一下飛機,便搬到圓山飯店去了。
這一來,更表明了金胖子今天的身價。當然,錢太太也是見過世面的,即使現在丈夫死了,事業完了,但手頭上還有個三幾百萬。她可以說根本無心去巴結金家;她的目的,說穿了,祇是想借這個機會替兒子在社會上安排一個出路而已。
因此,在今晚這個洗塵宴會上,她連一個陪客也不請。她認為這樣談起正事來方便些。而且她也有這份自信,她相信自己能夠打動金胖子,把兩家的實力併起來,好好的幹一下。
阿美端著早餐來了,她照例將托盤遞給錢太太,讓她親自端到樓上兒子的房裏去。
錢太太先檢查了一下托盤裏的早餐,然後接過來,當她正要上樓,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佛堂裏的香你給我點了沒有?」她緊張地問。
「有點啦!太太叫我我就去點了!」
「你一定忘了先洗手?」
「有洗啦!」阿美用一種像是受了委曲的,不純正的國語分辯。
「阿彌陀佛!」錢太太鬆下一口氣,然後返身上樓。
她一邊走,一邊在想:在習慣上,她每天的早課是唸九遍心經,三遍金剛經(這差不多就打發掉一個上午),今天因為忙著請客的事,連香也要下女代點;雖然這也並不是沒有過的事,但心理上總覺得有點大不敬。所以,她幾乎是以一種責備的心情要自己在晚間補唸,同時還要多唸幾遍。
她用身體推開兒子的房門,看見聖謚連衣服都穿著好了。他站在窗前俯望下面的園子,像是在等待些甚麼。
現在,他回轉身,他的母親不解地問:
「怎麼,你這麼早就要出去?」
錢聖謚並沒有回答母親的話。他問:
「小李早上來過沒有?」
錢太太放下托盤,慈愛地笑著回答:
「你的小李那一天能夠不來!」
這是實在話:小李是錢聖謚中學時代的同學,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變成了錢聖謚的影子,寸步不離;錢聖謚需要他,比需要自己的母親更甚,因為他有許多令人無法想像的過人之處。小李的身材矮小,距離他夢想的五尺二寸還差一寸,但,這無損於他的尊嚴,「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矮小的」。像他稱呼那些身材比較矮小的空軍一樣,他叫自己做「袖珍小生」;他的相貌,使你覺得熟悉,而分不出它那兒美那兒醜。他是樂天的,彷彿一切都為他個人而存在,這點性格,他在錢家表現得淋漓盡緻,比在自己的家中生活得更自然。在學校時,他幫助錢聖謚作弊,做狗頭軍師,出鬼主意;他甚麼都懂,而且甚麼都來,除了不能養孩子之外,這個世界似乎沒有甚麼可以難倒他的。但,這還不是使錢聖謚折服的原因,最重要的,卻是他的兩條腿和那張嘴。他肯跑腿,甚麼事情他都那麼熱心忠誠;至於那張嘴,更使平常拿不定主意的錢聖謚,凡事都聽從他的主意。
這方面錢太太對他也同樣的賞識;當他伯母長伯母短地喊的時候,心中有說不出的舒服。
「祇有小李最瞭解我!」這是錢太太常說的話。因為在這個家中,祇有小李對她的嘮叨聽得津津有味,對她「愛」錢聖謚的一切「措施」,都予以衷心的讚揚。
以錢聖謚休學這件事情來說,小李就是最得力的擁護者。
根據錢太太的想法:目前大學畢業之後,男孩子都得到鳳山去受兩年預備軍官訓練。這種訓練,她在新聞片上看到過:在大太陽下跑啦,十幾個人拋一根大木頭啦,在爛泥地上爬啦……等等—她的聖謚絕對吃不下這種苦頭。而且,一頭在臺北一頭在鳳山,相隔這麼遠,假如有點傷風咳嗽,誰去照顧他?她越想越覺得政府這件事情辦得沒有道理!他的聖謚是獨子,兵役法上也允許獨子緩召,為甚麼大學畢業之後就不能「緩訓」?或者「免訓」?總之,為了不放心兒子受訓,在錢聖謚唸大四的時候,她以患神經衰弱症為由替他休學了。她覺得,唸大學的目的祇不過是混一張文憑,好在社會上謀事立足而已;但她的聖謚不需要文憑,他用不著去替別人做事。再說「大人物也沒幾個是大學畢業的」!
就這樣,錢聖謚休學了。小李在錢太太面前大大的歌頌一番,說甚麼母愛偉大,無微不至。因為這一來,以後他便有很多時間和錢聖謚在一起,他自己也祇讀到大二就以一種從來不宣佈的理由停學了。錢太太也看在這一點,認為小李和她志同道合,對他更是另眼相看。
至於錢聖謚自己呢?他無所謂—他對甚麼都無所謂。他這一生中,從來沒有遭遇到任何一個需要他自己去解決的問題。每當問題發生時,他的母親便用錢、用人事、或者用她自己的「愛的主意」替他解決了。因此,他從小便養成了依從母親的習慣;雖然,有些時候他也有反抗的念頭,但,他從來沒有實現過;他不能拒抗母親對於他的那種強烈而豐富的「愛」,他感到束手無策,他不忍心拂逆她。同時,他也了解自己,他需要她。
現在,錢聖謚向母親淡淡的一笑,便坐下來用心的吃他的早餐。錢太太則過去替他整理被褥。她一邊喋喋不休地說著話,這些話就像她每天在佛堂裏所誦讀的經文一樣,虔誠而刻板。錢聖謚連半句也聽不進去,他心裏在想,小李來了,會對他說些甚麼話?那件事情……
一
這是金祖灝金先生擧家由港遷臺的第三天,錢家從一大早就開始忙亂起來;自從錢先生在五年前去世之後,這簡直是罕有的現象。
這五年來,在這棟座落在中山北路三段的假三層花園洋房裏面,幾乎連稍為大一點的聲音都沒有發生過。錢太太摒絕一切應酬,甚至連大門也難得邁出一步。汽車當然賣掉了,但並不是為了錢,而是錢太太怕聽汽車的喇叭聲,它會使她想起錢先生從公司裏回家來的情形。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覺得,丈夫的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太突然了,從發病到死亡,祇不過短短的半個月。她後悔在他中風之前沒注意他的體重和飲食。她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