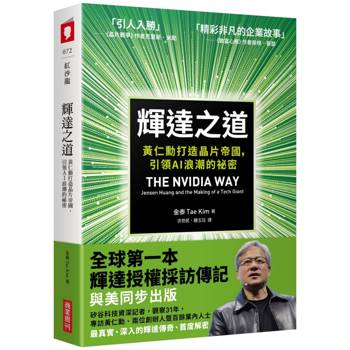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 邵氏臺灣名導潘壘依據真實經歷寫作的報導文學!
● 《靜靜的紅河》、《歸魂》、《狹谷》、《夢的隕落》等故事的原型!
● 第二次世界大戰境外中國軍隊從印度、緬甸打至國內,「上等兵」參軍的寫實經歷!
這是一本講述潘壘個人經歷的故事,一本橫跨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潘壘個人從軍三年多的自傳體報導文學。
在這本書,你可以看到許多熟悉的畫面,它們來自於潘壘的其他小說。有《靜靜的紅河》的原型,有《歸魂》對於時代的體悟,有《狹谷》的借鑑來源,更有一段親身的愛情經歷,成就了《夢的隕落》的哀戚惆悵。
曾經生澀的十八歲「上等兵」,從在昆明加入國軍開始,先是到了印度軍訓,再跟著軍隊一路打過中印邊境、緬甸,朝向國土進發,中間訓練以及戰場的艱辛,由寫實卻不失趣味的筆調,踏實地呈現出來。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最真實、也是最微小的存在,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但卻呈現了屬於小人物最為動人飽滿的人生片段。
作者簡介:
潘壘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生於越南海防市。一九四九年來台,獨資創辦台灣光復後第一本文學雜誌──《寶島文藝》月刊。一九五二年起,全心投入小說創作,出版了《紅河三部曲》、《魔鬼樹》、《歸魂》、《狹谷》、《安平港》等二十三本暢銷著作,為台灣五○年代的文壇巨擘。其中多本著作被改編為電影登上大銀幕;長篇巨著《魔鬼樹》更在一九七二年被華視改編為連續劇,紅極一時。
一九六○年代進入「中影製片部」編導組,自此投身電影界編寫劇本。一九六三年受邀進入香港「邵氏」,是邵氏四大文藝導演之一,更被譽為保守年代最勇於創新的作家導演。七○至八○年代已編導過四十三部電影,合作過的演員有唐寶雲、鄭佩佩、王羽、李烈、柯俊雄、張美瑤、龍君兒、胡燕妮、胡茵夢等港台兩地知名巨星演員。
一九六二年以《一萬四千個證人》獲得第一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同年再以《颱風》一片代表台灣參加「亞洲影展」,揚威海外;一九六四年以《情人石》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入圍肯定。其他電影代表作還有《金色年代》、《蘭嶼之歌》、《毒玫瑰》、《落花時節》、《新不了情》、《紫貝殼》、《天下第一劍》等片。
二○一四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了《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訴說這位縱橫文壇、馳騁影壇的傳奇人物!
潘壘身為作家兼導演,其創作的小說或電影,不論在哪個年代都堪稱跨時代的經典之作!
作者序
前記
我第一次穿軍服,只有六歲。那套「軍服」是父親在西服店裡特地為我訂製的,我還記得那套衣服的袖口和衣領上,都鑲有金色的帶子,樣子很怪。對於那次我能夠在兒童節遊藝會上帶頭走──當「總司令」,父親頗為自豪。以後,他一高興,便把腰一挺,用一種威嚴的,但是又有點滑稽的聲音喊我一聲:
「總司令!」
於是我便像一隻玩具木偶似的向他敬禮,然後說:
「有甚麼吩咐,皇帝!」
那個年代越南是有皇帝的,我只知道保大皇帝是最大。當我淘氣得令母親厭煩的時侯,她便莫可奈何地叫我皇帝,希望我能夠聽她的話。但是父親卻最反對皇帝,他時常向我們說,他就是因為要打倒皇帝,才「穿州越府」到「番鬼」地方來的。
於是,他便會認真地更正我的話:「叫爸爸,不應該叫皇帝!」
「但是『爸爸』沒有『總司令』大呀!」這是我的理由。
「那麼我問你──總司令有沒有爸爸?」
我想了想,覺得爸爸的話沒有錯,於是說:
「好吧,我們就派『爸爸』比『總司令』大好了!」
這樣「總司令」的遊戲,我一直玩到八、九歲。我的三個妹妹、同學,以及住在同一條街的孩子們,都成了我的部下;高與了,我便「封」他們作軍長、旅長,但可能幾分鐘之後,那位軍長、旅長便給我「革職」,甚至拖去「槍斃」──被「槍斃」的人要變成馬,讓我們當「官」的騎,想後再慢慢照「陸軍棋」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等級,一級一級的升上去。
每年七月十四日,法國人照例在大花園舉行一次國慶大閱兵,炫耀一下他們的武力。記得我十歲那一年,我隨著父親去參觀回來,父親在路上問我:
「你看他們是不是很威風?」
我沒有回答。
在法國人統治之下,越南的殖民地色彩和藝術氣氛一樣濃厚,華僑的待遇並不見得比越南人好。因此,我從小便對法國人──對一切暴力與權勢都懷著一種仇恨的心理。每當我在街頭看見同胞們被那些紅臉的警督凌辱,我便止不住渾身發抖;這種刺激一方面不斷的使我增強要做個強國子民的信念,同時亦使我萌發一種近乎瘋狂的反抗思想。
從那個時候起,我便渴望有一支槍。後亦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跨進中學那一年,我弄到了一支舊汽槍。於是,我和幾個同學秘密組織了一個「游擊隊」,專門「偷襲」法人區那些美麗住宅的門窗玻璃。
這種幼稚的行徑滿足了我心中那種神秘的英雄感,而且很快的便成為一群「愛國者」的首領。我印過標語傳單,用鞭炮火藥製過不能爆炸的「手榴彈」,還廣羅隊員,制定暗語。結果,這種不正常的發展漸漸變了質,我們天天逃學,在外面惹事生非,鬧得四鄰不安。
父親雖然對我管教得很嚴厲,但平常卻採取放任的態度,直到有一天他完全明白了真相,他憂心地向母親說:
「這小子將來如果不是個將軍,就是個土匪!」
但,父親只猜對四分之一,那就是我回國之後,竟然捨棄了美術,自動地把頭剃光,跑去當了兵──而結果只當上一個小中尉,而且只是沒有經過銓敘的「黑官」,既不是將軍,也不是土匪。
在那個年代,志願從軍是需要勇氣的。
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慘烈的階段,全國雖然大敵當前,一致對外,但是某些地區,情形並不那麼單純。以雲南一省來說,龍雲擁有他自己的軍隊,只在某一種條件之下,才聽命於中央,完全是一派軍閥作風,腐敗到極點。
因此,兵役幾乎無制度可言,買賣壯丁和別的行業一樣普遍;至於軍人待遇之壞,簡直不能用文字來加以形容,所以教育程度之低便不足為奇了。我曾經在昆明看見過師管區運送補充兵,為了害怕逃亡,竟像押解囚犯似的用蔴繩串著;一個連長要槍斃個把兵,也是司空見慣的事。由於補給不足,以及軍官們的吃缺和克扣糧餉,士兵們衣衫襤樓,形同餓殍,難怪老百姓們平常就像躲避瘟疫似的躲避軍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他們守軍紀重榮譽,毋寧是一件可笑的事。
這些事情,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使我不寒而慄。
可是,當我穿起那套破舊、發臭而且長滿了虱子的灰布棉軍服時,我的內心卻被一種幸福的激動浸潤著,覺得非常驕傲。
那時,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剛剛掀起,青年軍還沒有成立。讀過書非但沒有使我們在軍隊裡佔到甚麼便宜,反而引起過不少麻煩,老兵們都叫我們做「丘九」──這個名詞後來風行一時,變成了青年軍的別名。
從好的方面看,指我們有書卷氣,比「丘八」多一點;而壞的一面,卻是識諷我們不夠當「兵」的資格。
依據傳統的邏輯,所謂「兵」,似乎應該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老粗;要吃得起苦,要絕對服從,而且還要勇敢。所以,要達到這個標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連上有一個據說在奉軍裡當過多少年大班長的老兵曾經說過:「一個當兵的,一定要嚐過甜酸苦辣;吃耳光,關禁閉,挨屁股,這才算是『滿師』,不然只是一個『學徒』而已!」
因此,軍隊要如何把一個「老百姓」教育成一個「兵」,就不難想像了。我曾經把這種教育名之為「宗教式」的,因為它的「真理」,是要我們從痛苦中鍛鍊自己、犧牲自己。另外,還有一種「間接的」教育相輔而行,「老油子」們會帶你去玩女人,教你賭假牌,告訴你如何作弊取巧,逃避責任;當然,他們也會使你認識友情,和了解團體的意義,同時,他們還會引領你在戰火中大膽地越過災難。也只有在這種教育中,使你接觸到一種真純而原始的情感,使你從無數個善良的靈魂之中找尋到你自己。因為,人類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偽飾的,只有從生與死之間的小孔中,才能窺見你自己──那可能是一個陌生的人,連你自己都不敢認識的。
那個日子,距離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個年頭了。那些我曾經做過的每一件愚昧、荒謬和錯誤的事,現在同想起來,卻成為我這平庸的生命中最美麗的點綴了。
在我的小說裡,有很多是以我這一段「上等兵」生活為題材的,如《靜靜的紅河》、《狹谷》、《歸魂》等;但,都是不完整的,我只是擷取其中的片段,作為小說的素材而已。而這部書,我卻以一種自傳和報導文學的體裁處理它,無論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姓名,都力求真實,我由入伍出國起,而至勝利凱旋止,把許多小故事分段記述。雖然,其中部份內容實在不足為訓,但是我始終以一種虔誠而謙卑的心情描述著自己──一個有血肉、有抱負、勇敢,但是也懦怯的「上等兵」,他只是那個年代裡的無數個上等兵之中最平凡的一個而已,我不願隱匿自己的罪惡。它除了替我的生命留下一些痕跡之外,並無任何意義。因為,那個時代──那個動盪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今天軍中皆「丘九」,軍隊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從前同日而語。不過,我覺得今天的進步,正是以前錯誤的累積。出版這部書,未始不有一點警惕的作用吧!
潘壘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記於臺北市
前記
我第一次穿軍服,只有六歲。那套「軍服」是父親在西服店裡特地為我訂製的,我還記得那套衣服的袖口和衣領上,都鑲有金色的帶子,樣子很怪。對於那次我能夠在兒童節遊藝會上帶頭走──當「總司令」,父親頗為自豪。以後,他一高興,便把腰一挺,用一種威嚴的,但是又有點滑稽的聲音喊我一聲:
「總司令!」
於是我便像一隻玩具木偶似的向他敬禮,然後說:
「有甚麼吩咐,皇帝!」
那個年代越南是有皇帝的,我只知道保大皇帝是最大。當我淘氣得令母親厭煩的時侯,她便莫可奈何地叫我皇帝,希望我能夠聽她的話...
目錄
總序 無擾為靜,單純最美/宋政坤
前記
偶然的決定
巫家霸機場
喜馬拉雅山
丁江
秀才造反
開明專制
婆羅門之子
加爾各答的活劇
麻褐色的比哈爾
驟變
兵拜上等
人物列傳
帳篷
小愛人
麥利亞星
假日和脫衣舞
菩提伽雅
博幹男中尉
牛肉
利都
野人
婚俗及其他
太帕卡
丁高沙坎
沙杜渣
特殊任務
突襲密支那
四個「F」
米契爾砲長
火箭‧火車‧象
瑪愛耶
蜈蚣醬
報銷
私酒商
獵牛記
八莫之春
十板屁股
煉金術
薩漢民
公路和油管
發洋財
紅寶石
死亡的約會
凱旋歸國
總序 無擾為靜,單純最美/宋政坤
前記
偶然的決定
巫家霸機場
喜馬拉雅山
丁江
秀才造反
開明專制
婆羅門之子
加爾各答的活劇
麻褐色的比哈爾
驟變
兵拜上等
人物列傳
帳篷
小愛人
麥利亞星
假日和脫衣舞
菩提伽雅
博幹男中尉
牛肉
利都
野人
婚俗及其他
太帕卡
丁高沙坎
沙杜渣
特殊任務
突襲密支那
四個「F」
米契爾砲長
火箭‧火車‧象
瑪愛耶
蜈蚣醬
報銷
私酒商
獵牛記
八莫之春
十板屁股
煉金術
薩漢民
公路和油管
發洋財
紅寶石
死亡的約會
凱旋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