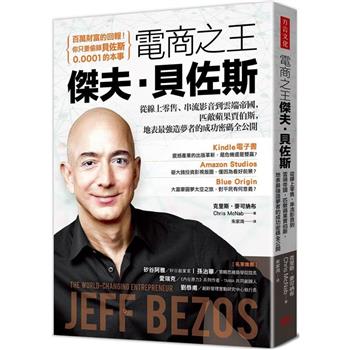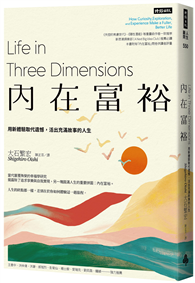本集收錄民國時期美術史料考證文章,共計十八篇,近十五萬字,附插圖七十五幅。內容涉及鄭振鐸、徐悲鴻、常任俠、滕固、王青芳、王子雲、衛天霖、于非闇等人,大都是以往鮮為人知或知之不詳、流傳有誤之人事,依據原始和參考材料,力圖還原歷史的真實,辨析和發掘被人們誤解和遺忘的史實,為研究者從事與之相關的人物個案之研究,為民國現代美術史留下一份接近真實的史料。自然談不到是“重新發現”,因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有待重新發現的,只是人們是否心存“有意與無意遮蔽”和“主動與被動遺忘”的主觀態度而已。
本書特色
●「帥府園」即為「中國藝術大師的殿堂」。
●內有圖片與豐富的史料,是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珍貴書籍。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難忘帥府園: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的圖書 |
 |
難忘帥府園──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5-06-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92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8 |
社會人文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藝術總論 |
$ 315 |
藝術史 |
$ 315 |
藝術設計 |
$ 315 |
美術 |
電子書 |
$ 350 |
藝術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難忘帥府園: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沈寧
筆名沈平子,中國北京人。供職圖書館。對民國時期文化教育、藝術社團及人物史料多有鉤稽,整理出版《滕固藝術文集》、《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閒話徐悲鴻》等圖書二十餘種,撰寫發表研究文章近百篇。
沈寧
筆名沈平子,中國北京人。供職圖書館。對民國時期文化教育、藝術社團及人物史料多有鉤稽,整理出版《滕固藝術文集》、《遺忘的存在:滕固文存》、《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閒話徐悲鴻》等圖書二十餘種,撰寫發表研究文章近百篇。
目錄
鄭振鐸對中國美術史研究的貢獻
滕固和他的中國美術史論著
從傅雷和滕固的一次爭吵說起
「傅汝霖」非傅雷筆名辨析
王子雲未協助朗多斯基創作孫中山塑像
衛天霖1930年北平畫展史料補遺
徐悲鴻的1931年冀魯之行
美術家王青芳生辰之謎
于非闇畫展史料鉤稽及相關美術家史料辨析
《流民圖》的故事在延續……
讀富家珍學籍檔案
離群孤雁王寶康
難忘帥府園:國立北平藝專遷校紀略
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史料鉤沉
蘇州美專旅平畫展的插曲
中國藝術史學會: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學術研究團體
故都新枝話藝文:民國時期北京(平)舉辦美術活動場所之一
青年會所留美名:民國時期北京(平)舉辦美術活動場所之二
編後瑣語
滕固和他的中國美術史論著
從傅雷和滕固的一次爭吵說起
「傅汝霖」非傅雷筆名辨析
王子雲未協助朗多斯基創作孫中山塑像
衛天霖1930年北平畫展史料補遺
徐悲鴻的1931年冀魯之行
美術家王青芳生辰之謎
于非闇畫展史料鉤稽及相關美術家史料辨析
《流民圖》的故事在延續……
讀富家珍學籍檔案
離群孤雁王寶康
難忘帥府園:國立北平藝專遷校紀略
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史料鉤沉
蘇州美專旅平畫展的插曲
中國藝術史學會: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學術研究團體
故都新枝話藝文:民國時期北京(平)舉辦美術活動場所之一
青年會所留美名:民國時期北京(平)舉辦美術活動場所之二
編後瑣語
序
編後瑣語
1979年秋,我以偶然的機會踏入中央美術學院從事圖書館工作,從此開始了人生一條坎坷艱辛之路。原因很簡單,我所成長的年代是各種政治運動頻發期,突出表現為:蔑視傳統文化教育,灌輸「新」的歷史觀,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逐漸升級,進而開展慘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致使人性扭曲,上演了無數家破人亡的歷史悲劇,也造成了一代人的學業荒置,知識匱乏。浩劫過後,百廢待興,新形勢下如從未接受過系統正規專業教育之我輩,又要面對惟學歷是瞻的用人制度,從事一份傳送知識、服務教學和研究的職業,不啻是種人生的殘酷挑戰。
很慶幸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踉蹌前行中遇到了許多師長友朋的關愛和鼓勵,其中最是難忘詩人、東方藝術史學家常任俠先生。先生以「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為座右銘,待人誠懇,和藹可親,學識淵博,著述豐盛。他當時還擔任著館長的職務,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猶能偶爾來館進行業務講座、參加聯歡活動,給我以初步的對於圖書館學的啟蒙知識。日後由於工作的關係,使我有機會經常前往位於西總布胡同五十一號先生寓所當面聆聽教誨,得到不少有關館史知識和文化藝術界趣聞軼事,開啟了我業餘從事對民國時期文化教育、藝術社團及人物史料的探究。
從最初的藏書大家、文化學者鄭振鐸入手,轉向美術名家、前任院長徐悲鴻,又盡心常任俠先生遺作整理,旁及了美術史學家滕固、民國西畫收藏第一人孫佩蒼,故都「藝壇交際花」王青芳,工筆畫大家于非闇,以及同時代藝術教育機構、社團、美術活動、文學藝術家等等史料的挖掘整理,這些看似孤立的個案研究,置身於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中,都有其內在的關聯性,通過點與線的鏈接後逐漸形成系統。面對歷史與現實經常發生錯位的現象,我大多採取著最笨拙的手段對研究的人物與事件,從系年做起,盡量做到收集資料竭澤而漁,使用材料去粗取精,採用最接近原始的一手材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加以認真辨析,形成自己的觀點。胡適先生「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治學態度給我一定的影響,「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故我們若非有十分證據,決不可輕下刑事罪名的判斷。」(致劉修業函)用事實說話也成為我寫作中側重展示史料,避免空談理論的堅守,這種略帶考據性質的文字,儘管讀來有些枯燥無味,沒有更多的故事性趣味和時空穿越的肆意飛揚,但於呈現歷史原貌或許能走得更近一些。
我原來居住的東城祿米倉胡同寓所是第二代面人湯舊居,相鄰的小雅寶胡同內有故宮博物館馬衡院長的故居;東側的大雅寶胡同是美院的職工宿舍,李苦禪、張仃、黃永玉諸位都在此生活多年,張朗朗的《大雅寶舊事》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南面的北總布胡同就是抗戰期間北京藝專校址,散落四周的東裱褙胡同、東受祿街曾經時徐悲鴻來京后的舊居;五老胡同、洋溢胡同、煤渣胡同等也曾有藝專和美院的宿舍,積聚著一批享譽中外的美術家;拆而復原的蔡元培故居位於東堂子胡同,這條元代就有的胡同內也是文學家沈從文、文博專家史樹青居住過的地方;南側不遠處的西總布胡同51號美院宿舍內居住著常任俠、艾中信、王琦諸位,誕生過不少藝術史論和繪畫作品;北側的西石槽胡同內是當年鄭振鐸在京求學時的暫住地;史家胡同內有前教育總長章士釗的舊址;朝陽門內南小街北側的芳嘉園胡同內,有被稱為「奇士」的王世襄和藝苑佳儷黃苗子夫婦的身影;竹竿胡同是早年蔣兆和開辦畫室之所;中山公園、太廟內檔期無間的畫展、米市大街北京青年會所內畫家的身影、東華門孔德學校內的萬板樓、升平署藝文中學舉辦的版畫展覽、京畿道北京美術學校的開學典禮……每當騎車上班或辦事穿梭於這些街巷胡同中,都會引發出無盡的聯想。如今,面對這些文化機構、文化人的歷史遺跡和旅痕的日益消逝,生活工作在京城鐘鼓樓下一介子民,懷舊的感覺越發濃烈:當年徐悲鴻先生手植的白皮松和書寫的校名匾額、曾經的德鄰堂中教師員工聯歡會上的文娛節目、陳列館內異彩紛呈的美術展覽、講授美術史課程的42教室、1995年夏季起運書箱的第一輛軍車……,這些往事有誰還曾記憶?曾經服務於這所藝術殿堂中二十餘年的我,自感有義務用文字記錄下當年的這些人與事,為後來者及研究者留下些許有助參考之文字,這完全是出於對文字的敬畏感,懷抱「書比人長壽」(當然是有價值的書)之信念,即為選編此書之初衷。
本集收錄民國時期美術史料考證文章十八篇,內容涉及鄭振鐸、徐悲鴻、常任俠、滕固、王青芳、王子雲、衛天霖、于非闇等人,以及美術院校歷史、美術活動及場所的介紹,大都是以往鮮為人知或知之不詳、流傳有誤之人事,依據原始和參考材料,力圖還原歷史的真實,辨析和發掘被人們誤解和遺忘的史料,為研究者從事與之相關的人物個案之研究,為民國現代美術史留下一份接近真實的文字。自然談不到是「重新發現」,因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有待重新發現的,只是人們是否心存「有意與無意遮蔽」和「主動與被動遺忘」的主觀態度而已。
我始終堅持說這些年寫出的文字不是學術論文,只能算是略帶學術研究性質的史料整理札記而已。鑒於新的材料不斷出現,在編輯本冊時,對以往發表過的文字又作了審慎的修訂,意在盡量減少由於自身學識淺陋在寫作中出現認識偏差和引用史料的失誤,以致造成不良影響。不久前,陳丹青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有關孫佩蒼為北平研究院代為搜集歐洲油畫的考略文字後,點評為寫得「周正」,并以算「是個做事情的人」相許,令我汗顏,權當做為一種鞭策吧。文章質量如何要由別人去評說,但這些粗淺的文字確是用心去寫的,聊以欣慰。
多年來心靈間的自我救贖和選擇的自我放逐之路,有了這本小冊子的問世,誠懇企盼讀者的不吝指正,藉此感謝眾多關心和幫助過我的師長友朋,感謝家人多年來忍受我埋頭故紙堆中拾荒自娛的行為,更要感謝秀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們對拙著選題、編輯、出版過程中給予的熱情幫助。
僅以此書的出版紀念常任俠先生誕辰百十週年。
沈寧 甲午中秋節前夕於京城殘墨齋
1979年秋,我以偶然的機會踏入中央美術學院從事圖書館工作,從此開始了人生一條坎坷艱辛之路。原因很簡單,我所成長的年代是各種政治運動頻發期,突出表現為:蔑視傳統文化教育,灌輸「新」的歷史觀,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逐漸升級,進而開展慘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致使人性扭曲,上演了無數家破人亡的歷史悲劇,也造成了一代人的學業荒置,知識匱乏。浩劫過後,百廢待興,新形勢下如從未接受過系統正規專業教育之我輩,又要面對惟學歷是瞻的用人制度,從事一份傳送知識、服務教學和研究的職業,不啻是種人生的殘酷挑戰。
很慶幸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踉蹌前行中遇到了許多師長友朋的關愛和鼓勵,其中最是難忘詩人、東方藝術史學家常任俠先生。先生以「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為座右銘,待人誠懇,和藹可親,學識淵博,著述豐盛。他當時還擔任著館長的職務,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猶能偶爾來館進行業務講座、參加聯歡活動,給我以初步的對於圖書館學的啟蒙知識。日後由於工作的關係,使我有機會經常前往位於西總布胡同五十一號先生寓所當面聆聽教誨,得到不少有關館史知識和文化藝術界趣聞軼事,開啟了我業餘從事對民國時期文化教育、藝術社團及人物史料的探究。
從最初的藏書大家、文化學者鄭振鐸入手,轉向美術名家、前任院長徐悲鴻,又盡心常任俠先生遺作整理,旁及了美術史學家滕固、民國西畫收藏第一人孫佩蒼,故都「藝壇交際花」王青芳,工筆畫大家于非闇,以及同時代藝術教育機構、社團、美術活動、文學藝術家等等史料的挖掘整理,這些看似孤立的個案研究,置身於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中,都有其內在的關聯性,通過點與線的鏈接後逐漸形成系統。面對歷史與現實經常發生錯位的現象,我大多採取著最笨拙的手段對研究的人物與事件,從系年做起,盡量做到收集資料竭澤而漁,使用材料去粗取精,採用最接近原始的一手材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加以認真辨析,形成自己的觀點。胡適先生「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治學態度給我一定的影響,「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故我們若非有十分證據,決不可輕下刑事罪名的判斷。」(致劉修業函)用事實說話也成為我寫作中側重展示史料,避免空談理論的堅守,這種略帶考據性質的文字,儘管讀來有些枯燥無味,沒有更多的故事性趣味和時空穿越的肆意飛揚,但於呈現歷史原貌或許能走得更近一些。
我原來居住的東城祿米倉胡同寓所是第二代面人湯舊居,相鄰的小雅寶胡同內有故宮博物館馬衡院長的故居;東側的大雅寶胡同是美院的職工宿舍,李苦禪、張仃、黃永玉諸位都在此生活多年,張朗朗的《大雅寶舊事》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南面的北總布胡同就是抗戰期間北京藝專校址,散落四周的東裱褙胡同、東受祿街曾經時徐悲鴻來京后的舊居;五老胡同、洋溢胡同、煤渣胡同等也曾有藝專和美院的宿舍,積聚著一批享譽中外的美術家;拆而復原的蔡元培故居位於東堂子胡同,這條元代就有的胡同內也是文學家沈從文、文博專家史樹青居住過的地方;南側不遠處的西總布胡同51號美院宿舍內居住著常任俠、艾中信、王琦諸位,誕生過不少藝術史論和繪畫作品;北側的西石槽胡同內是當年鄭振鐸在京求學時的暫住地;史家胡同內有前教育總長章士釗的舊址;朝陽門內南小街北側的芳嘉園胡同內,有被稱為「奇士」的王世襄和藝苑佳儷黃苗子夫婦的身影;竹竿胡同是早年蔣兆和開辦畫室之所;中山公園、太廟內檔期無間的畫展、米市大街北京青年會所內畫家的身影、東華門孔德學校內的萬板樓、升平署藝文中學舉辦的版畫展覽、京畿道北京美術學校的開學典禮……每當騎車上班或辦事穿梭於這些街巷胡同中,都會引發出無盡的聯想。如今,面對這些文化機構、文化人的歷史遺跡和旅痕的日益消逝,生活工作在京城鐘鼓樓下一介子民,懷舊的感覺越發濃烈:當年徐悲鴻先生手植的白皮松和書寫的校名匾額、曾經的德鄰堂中教師員工聯歡會上的文娛節目、陳列館內異彩紛呈的美術展覽、講授美術史課程的42教室、1995年夏季起運書箱的第一輛軍車……,這些往事有誰還曾記憶?曾經服務於這所藝術殿堂中二十餘年的我,自感有義務用文字記錄下當年的這些人與事,為後來者及研究者留下些許有助參考之文字,這完全是出於對文字的敬畏感,懷抱「書比人長壽」(當然是有價值的書)之信念,即為選編此書之初衷。
本集收錄民國時期美術史料考證文章十八篇,內容涉及鄭振鐸、徐悲鴻、常任俠、滕固、王青芳、王子雲、衛天霖、于非闇等人,以及美術院校歷史、美術活動及場所的介紹,大都是以往鮮為人知或知之不詳、流傳有誤之人事,依據原始和參考材料,力圖還原歷史的真實,辨析和發掘被人們誤解和遺忘的史料,為研究者從事與之相關的人物個案之研究,為民國現代美術史留下一份接近真實的文字。自然談不到是「重新發現」,因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有待重新發現的,只是人們是否心存「有意與無意遮蔽」和「主動與被動遺忘」的主觀態度而已。
我始終堅持說這些年寫出的文字不是學術論文,只能算是略帶學術研究性質的史料整理札記而已。鑒於新的材料不斷出現,在編輯本冊時,對以往發表過的文字又作了審慎的修訂,意在盡量減少由於自身學識淺陋在寫作中出現認識偏差和引用史料的失誤,以致造成不良影響。不久前,陳丹青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有關孫佩蒼為北平研究院代為搜集歐洲油畫的考略文字後,點評為寫得「周正」,并以算「是個做事情的人」相許,令我汗顏,權當做為一種鞭策吧。文章質量如何要由別人去評說,但這些粗淺的文字確是用心去寫的,聊以欣慰。
多年來心靈間的自我救贖和選擇的自我放逐之路,有了這本小冊子的問世,誠懇企盼讀者的不吝指正,藉此感謝眾多關心和幫助過我的師長友朋,感謝家人多年來忍受我埋頭故紙堆中拾荒自娛的行為,更要感謝秀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們對拙著選題、編輯、出版過程中給予的熱情幫助。
僅以此書的出版紀念常任俠先生誕辰百十週年。
沈寧 甲午中秋節前夕於京城殘墨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