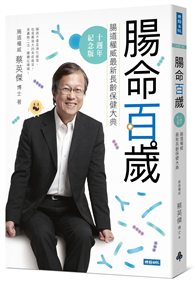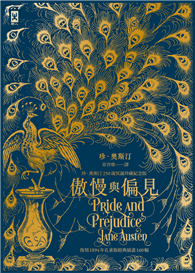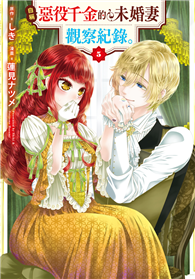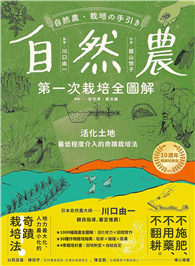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孔丘‧出道‧顯其暴】
孔丘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地位獨特而又複雜。他是什麼我們先不論,僅僅後世拿他所做的文章,簡直不計其數。附在他老人家身上的公案也出奇之極,比如文革的林彪事件,你批林彪就批唄,愣把孔丘也捎帶上。以致讓當時的儒學大師梁漱溟受盡精神上的折磨,也因此給自己引來政治災難。當年他就開宗明義地說:「批林可以,批孔我不幹,因為我實在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你說,梁漱溟說這話,他能好得了嗎?
還有歷朝歷代的政權,一看人民的心思有點活泛,就趕緊把孔丘搬出來(謂之「敲門磚」),大搞尊孔祭孔,以此鉗制人民的思想。這些政客中,一肚子壞水的有之,道貌岸然的亦有之,總之好東西不多。把孔丘當作教育家,單純尊之祭之,也許沒什麼,但尊孔祭孔,一旦出自黨派或政權的策劃,百分之八九十沒有好事,或著乾脆說就是愚弄人民。孔丘有這麼厲害嗎?當然有,他有一切專制主義的權力意識,更有助紂為虐的幫兇理論。
前五○○年,魯國國君姬宋跟齊國國君姜杵臼在山東新泰(時稱夾谷)舉行峰會,這樣的峰會在當時的封國間非常流行,就跟當今頻繁的國際峰會是一樣的。在這次峰會上,孔丘被任命為姬宋的賓相,負責禮儀事宜。孔丘平生多不得意,好不容易被國君看中一回,機遇難得,於是決定,挽挽袖子,賣賣力氣。這也是常人心態,有戲臺給他,不好好表現,誰都對不住。結果,孔丘腦門一熱,把事做過了頭。
事情是這樣的,根據慣例,峰會期間,都有文藝演出(這如同每年春天的北京「兩會」,都有文藝演出,慰問代表與委員)。當齊國代表隊演出原生態的土風舞時,孔丘根據儒學理論,指斥土風舞的不當,認為在兩國峰會這樣的重大場合,應該表演莊重的宮廷舞。孔丘據此得出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土風舞侮辱了峰會領導人。隨即,孔丘命魯國衛士,把那些跳土風舞的男女演員趕下臺,並殘忍的砍斷他們的手足!
這在當今怎麼可以想像呢?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澳洲時,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電視鏡頭,東道主往往會安排當地的土風舞,以示特別的禮遇和熱忱的歡迎。那些土著演員,多以半裸,呈現在客人面前。按照孔丘「平民輕視國君」的戒規尺度,得有多少土風舞演員被斬斷手腳呀。難以置信的是,孔丘的過度使用暴力,不僅沒有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相反,還在四年後(前四九六年),使他的祖墳上冒起了青煙,即他被國君姬宋拔擢為代理宰相(攝相事)。
或許這一任命,鼓勵了孔丘,他到職第七天,便拿少正卯開刀,祭他內心那把私怨小旗。把少正卯殺了就殺了吧,他還曝屍三日,可見孔丘之狠。孔丘與少正卯何怨之有?在魯國,少正卯與孔丘齊名,且開辦私立學校,與孔丘爭奪學生。國家領導人不允許大臣與他爭奪人民群眾(蕭何求媚人民,不就被劉邦下獄了嗎),孔丘同樣不允許別人與他爭奪學生,這都是競爭起的禍。但孔丘畢竟不同,他是文化名人,又是為人之師,不能公報私仇,更不能無緣無故的殺人。所以,他的學生自貢就問老師,為什麼要殺少正卯。孔丘給出的理由竟然是:少正卯系小人之桀雄!並歷數其五大罪狀,原話即「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白話即:
一、居心叵測,迎奉人意;二、行為邪惡,不受勸告;三、口是心非,琢磨不定;四、強記博學,所知皆謬;五、文過飾非,自卸責任。
孔丘所指,無一實證。即便上述莫須有的罪名成立,孔丘的司法手段,也完全弄顛倒了,即採取倒走模式,也就是先殺人,再宣布其罪名。這為後世陰謀家們以及惡意執法者,標立了極其惡劣的範本。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些司法系統照樣是先羈押人,後搜羅證據。
也正因為有了孔丘這麼一位奇人,位於泰山腳下、其小如豆的魯國,才在中國歷史上,成為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封國。當然,這也取決於魯國本身的歷史特點。魯國是姬伯禽的封國,其父姬旦乃周朝文物制度的首創者。因此,魯國所收藏的圖書和文獻,為所有封國之最,其貴族階層的文化水準,也普遍高於其他封國貴族階層。尤其前八世紀,周朝首都西安(時稱鎬京)被犬戎部落所攻陷,圖書文獻盡毀於戰火之中,而魯國的圖書文獻,卻完好無損。魯國首府―山東曲阜,遂成為當世惟一的文化大都市。再加上魯國從沒有遭受過劫掠焚燒的惡運,對周王朝初期的文物制度,保持的也最完整。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古希臘那樣的大環境下,產生了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在魯國這樣的大背景下,卻必然產生孔丘這樣的教育家;蘇格拉底一條道跑到黑,孔丘卻顯得複雜多變。我們常說的「人文環境」這個詞,即可以用於古希臘對蘇格拉底,魯國對孔丘。
魯國確實是偉大的,它給後世留下一個人―孔丘,留下一套完整的《周禮》;孔丘又給我們留下「五經」,即《易經》、《春秋》、《詩經》、《書經》、《禮經》。還是那句話,先不論孔丘刪減編纂的這「五經」價值如何,至少以孔丘為座標的春秋政治、思想、文化,其影響至今不衰。貢獻有之,破壞有之。這就是事物的兩面性,陰陽共存。
------
【卑儒‧犬儒‧成大儒】
儒家一直不怎麼得志,他們見縫插針,一旦發現天下大亂,四分五裂,便開始懷揣治國夢想,去投奔新興國家。然而,所到之處,幾乎是處處碰壁。你不得不佩服儒家學者,這些人好比飄搖於沙漠中的零星野草,看似枯的,其實卻有著極強的生命力,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箭一般射出,也完全不在乎結果如何。或許是失敗再失敗造就了他們的這一堅韌不拔的性格。
周朝的時候,儒家小有風光,一直到嬴政時代,他們也還念念不忘重振儒學。嬴政平定六國,實現統一,儒家發現嬴政喜歡人家給他歌功頌德,於是就策應過去,拿「統一中國的領導人」這樣華麗的詞藻,去狠拍他的馬屁,結果真就把這位帝制始祖給拍舒服了。儒家以為翻身的機會來了,不料嬴政的臉一變,倒來了個焚書坑儒。
這一來,儒家就更加認識到復古的重要性了,因此都盼著嬴政早死。在一定時期內,儒家的想法,幾乎代表了整個秦帝國社會的心聲。嬴政大帝一死,陳勝吳廣一起事,結果一呼百應,整個帝國全亂套了。儒家就盼這個,所有被壓制的人群,尤其是高知群體,也都盼這個,改朝換代總會帶來新的機遇,正如一棵老樹之死孕育無數新生命一樣。帝國一亂,儒家便開始四處活動。最初是孔子的後裔孔甲,他和一些儒家學者,一聽說陳勝吳廣起事了,還不等形勢明朗,也不知人家是否會聘用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投靠去了。最後陳勝吳廣自身都難保,還會收留什麼儒家學者嗎?
在儒家學者眼裡,能者為哥。其中有這麼一個儒家分支看好劉邦,二話沒說就投奔而去。按說,儒家那一套理論是排斥與流氓同道的,可是為了儒家的發展,也就難顧廉恥,於是就有了儒家與流氓共簷的奇觀。當然,一開始的時候,劉邦還比較排斥儒家,人家好心投奔他,給他當狗使,他卻抓過一頂儒生的帽子,往裡撒尿。那儒生也真夠可以的,劉邦如此侮辱他,他竟然一點氣都沒有,依舊忍著,別的儒生也依舊忍著。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原來是一句裝門面的話。而且,這一回不是儒家排斥流氓,而是流氓排斥了儒家。
嬴政死後,儒家再次尋覓到新的機會,他們從地上一躍而起,四處投奔那些叛軍首領。投到劉邦腳下的儒家分支,雖不被尊重,畢竟劉邦收留了他們,這已經夠讓那些儒家學人感激涕零的了。試想,當年除了孔子有過這等榮幸外,誰還有過?燒高香吧!只要留下來,說不定就有機會。果然,劉邦完成統一大業。流氓終歸是流氓,他們打下江山,並組成以高級流氓為首的中央政府後,流氣不改。比如政府高官在皇宮內山吃海喝時,醉了或淫聲蕩調,或拔劍比武,以此取樂。劉邦是流氓出身不假,但他也絕不是白癡,他知道皇宮內亂糟糟的局面,很容易被不軌者所利用,是以愁眉不展。皇上的心思,被儒家學者叔孫通看在眼裡,如此這般,媚了一通。劉邦樂道:「你設計的朝儀,若能解除這混亂的局面,朕便重重有賞。」
劉邦的欣然接受,實際就是為我所用。叔孫通果真能搞出個名堂,保大漢江山永不變色,何樂而不為?由此可見,儒學對極權統治者的重要性,亦可見儒學對民主自由的破壞性。難怪顧準對他的胞弟陳敏之說,你寫孔子的評傳,可以把他小醜化。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儒學的確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不說把孔子小醜化,至少也應該力加批判。
閒話少說。下面來說說叔孫通在前二○○年給劉邦搞的那個朝儀,這裡用幾個分鏡頭來說明:
(一)文武百官在宮廷官員的引導下,依序入殿,分班兩廂就座;文官居左,武官居右。那座兒,不過大臣自己跪著的雙腿。禁衛軍官,則站在文武百官身後。
(二)劉邦坐著人拉的輦車,適時緩緩而現。每隔幾米,便有一位官員高聲傳報:「皇帝駕到!」一路遞進,待劉邦入殿方畢。
(三)劉邦落座,大殿肅穆。見昔日一塊打天下的哥們,個個臣服在地,劉邦那個舒坦。
(四)宮廷官引導文武百官,依序職務大小,向劉邦敬獻頌詞。那些程式化的辭藻,不外乎偉大、英明、正確之類。
(五)國宴始,大臣伏地,仰望主上,以示低賤。席間,大臣依序向劉邦敬酒,如是九次。
(六)國宴畢,司儀大聲宣布:「宴會禮成。」監察官(御史)進入文武百官隊伍,猶如老師檢查學生指甲頭髮之類,檢查百官的舉止,把失儀者一一趕出殿外,登入監督薄,為日後懲戒備案。失儀者或被彈劾,或被罰款(萬曆年間的御史,甚至參劾朝儀過程中咳嗽和步履不穩的官員)。從此,國宴之上,秩序井然。
朝儀後,劉邦大喜,隨即提升叔孫通為祭祀部長(奉常),賞黃金五百斤,門徒亦一一升官發財。打這兒,叔孫通成為門徒眼裡的聖人;打這兒,皇帝與大臣拉開距離;打這兒,儒家的聲望冉冉升起;打這兒,獨裁專制走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很難找出和叔孫通的設計近似但結果卻正相反的例子來,找來找去,以為只有湯瑪斯‧傑弗遜(他曾代表新生的美國和英國在巴黎簽訂獨立條約)為華盛頓設計的退職儀式相對接近,即二者都有為早期政府做行為設計的「共性」。
言歸正傳。劉邦死後的儒家,又經歷過一段曲折。劉恒繼位後,他的妻子竇猗房皇后信奉道家學說,實行清靜無為的國策,也就是老子的那套無為就是有為的混帳學說。劉恒(文帝)死,其子劉啟(景帝)繼位,竇太后參與國政,繼續信奉道家學說。如此,儒家便被排斥四十年之久,但也正是這一時期,創造了中國史上的一段輝煌:糧倉盈滿錢成堆,穀多腐爛錢生黴。這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如此說來,老子的無為理論,不就被西漢輝煌的經濟驗證了嗎?
總之,竇太后喜道厭儒,也就聽不進對道家不同的言論。有一次,儒家博士轅固生對道家人物李耳(老子)、莊周略有非議,竇太后就懲罰他到圈舍裡去,赤手空拳鬥野豬。這活兒若是給施瓦辛格(Schwarzenegger)去幹,小菜一碟,給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去幹,還不成了野豬戲人。幸虧當時的皇帝劉啟暗中悄悄塞給轅固生一把刀,才算沒把老命送掉。前一三五年,竇太后一命嗚呼,儒學才算重新回到軌道上來,而且來勢洶洶。董仲舒見儒學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已基本確立,便在他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為異端,為歪理邪說。他提出,立儒學為一尊,其外的書籍,一律禁絕。
儒家學者、身為當朝宰相的衛綰,把董仲舒列為全國統考第一名,董仲舒的意見也很快被漢武帝劉徹所採納,並將儒學定於一尊。從此,諸子百家只剩一家,一家中只剩《五經》。這影響,就是今天的中國學子乃至普通的中國人,心靈深處,也都深深地打著儒家文化的烙印。當代人常說的「亞洲價值觀」,多半也都來自儒家文化的影響。卑儒犬儒都「世界觀」了,這玩笑也未免太過了。
------
【女皇‧女患‧武則天】
李世民死後,悄然之中,向我們走來一位絕代佳麗,那就是武則天。她原本是李世民的姬妾,為什麼要等到自己的丈夫死後,才走進人們的視野呢?這就是機緣問題了。後宮女人,成千上萬,哪能就輕易出人頭地呢?唐初,皇宮姬妾有十九級之多(每級多人),而武則天僅排位第十六級,才人而已。
六四九年,李世民去世時,武則天已二十六歲。按舊朝慣例,皇帝死了,他的宮妃們都是要陪葬的。到了唐帝國,早已不復如此殘暴的陋習,改為已故皇帝的姬妾削髮為尼。就這樣,李世民死後,其姬妾宮妃,均被送往長安感業寺,以終天年。武則天在列。
六五四年的一天,李世民的繼任者李治,跟王皇后到感業寺禮佛,邂逅早年就令他垂涎三尺的武則天。武則天也彷彿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使盡渾身解術,把那成串的淚珠,灑給李治看。王皇后見了,不僅不吃醋,反而要當牽線人,成全李治與武則天的好事。何以至此?卻原來,王皇后是要利用武則天,去打壓她的情敵蕭淑妃。
感業寺一行,皇帝、皇后、武則天,形成三人共贏的局面。李治對王皇后,陡增好感。王皇后的算盤非常如意,她想:「我給皇帝弄來一個他垂涎已久的美人,在皇帝那裡,我贏得一分;由此打壓了蕭淑妃,那麼我在蕭淑妃那裡,也贏得一分;把武則天接回皇宮,安排在皇帝身邊。武妹妹必定對我感恩戴德,那麼她也就是我的人。因此,在武則天那裡,我又贏得一分。」這勝券在握的三分,把王皇后樂得連北都找不著了。然三十一歲的武則天進宮僅幾個月,便把二十七歲的青年皇帝李治給搞定了。轉年,也就是六五五年,武則天親手掐死新生的女兒,栽贓王皇后與蕭淑妃。冤獄判決的結果是:王皇后、蕭淑妃各打一百棍,然後砍斷她們的手足,再投至酒缸,令她們在無限的痛苦中,結束生命。則那武則天,一舉奪得皇后寶冠。武則天掃平內宮,遂向龍椅奔襲。好個生猛的女人!
武則天與其生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黃仁宇先生也才在他的書中,把「女患」與「外戚政治」的字眼,加諸於她。言之大意就是,唐帝國的天下,只能老李家的人來統治,換成皇帝的老婆、皇帝的舅子來掌權、分權、主權,彷彿那就不是中國人了,因而也就「外」起來。尤其「女患」二字,相當不雅,帶著一種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
中國自帝制以來,歷朝歷代,有幾多皇帝不是暴徒?暴徒皇帝,哪個不殺人如麻?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回頭去翻翻「漢尾」各節,在那近四百年的時間裡,充滿了皇族之間的相互屠殺。他們動輒把同胞骨肉,當街像殺豬那樣,老老小小的屠宰個一乾二淨。彼此屠殺完了,又開始國與國之間的屠殺。這些難道不是患嗎?這些患,百分之九十九全是男人們幹的,以黃仁宇的觀點,這些該叫「男患」才是,為什麼不提出來,到武則天這裡就突兀的造出一個「女患」來呢?
我並非為武則天辯護,意在說,專制集團亦即暴政集團,在殘暴的手段上,那是無論男女的。只要他/她掌了權,他/她必定由人變成畜牲。是專制、是暴政這一制度把人變成那樣的,是專制、是暴政這一制度,讓權力變成殺人機器的。因此,不能把專制暴政集團裡的某個男人或某個女人單獨拿出來,評其長短。這樣,後世讀者真的以為,是女人誤國了,而男人卻不必承擔這樣的歷史罪責。
閒話少敘,咱們接著說武則天奔襲龍椅的事。李治身體不怎麼好,許多國事,便交由武則天代理。這段時期的唐帝國,為夫婦共治。待李治一死,武則天便把幾個皇位繼承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六九○年,武則天不再玩弄兒皇帝們,自己登上皇帝大位,稱自己的帝國為周王朝。這一年,她已是六十七歲。李家親王不能接受,便舉旗造反,結果被武則天一一誅殺。……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都是孔子惹的禍?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5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Others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中國歷史 |
$ 315 |
中國歷史 |
$ 315 |
社會人文 |
$ 315 |
歷史 |
電子書 |
$ 35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都是孔子惹的禍?
中國帝王勝利組SOP:
打江山時殘暴,打下江山後專制;坐穩江山後橫徵暴斂+腐敗!
尊孔祭孔一旦出自黨派或政權的策劃,十之八九沒有好事,或者乾脆說就是愚弄人民。
歷來統治集團重用儒家,是因為儒家學說有助於鞏固政權,他有一切專制主義的權力意識!
1.《大宋帝國亡國錄》《漢室江山興衰史》《慈禧與她的帝國》暢銷作者魏得勝首部中國史通論,澈底反思儒家思想、奴役制度與專制政權。
2.本書曾榮登中國圖書暢銷榜,卻因太過熱賣,反遭封殺禁售!全新增訂版,一刀不剪,台灣犀利上市!(簡體版原名:歷史的點與線)
歷史才子魏得勝
繼《漢室江山興衰史》、《大宋帝國亡國錄》,全新刻劃中國歷史新風貌。
華人文化重視的儒學思想是專制主義的開端。
唐太宗的殘暴可比秦始皇,他與魏徵的君臣佳話都是假的;
大明帝國的建立與穩固靠的也是朱元璋和朱棣的大屠殺。
這世界上最容易建立的就是專制制度,靠暴力起家的人,也一定用各種暴力統治一個國家,這就是專制,這就是暴政。本書敘述中國歷史的點滴,揭示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生成與演進,既有小說之精彩筆法,亦有對史實的透澈剖析,揭開你未思考過的中國歷史。
作者簡介:
魏得勝
著有《大宋帝國亡國錄》、《慈禧與她的帝國》、《秦淮河》、《漢室江山興衰史》、《另類人生》、《風中的文化帝國》、《歷史深處話名著》等書。《漢室江山興衰史》入選第68梯次「好書大家讀」推薦。《雜文選刊》讀者評為「我最喜歡的五位雜文作家」之一。中國暢銷雜誌《讀者》的首批簽約作家。
TOP
章節試閱
【孔丘‧出道‧顯其暴】
孔丘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地位獨特而又複雜。他是什麼我們先不論,僅僅後世拿他所做的文章,簡直不計其數。附在他老人家身上的公案也出奇之極,比如文革的林彪事件,你批林彪就批唄,愣把孔丘也捎帶上。以致讓當時的儒學大師梁漱溟受盡精神上的折磨,也因此給自己引來政治災難。當年他就開宗明義地說:「批林可以,批孔我不幹,因為我實在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你說,梁漱溟說這話,他能好得了嗎?
還有歷朝歷代的政權,一看人民的心思有點活泛,就趕緊把孔丘搬出來(謂之「敲門磚」),大搞尊孔祭孔,以此...
孔丘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地位獨特而又複雜。他是什麼我們先不論,僅僅後世拿他所做的文章,簡直不計其數。附在他老人家身上的公案也出奇之極,比如文革的林彪事件,你批林彪就批唄,愣把孔丘也捎帶上。以致讓當時的儒學大師梁漱溟受盡精神上的折磨,也因此給自己引來政治災難。當年他就開宗明義地說:「批林可以,批孔我不幹,因為我實在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你說,梁漱溟說這話,他能好得了嗎?
還有歷朝歷代的政權,一看人民的心思有點活泛,就趕緊把孔丘搬出來(謂之「敲門磚」),大搞尊孔祭孔,以此...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時隔十年,《歷史的點與線》以《都是孔子惹的禍》為書名得以在臺灣再版,幸甚。作為單一體制下的作者,面對多元社會的臺灣,面對獨特而前瞻的讀者,很是誠惶誠恐,不知說什麼好。思之再三,惟有遵循內心,隨意就好。
記得初寫本書時,我常常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緒。有一天,我去郵政局取稿酬,走到半路,想到令我熱血沸騰的觀點,身上又沒帶筆,怕忘了那些一閃而過的思想火花,一度想折頭,回家去寫。本書,基本就是在這麼一個亢奮狀態下完成的。
《歷史的點與線》是我的第一本書,其好壞,不取決於我的亢奮,而取決於讀者的認可。這第一道...
記得初寫本書時,我常常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緒。有一天,我去郵政局取稿酬,走到半路,想到令我熱血沸騰的觀點,身上又沒帶筆,怕忘了那些一閃而過的思想火花,一度想折頭,回家去寫。本書,基本就是在這麼一個亢奮狀態下完成的。
《歷史的點與線》是我的第一本書,其好壞,不取決於我的亢奮,而取決於讀者的認可。這第一道...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混沌篇】
神話‧傳說‧煮一鍋
三皇‧五氏‧石頭記
黃帝‧黃龍‧升天龍
【周朝篇】
美女‧亡國‧誰興邦
土屋‧土院‧土皇宮
春秋‧爭霸‧看城邦(上)
春秋‧爭霸‧看城邦(下)
孔丘‧出道‧顯其暴
諸子‧百家‧數墨家(上)
諸子‧百家‧數墨家(下)
國事‧安危‧繫一身
刺客‧政客‧全是禍
【秦朝篇】
猛蟲‧吸血‧韓非子
葡萄‧美酒‧夜光妞
官制‧人治‧極權制
焚書‧坑儒‧不死藥
馬派‧鹿派‧真假派
霸王‧別姬‧劉邦起
【漢朝篇】
卑儒‧犬儒‧成大儒
木犁‧鐵犁‧曇花裡
桃花‧不就‧胭脂失
竹子‧布匹‧枸杞醬
沉滓‧泛起‧漢武帝
一...
【混沌篇】
神話‧傳說‧煮一鍋
三皇‧五氏‧石頭記
黃帝‧黃龍‧升天龍
【周朝篇】
美女‧亡國‧誰興邦
土屋‧土院‧土皇宮
春秋‧爭霸‧看城邦(上)
春秋‧爭霸‧看城邦(下)
孔丘‧出道‧顯其暴
諸子‧百家‧數墨家(上)
諸子‧百家‧數墨家(下)
國事‧安危‧繫一身
刺客‧政客‧全是禍
【秦朝篇】
猛蟲‧吸血‧韓非子
葡萄‧美酒‧夜光妞
官制‧人治‧極權制
焚書‧坑儒‧不死藥
馬派‧鹿派‧真假派
霸王‧別姬‧劉邦起
【漢朝篇】
卑儒‧犬儒‧成大儒
木犁‧鐵犁‧曇花裡
桃花‧不就‧胭脂失
竹子‧布匹‧枸杞醬
沉滓‧泛起‧漢武帝
一...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魏得勝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6-05-10 ISBN/ISSN:978986571674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6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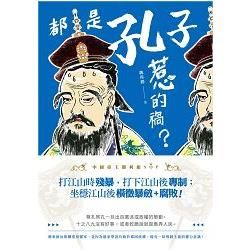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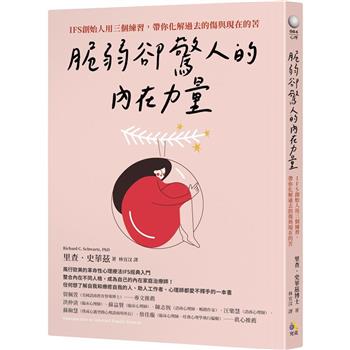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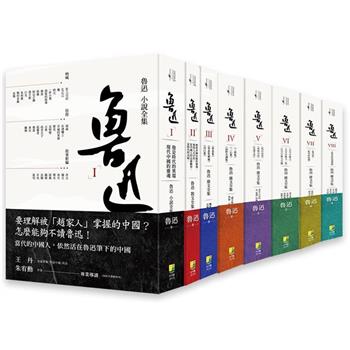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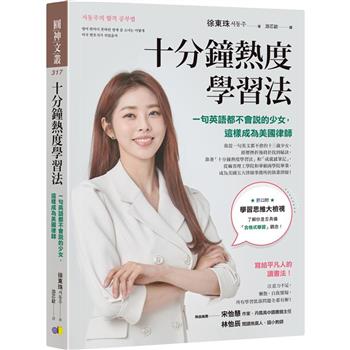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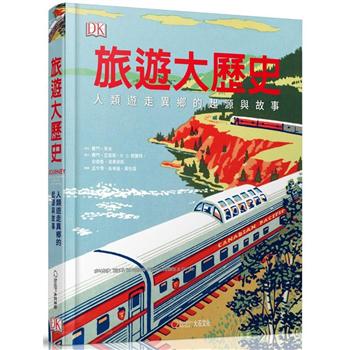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