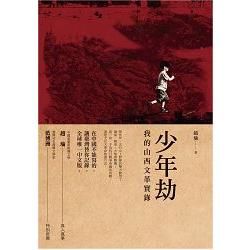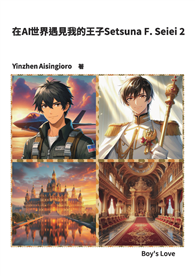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野火席捲全中國,本書作者趙瑜的故鄉晉東南專區(今山西省)亦不得倖免。在1966至1969這三年間,晉東南兩大派系間的鬥爭規模逐漸失控,為了要爭權,兩派人馬在山西展開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無產階級鬥爭;為了求生存,男女老幼的家園變成了無數你死我活的「武鬥」戰場。當年不到十五歲的趙瑜,也成了這場「大戰」中的一份子。他目睹了成千上萬的人們是如何在文革的鬥爭浪潮下,做出種種泯滅人性的瘋狂行徑,從互相批鬥到相視如寇讎的相殺相食……在失序的年代,鮮血浸染了太行山,也浸染了一整代人的少年時光。在事隔五十年後,難以忘卻這段慘痛經歷的趙瑜決定透過報導文學的形式,結合自己多年來對故鄉人事的採訪與考察,寫下這本使人讀來宛若身歷其境的《少年劫:我的山西文革實錄》。
本書特色
中國重量級報導文學家趙瑜────────深入直擊
全球唯一中文版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少年劫:我的山西文革實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5 |
中國歷史 |
$ 572 |
中文書 |
$ 572 |
中國歷史 |
$ 585 |
社會人文 |
$ 585 |
科學科普 |
電子書 |
$ 65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少年劫:我的山西文革實錄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瑜
1955年出生於山西上黨,原籍河北安平,中國報導文學作家。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曾任晉東南地區文聯秘書長。現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與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其主要作品有《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但悲不見九州同》、《強國夢》、《兵敗漢城》、《尋找巴金的黛莉》、《火車頭震盪》、《野人山淘金記》等三十餘部,其中《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被稱為「中國體育三部曲」。
趙瑜
1955年出生於山西上黨,原籍河北安平,中國報導文學作家。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曾任晉東南地區文聯秘書長。現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與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其主要作品有《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但悲不見九州同》、《強國夢》、《兵敗漢城》、《尋找巴金的黛莉》、《火車頭震盪》、《野人山淘金記》等三十餘部,其中《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被稱為「中國體育三部曲」。
目錄
自序
潛入兵營心跳急
革命的對象
小型造反的流產
見到真屍體
晉東南老幹部的抵抗
大奪權與大分裂
紅字號與聯字號
奪權三日即衝突
「三結合」的權力機構
聯字號頭頭出山錄
一段閒話與大碗吃麵
上千人的肉搏
長平之戰的血光
張炳臣慘死
神槍震鬧市
第一槍打響在長治北
兵工廠人馬參戰
王金紅的見證
戰爭傳統,精良武器
楊萬盛死裡逃生
劉格平上太行
強龍撲火急
紅字號大振聲威
風飄絮兮浪淘沙
把棺材抬上卡車
全城大逃亡
見證一場血戰
老母親絕境求生
老幹部夜潛糧倉
老婆婆的生與死
醫專激戰
聯字號營救常醫生
伏擊抓獲李順達
事件後果特別嚴重
兵發太行
飛機播撒十二道電令
先遣部隊受阻
趙震元和他的夥計們
總部防禦和特工隊
「二‧四慘案」始末
祕密試驗與專家之死
民兵集結人槍上萬
戰火在燃燒
山地公路上的激戰
修善村的屠殺
戰場上的戀人
刺刀下的談判
追悼亡靈與徐公達慘案
烈火焚樓小麥焦
家犬吃人肉
恍若隔世的戰後上黨
少年人的悲傷事
少年人的危險事
集中營酷刑撼太行
婦女的冤仇深
槍決趙震元
捕殺侯小根
刮颱風橫掃上萬生靈
晉城縣自殺者名單
反擊右傾翻案風
劃線切瓜獄滿為患
徐志有的逃亡生涯
後記:省思與懺悔
附錄一:是誰殺了王尚志
立場不同判斷兩異
失蹤當晚被揪鬥
黑暗的歷史怪圈
名探出馬
十五年後的結論
附錄二:血火四新礦
這裡只生產仇恨的烈焰
坦克車與地雷陣
重炮轟開文革路
老兵張永富和小鬼王訓
奪命突圍全軍覆沒
白森森的人骨架子
附錄三:五路進剿看屍橫
發射毒氣彈
高平中學生的戰地日記
高平兩派戰死名單
潛入兵營心跳急
革命的對象
小型造反的流產
見到真屍體
晉東南老幹部的抵抗
大奪權與大分裂
紅字號與聯字號
奪權三日即衝突
「三結合」的權力機構
聯字號頭頭出山錄
一段閒話與大碗吃麵
上千人的肉搏
長平之戰的血光
張炳臣慘死
神槍震鬧市
第一槍打響在長治北
兵工廠人馬參戰
王金紅的見證
戰爭傳統,精良武器
楊萬盛死裡逃生
劉格平上太行
強龍撲火急
紅字號大振聲威
風飄絮兮浪淘沙
把棺材抬上卡車
全城大逃亡
見證一場血戰
老母親絕境求生
老幹部夜潛糧倉
老婆婆的生與死
醫專激戰
聯字號營救常醫生
伏擊抓獲李順達
事件後果特別嚴重
兵發太行
飛機播撒十二道電令
先遣部隊受阻
趙震元和他的夥計們
總部防禦和特工隊
「二‧四慘案」始末
祕密試驗與專家之死
民兵集結人槍上萬
戰火在燃燒
山地公路上的激戰
修善村的屠殺
戰場上的戀人
刺刀下的談判
追悼亡靈與徐公達慘案
烈火焚樓小麥焦
家犬吃人肉
恍若隔世的戰後上黨
少年人的悲傷事
少年人的危險事
集中營酷刑撼太行
婦女的冤仇深
槍決趙震元
捕殺侯小根
刮颱風橫掃上萬生靈
晉城縣自殺者名單
反擊右傾翻案風
劃線切瓜獄滿為患
徐志有的逃亡生涯
後記:省思與懺悔
附錄一:是誰殺了王尚志
立場不同判斷兩異
失蹤當晚被揪鬥
黑暗的歷史怪圈
名探出馬
十五年後的結論
附錄二:血火四新礦
這裡只生產仇恨的烈焰
坦克車與地雷陣
重炮轟開文革路
老兵張永富和小鬼王訓
奪命突圍全軍覆沒
白森森的人骨架子
附錄三:五路進剿看屍橫
發射毒氣彈
高平中學生的戰地日記
高平兩派戰死名單
序
序
我出生在山西晉東南,位於中國華北古老而又富饒的太行山地,平均海拔1000多米。具體說,我出生在上黨盆地長治市,一家由共產黨人創辦的醫院,叫太行白求恩和平醫院。直到我三十歲時候,才離開這裡。
一場曠日持久文革戰火,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之間,殺傷了萬千生命。激戰流淌出鮮血,浸染了太行山上這塊內陸地區,也浸染了我的少年時代,數十年未能褪色。屍體橫陳殘肢飛舞,是伴隨一代人成長的印象,扭曲我們殘破心靈永不康復。
文革時,晉東南地區轄長治、晉城等十七個縣市,人口近300萬。中心區域史稱上黨郡、潞安府,南部含澤州府,北部含沁州府。說太行太岳,說上黨盆地,說晉東南,差不多是一回事,不要弄錯。一九八五年以後,原先的晉東南地區分成了長治、晉城兩個地級市,南邊五縣歸屬晉城。
我所講述的恐怖故事,善良人難以置信,只是史實真相,不敢遮蔽。
我出生在山西晉東南,位於中國華北古老而又富饒的太行山地,平均海拔1000多米。具體說,我出生在上黨盆地長治市,一家由共產黨人創辦的醫院,叫太行白求恩和平醫院。直到我三十歲時候,才離開這裡。
一場曠日持久文革戰火,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之間,殺傷了萬千生命。激戰流淌出鮮血,浸染了太行山上這塊內陸地區,也浸染了我的少年時代,數十年未能褪色。屍體橫陳殘肢飛舞,是伴隨一代人成長的印象,扭曲我們殘破心靈永不康復。
文革時,晉東南地區轄長治、晉城等十七個縣市,人口近300萬。中心區域史稱上黨郡、潞安府,南部含澤州府,北部含沁州府。說太行太岳,說上黨盆地,說晉東南,差不多是一回事,不要弄錯。一九八五年以後,原先的晉東南地區分成了長治、晉城兩個地級市,南邊五縣歸屬晉城。
我所講述的恐怖故事,善良人難以置信,只是史實真相,不敢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