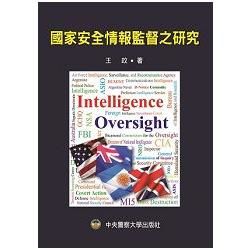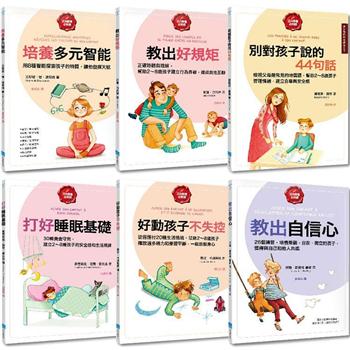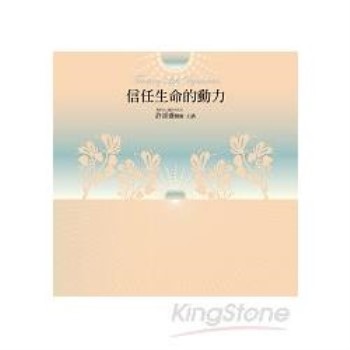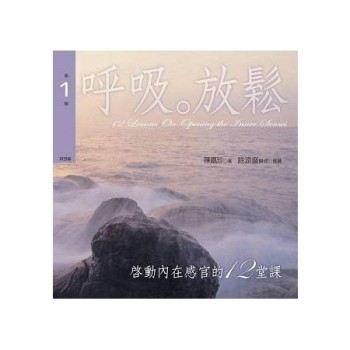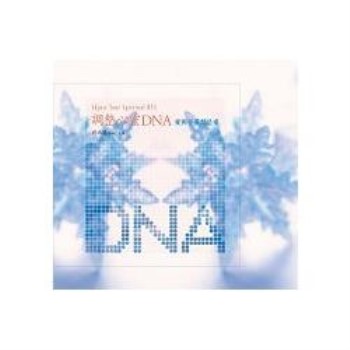第一章 導論
從古至今,人類大多處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為了求生存,總是期望有一位偉大的君王治理他們、保護他們;隨著國家的出現,人們進一步將安全感寄託在一個強大的國家。然而,國家為了對內治理及對外征戰之需,必須集中權力、掌握資訊、有效動員,但這些活動的本質卻與人類愛好自由、不受拘束的天性背道而馳,因此,人類便陷入對於國家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結中。為了解決這種安全與自由的困境,歷代哲學家及政治學家便不斷思考如何透過制度設計防止國家濫權。
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情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於國家的外交與軍事行動、經濟與產業發展、國內治安與偵防、反滲透與反顛覆,都需要情報做後盾,致使情報對政治、社會、文化及人民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情報時,很難忽略情報的政治性功能,尤其是情報做為國家控制工具的角色。
回顧整個20世紀,由於國際衝突不斷,國家競爭激烈,各國情報組織與規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與擴大。雖然冷戰在20世紀末結束,但國際社會在邁入21世紀時卻又面臨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區域性軍事衝突或內戰、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等挑戰,顯然的,情報仍將是國家安全決策機制與軍事作戰不可或缺之物。
然而,情報的運用正如一刀之雙刃,足以利之亦足以害之,情報機構神秘複雜,尤非一般人所能輕易駕馭,若無妥適之監控機制,極易成為反噬人民的怪物。以美國為例,不僅有龐大的情報體系,更擁有最先進的情報蒐集技術與工具,故美國國會自1970年代以來便積極行使情報監督的權力,隨後其他民主國家亦跟隨其腳步,透過法律與組織逐漸建立情報監督機制;至於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在民主鞏固時期也紛紛致力於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調整及安全部門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
第一節 情報監督制度的精神與發展
為何近年來情報監督(intelligence oversight)成為國家安全與政府治理的重要議題,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情報機關通常以秘密方式運作,其活動本質往往抵觸民主社會所強調的公開、透明之核心價值,然而,民主國家情報機關又以捍衛民主為其存在之理由,可見兩者之間自始存有矛盾的關係,為了保證情報機關是為民主國家服務,必須設計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才能避免秘密的情報活動傷害民主價值。
其次,為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必須建構一個有效的情報體制,故情報機關通常擁有特別的權力,例如搜查、監聽、調查、訊問等,倘若缺乏一套控制方法,情報機關在行使特別權力時很容易濫用權力,甚至戕害人權。
再者,機報機關蒐集的資訊,往往具有重要用途,甚至帶有特別含意,可能傷害到無辜的人,但情資的來源與蒐集手段往往屬於機密,為了確保資訊的正確性,並且讓政府決策者或人民相信情報機關的公信力,必須有一套科學的評估與監督方法。
還有,儘管世界各國情報機關的存在已有超過百年、甚至數百年的歷史,但因為運用情報是統治者的手段之一,故大多數國家(包括民主國家)的情報機關都曾有過壓制、迫害、監視人民的紀錄。相對而言,各國的情報監督卻是近年來才開始受到重視,透過有效的民主控制,將可避免情報機關重蹈錯誤,再有機會侵犯人權。
以美國為例,由於珍珠港情報失誤的慘痛經驗,以及冷戰時期面臨蘇聯擴張的國家安全威脅,在1947年中央情報局(CIA)成立的最初25年中,國會對其活動基本上是採取信任和支持的態度,目的在發展一個強大有效的情報體系。然而,受到1970年代初期「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和反越戰示威的影響,以及一連串媒體報導有關CIA在世界各國從事秘密暗殺、顛覆的任務,包括智利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越南共和國總統吳廷琰(Ngo Dinh Diem)、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理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等人;還有CIA與聯邦調查局(FBI)在國內非法進行國內情報活動以打擊異議人士和反越戰份子的負面報導,不僅美國民眾與國會感到震驚,國會也改變與情報機關合作的關係,成立調查委員會針對情報機關的違法濫權展開檢討調查,同時立法約束情報機關活動,最後更在國會參、眾兩院分別設立常設性情報監督委員會。2
綜合以上分析,足見情報監督的必要性已成為民主國家的共同認知,因為先進民主國家瞭解,若無課責機制,權力獨佔必然產生濫權問題,因此在情報監督上採取較為積極的政策。然而,由實務經驗觀之,世界各國在推動情報監督的歷程與步調並不一致,即便在民主國家中,對於情報機關的開放程度與監督方式仍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建立情報體系,但1952年CIA即已設置督察長,1970年代也在國會設立情報監督的專門委員會,1978年「督察長法」通過以後,各部會及主要情報機關陸續設置督察長,使情報監督制度逐漸完備。澳洲雖於1987年設置「情報與安全督察長」,但直到2001年才在國會設立常設的情報監督委員會。英國的民主政治歷史悠久,也是最早發展情報機關的國家,卻是1994年才設立「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但非國會專門委員會,其獨立性和監督權力都受到限制,直到2013年才通過「司法暨安全法」,使「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成為國會的專門委員會。此外,英國情報機關至今仍未設置督察長,雖有「督導專員」一職之設置,但其職權僅限於審查大臣關於令狀的核發與情報機關對令狀之執行,無法與美國及澳洲的督察長相提並論。
造成以上差異之原因,論者會指美國為總統制國家,憲法揭櫫的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s)與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原則,使國會對於行政部門的強力監督得以落實在情報政策上。然而,許多總統制的民主國家,情報機關卻未必受到有效節制,以阿根廷為例,在1983年結束軍人獨裁統治、恢復民主政治以後,雖然1992年通過的「國內安全法」規定在國會設立常設性情報監督委員會,但委員會僅具諮詢功能,無任何強制力,阿根廷亦無法律規範情報機關之運作,直到2001年通過「國家情報法」,情報體系始有法律依據,並賦予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實質的預算審查及調查等實質權力;然而,阿根廷至今仍未設置督察長負責情報機關的行政督控。
因此,本書選擇美國、英國、澳洲及阿根廷為研究個案,從政府體制、歷史發展、政治文化等因素,探討個別國家情報機關及其監督機制發展的歷程,並分析主要的情報監督機制的運作方式與功能,包括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行政督控、督察長(或督導專員)、司法審查、調查委員會等,最後再進行跨國情報監督之比較,並且論述外國經驗對我國情報監督之啟示。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國家安全情報監督之研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社會哲思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政治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政治 |
$ 428 |
社會人文 |
$ 428 |
軍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國家安全情報監督之研究
情報是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必要之物,然而,情報活動的隱密性與民主政治強調的公開、參與、互信的價值在本質上是衝突的;情報蒐集的手段甚至會與法治及人權保障相互違背。因此,民主國家會透過各種監督機制,確保情報機關的政策與運作得以落實公共課責的精神,情報活動皆能符合合法、適當、效能和效率的原則,使情報機關成為國家安定的磐石。然而,由於政府體制、政治發展經驗、安全威脅環境、以及政治文化等差異,不同國家的情報改革與監督制度也未盡相同。
本書分為八章,第一章闡述情報監督的緣起、重要研究文獻、個案選擇的理由及分析架構。第二章說明情報的概念與特質、情報對民主的威脅、情報監督的意義及目的。第三章介紹民主國家主要的情報監督機制,包括:國會監督、行政督控、督察長或督導專員、司法審查、調查委員會、媒體與社會監督等。第四至第七章分別探討美國、英國、澳洲及阿根廷等四個國家的情報體系、邁向情報監督的改革歷程,以及主要的情報監督機制。第八章對四個國家情報監督的特色及制度進行綜合比較,最後論述外國經驗對我國情報監督之啟示。
作者簡介:
王政
現職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學歷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博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經歷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訪問學者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薦任科員
民國83年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及格(英文組)
民國83年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及格(國際關係學門)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導論
從古至今,人類大多處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為了求生存,總是期望有一位偉大的君王治理他們、保護他們;隨著國家的出現,人們進一步將安全感寄託在一個強大的國家。然而,國家為了對內治理及對外征戰之需,必須集中權力、掌握資訊、有效動員,但這些活動的本質卻與人類愛好自由、不受拘束的天性背道而馳,因此,人類便陷入對於國家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結中。為了解決這種安全與自由的困境,歷代哲學家及政治學家便不斷思考如何透過制度設計防止國家濫權。
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情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於國家的外交與...
從古至今,人類大多處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為了求生存,總是期望有一位偉大的君王治理他們、保護他們;隨著國家的出現,人們進一步將安全感寄託在一個強大的國家。然而,國家為了對內治理及對外征戰之需,必須集中權力、掌握資訊、有效動員,但這些活動的本質卻與人類愛好自由、不受拘束的天性背道而馳,因此,人類便陷入對於國家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結中。為了解決這種安全與自由的困境,歷代哲學家及政治學家便不斷思考如何透過制度設計防止國家濫權。
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情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於國家的外交與...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情報監督制度的精神與發展
第二節 情報監督的研究方法與文獻
壹 法律與制度研究
貳 Smist的國會監督模式
參 Johnson的衝擊理論
肆 Johnson的國會議員角色類型
伍 Bar-Joseph和Weeks的國家與情報關係理論
第三節 個案選擇與分析架構
壹 個案選擇理由
貳 本書分析架構
第二章 情報與民主的衝突及調和
第一節 情報的概念與特質
壹 情報的意義貳 情報的功能
參 情報的本質
第二節 情報對民主的挑戰
壹 機密文化與民主程序的衝突
貳 情報活動與民主價值的衝突
參 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的衝突
肆 情報機關...
第一節 情報監督制度的精神與發展
第二節 情報監督的研究方法與文獻
壹 法律與制度研究
貳 Smist的國會監督模式
參 Johnson的衝擊理論
肆 Johnson的國會議員角色類型
伍 Bar-Joseph和Weeks的國家與情報關係理論
第三節 個案選擇與分析架構
壹 個案選擇理由
貳 本書分析架構
第二章 情報與民主的衝突及調和
第一節 情報的概念與特質
壹 情報的意義貳 情報的功能
參 情報的本質
第二節 情報對民主的挑戰
壹 機密文化與民主程序的衝突
貳 情報活動與民主價值的衝突
參 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的衝突
肆 情報機關...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政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3-01 ISBN/ISSN:978986571718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98頁 開數:20K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