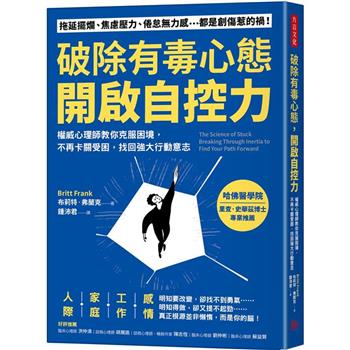越讀眼淚就越是不自主地落下
引起國外讀者廣大迴響,國外媒體一致好評的「必讀」小說
一部撫平死者傷痛,療癒生者哀傷的鎮魂文學
絕對會讓你想好好珍藏一輩子
★榮獲
第11屆本屋大賞第8名
第10屆《達文西》編輯部推選2013年白金之書iBooks Best of 2013的Best Book
第2屆靜岡書店大賞小說部門大賞
第35屆野間文藝新人賞
紀伊國屋書店店員全力推薦Best30「KinoBest!2014」第1名
★獲選為
第149屆芥川賞候補
第26屆 三島由紀夫賞候補
只要用心傾聽,你一定能聽見他們的聲音
那些,來自亡者的聲音-—
你相信嗎?
只要透過這台收音機,就能和那些離開的、以為永遠都無法再見面的逝者再度對話
所有想說卻來不及說的話,所有的眼淚、悲傷與遺憾都能藉由DJ傳達給彼此
如果這是可能的,你最想和誰說些什麼?
在海濱的城鎮,不知何故被掛在高大松樹頂端的DJ Arc主持著一個名為「想像收音機」的廣播節目
他使用「想像」這個電波,持續播放著只在「你的想像之中」才能聽到的廣播
唸誦著聽眾寄來的信件,不斷饒舌說話的Arc其實有個他不論如何都想聽到的「聲音」——。
「想像力是我們的電波其實是錯的。
哀愁才是我們的電波,哀愁是我們的麥克風、是我們的播音室,化成了你們所聽見的我的聲音。」
作者簡介:
伊藤正幸
一九六一年生於東京。作家、創作者。自早稲田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任職出版社編輯,目前活躍於音樂、舞台劇、電視等領域中。一九八八年以小說《No-Life-King》出道,一九九九年以《植物生活》拿下第十五屆講談社散文大獎。另著有《World’s End Garden》《當果陀讓人等待》(戲劇)《文藝漫談》(與奧泉光合著,文庫版發行時改名為《小說的聖典》)《Back 2 Back》(與佐佐木中合著)等。
譯者簡介:
蘇文淑
雪城大學建築研究所畢,現居京都,專職翻譯。
springbest@hotmail.com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第11屆本屋大賞第8名
第10屆《達文西》編輯部推選2013年白金之書iBooks Best of 2013的Best Book
第2屆靜岡書店大賞小說部門大賞
第35屆野間文藝新人賞
紀伊國屋書店店員全力推薦Best30「KinoBest!2014」第1名
名人推薦:
「我喜歡聽廣播。沒有影像的聲音,讓人有更多天馬行空的空間,激發無限的想像力。主角DJ Arc在生與死之間穿梭,當我閱讀這本書時,彷彿自己也正在收聽DJ Arc的廣播,字裡行間都是扣人心弦的聲音。『生者和亡者的關係是互相平衡』,人活著的記憶裡總是少不了對死者的悼念。這本書讓我瞭解到原來生與死是如此地貼近……」──一青妙
「用另一個世界寫三一一事件,除了哀愁,還帶領出希望。」──張國立
「隱忍或遺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創傷的療癒需要過程,思念的對話更需要勇氣,回不來的悔恨與走不出去的糾結,這次我們藉由《想像收音機》的真情告白,放聲大哭,選擇面對,進而找到重生的救贖。」──小葉日本台
「三一一後,伊藤就到災區做志願活動,據說聽到了很多『死者的聲音』。作為創作者,他決定重新執筆把那些聲音用文字記錄下來,並傳播給廣大群眾聽,結果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目共睹,這是震後日本出現的第一部安魂曲。」──新井一二三
得獎紀錄:第11屆本屋大賞第8名
第10屆《達文西》編輯部推選2013年白金之書iBooks Best of 2013的Best Book
第2屆靜岡書店大賞小說部門大賞
第35屆野間文藝新人賞
紀伊國屋書店店員全力推薦Best30「KinoBest!2014」第1名名人推薦:「我喜歡聽廣播。沒有影像的聲音,讓人有更多天馬行空的空間,激發無限的想像力。主角DJ Arc在生與死之間穿梭,當我閱讀這本書時,彷彿自己也正在收聽DJ Arc的廣播,字裡行間都是扣人心弦的聲音。『生者和亡者的關係是互相平衡』,人活著的記憶裡總是少不了對死者的悼念。這本書讓我瞭解到原來生與死是如...
章節試閱
晚安。
早安,
或者,午安。
歡迎收聽想像收音機!
不好意思,節目一開播的招呼說得這麼模稜兩可,其實本節目沒有時間限制,只在聽眾的想像力中播放。你可以選擇在靜謐月光洩下的銀色夜晚即時收聽,也可以在清晨還積著一層薄雪時重聽兩天前的深夜節目──如果有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在陽光普照的大白天裡重播我今天早上清爽的聲音。
不過完全沒有一個基準時間好像也有點麻煩,我看看……好!就以我這兒的時間為準吧!現在應該要跟大家說晚安了。此刻是萬籟俱寂的深夜兩點四十六分。哎唷唷,好冷呀!快結冰了。其實我現在全身凍僵,在這飄雪的深夜裡,我身上只穿了一件紅色的防風薄外套。感謝各位在這樣的靜夜裡收聽本節目。
自我介紹得有點晚,我是很會說故事的DJ Arc。Arc這個字來自於我的姓氏諧音,現在剛好發生了點事情,很適合Arc這個擁有「方舟」含意的綽號。
這方面的事,晚點有機會再來跟聽眾朋友聊聊。本節目《想像收音機》既沒有贊助商、沒有電台、也沒有播音室,我眼前也沒擺著麥克風。其實我連嘴巴都沒有打開呢。那麼各位怎麼會聽見我的聲音呢?還記得我一開始時提到的某個字嗎?想像力!是的,正是各位的想像力化成了電波、變成了麥克風、蓋了播音室、架起了電塔,化為了我的聲音。
各位還喜歡我的聲音嗎?是不是像上低音薩克斯風一樣地低啞渾厚?還是像海邊的死小孩尖叫聲那麼刺耳?或是像和紙表面聽起來沙沙的?像融化的巧克力那麼柔膩?我相信聲音也有各種質感,請各位調到你們自己喜歡的聲道吧。
不過請記得,我的聲音絕對跟任何人都不像。雖然是個剛出道的菜鳥,我還是有身為廣播人的自尊呢。
那麼,歡迎收聽本節目。
想~像~收音機~~
就在可能高揚振奮、可能輕柔、也許像重低音一樣低沉的台呼之下,來給各位一點暗示,我年紀應該比各位想像的還大囉。呃──今年三十八歲了。大家以為我還更年輕?嘿嘿嘿,那還不錯,表示我聲音還挺有張力的。人到了這年紀哪,什麼事都要正面看待,不然怎麼在社會上討生活啊?喔哈哈。
說到這兒,今年如假包換、三十八歲的我正是在這個小巧的海邊小鎮出生的,沒想到現在自己的身體──這個想像收音機的播放據點──居然會困在這個冬季漫長的地方。我是一家米屋的次男。之所以講這件事是因為附近可能有知道我家的聽眾朋友正在收聽。現在你們腦海裡可能浮現了一家老舊的米店吧。感謝各位長期以來關照我家那個小個子的父親跟大塊頭的哥哥。至於我,我倒是沒在店裡幫忙過,除了小時候在附近鄰居辦喪事時幫忙顧一下店,或是在後頭米倉玩時,看著貨車上的一袋袋米卸下來而已。
差不多國中二年級時,我開始迷上了廣播,總是很激動地黏著只能依稀聽見接收自訊號圈外的深度音樂節目。考上一間三流大學後我去了東京,拿著家裡寄來的生活費買了電吉他、弄了個非洲鼓,參加個怪怪的樂團,那時候我們評價還不錯,可惜最後沒有出道,我進了一間小型音樂事務所工作。
噢對了,我大學時念的是文學部。那時候只是因為剛好迷上了美國文學,沒有多想就選了美國文學當主修,當然都是看些翻譯作品啦,哈哈哈。不過那時候我把可以弄到手的外國小說都讀光了,我特別偏好結構比較特別的。受到影響之下也寫了不少短篇投稿到同人誌。有一篇叫做《SHAKE》的寫一個在店內水族箱裡養鼓蟲的調酒師。那篇小說的觀點很跳躍,一下子跳到這、一下子跳到那,最後還跳到了一個經過店前的男性視角。現在想想,其實就是一般年輕人常寫的平凡小說。有一陣子我也想當作家,但實在想不出來要怎麼靠那吃飯,如果一出道沒掄下什麼大獎,光靠打工、玩樂團跟寫小說一定完蛋吶。
最後,一個還滿關照我們樂團的事務所社長,叫做高瀨的,滿臉鬍子。剛好很喜歡我,他半強迫似地逼我去他們事務所上班。我一路帶了幾個樂團,像是在獨立樂界還滿紅的Metals、mighty flower、Atom & Uran等等還有一些新人,但經紀人當久了不知不覺間開始厭煩,可是我還是幹了十幾年唷,終於在昨天狠下心來搬回故鄉。回到這個有山有水還有小河的小鎮,帶著比我大的老婆。
我還有個國二的兒子,不過沒跟我們一起回來。他去美國念國中了,寄宿在學校。哎唷,是我老爸贊助的啦,我也是為了兒子好才不得已當個啃老族嘛。我自己不成才,是沒什麼資格這麼講啦,不過我兒子在日本繼續念書沒問題嗎?我是真的很擔心。剛好有一天我太太拿了留學簡章回來,我一看這簡直是天意哪!趕緊哭著去找我老爸贊助。當我事先問過我兒子的意願。這小孩子體格不好,常發現他這裡、那裡烏青一塊地回家,也不曉得是不是在學校裡發生了什麼事。大概也因為這樣吧,我們問他的意見時,他也一口就說他要去美國。
昨天搬回來後,我的心情已經看開了。噫,是呀,現在回到了故鄉。再來不得不考慮往後的生活了。其實我可以靠著之前累積下來的人脈跟經驗,在這小鎮繼續從事音樂工作,不過各位也知道現在業界情況很不景氣。我老哥說,不然你一邊幫忙家裡生意、一邊跟我合開公司賣園藝用土。那些土還可以賣給農家,泥土對農家來講算是資財。我老哥剛好認識一位專精這方面的大學教授,所以這門生意或許可以考慮。前方的路雖然還不知道要怎麼走,但我也不假思索地大轉彎了,反正我一路都是這麼邊走邊想辦法。。
結果沒想到,現在居然會變成這樣!我被勾在一棵高聳的杉樹頂端,沒事可做之下只好開始廣播。到現在我還是懷疑這一切都是狐仙做出來的幻覺。對呀,聽眾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吧。杉樹?是呀,我現在就掛在杉樹上呀!
算了,現在應該先來播首歌。為各位獻上本節目開台第一首──一九六七年The Monkees樂團的《Daydream Believer》,敬請欣賞!
Daydream Believer!歡迎回到DJ Arc的想像收音機。哇,這首歌曲真的太適合本節目了,真是首名曲!講一個相信白日夢的男人。剛才播歌的時候,有些朋友應該想起了忌野清志郎所率領的The Timers樂團翻唱的日文版本,那一首我剛剛也播了唷。
本節目可以多線播放。不但如此,如果有聽眾朋友想多聽幾首The Monkees的歌,接下來將一次讓您聽個夠!如果不想聽音樂,那這個節目連一首音樂都沒有。二十一世紀的廣播節目充滿了彈性、自由自在,請聽眾朋友隨心所欲選擇你想收聽的方式。
好吧,在下DJ Arc,想說的話如滔滔江水滾滾不絕,就像一輛超載的卡車左搖右晃地全速前衝!現在我想麻煩各位再聽我講一下剛剛那件辭職的過程,哎呀呀我不是要抱怨啦,不要擔心嘛。
說起我以前,也有過像彈珠一樣亮晶晶的夢想,我陪著那些根本一隻腳還跨在童年裡的年輕人玩音樂,到處巡迴,有時候去的live house小到會讓人懷疑「喂,這是套房吧!」。那種地方的休息室通常都妙到讓人捧腹大笑,例如走廊上隨便堆幾個紙箱就叫你在後面換衣服的情況簡直是家常便飯。哦噢,您不知道,在紙箱後面換衣服這種事對男孩子來說還好,反正我們家也沒有視覺系藝人。我家的不是玩龐克的就是一天到晚跳舞跳個不停的放克掛,換掉這件T恤後再穿上另一件更髒的T恤就上場了,所以他們根本不在乎在走廊上換衣服,這樣反而更顯得傳奇。
問題是女生或女子團體就不行了,士氣明顯會遭受打擊。明明等一下就要像個明星一樣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了,上台前卻被澆了一大盆冷水,覺得自己好像是隻被趕到走廊角落的老鼠一樣。那種漂散著霉味的地下一樓,通常都有幾盞要壞不壞的燈,在那不知道被多少少男少女踢得凹下去的紙箱後面,我的明星們就站成一排、背對著讓女孩子換衣服。偏偏這種時候很該死地一定會從哪裡傳來「咿呀哈哈」的嬉鬧聲。
咦,該不會聽起來還是像在抱怨吧?可是對我來講那已經是久遠得有點害臊的往事了,記憶的畫面像披上了層黑白或棕褐色的霧,轉速有點慢。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我上班的最後那五年,剛才我提到的那些live house幾乎全數滅亡。因為有一家財力雄厚的財團推出了許多時髦的音樂空間。現在我眼前這塊被山與海環抱的土地上應該還沒有,不過那種看起來漂漂亮亮的空間其實就是騙這些鄉下地方喜歡玩音樂的年輕人。說騙可能不好聽啦,但就是跟年輕人收收場地費、讓年輕人自我感覺良好,可是在那樣的音樂空間表演跟去卡拉OK唱歌其實沒什麼兩樣。
如果練團室也是同一間公司開的那更慘了。好像倉鼠被放進跑球裡跑一樣,一個晚上跑幾十公里還是在原地踏步。那倒不如像以前那樣在髒亂的live house表演比較好,至少眼神裡閃耀著對未來的希望。我就是懷念這點!
哎,算了,總之我辭職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再看到這些纖細、脆弱、自我中心又自暴自棄的年輕人。我覺得繼續待在他們身邊的話真是又恐怖又傷心,好像看著成熟的水果紛紛染病,一顆顆掉下來一樣,又惱又氣,對這個放任不管的社會已經不滿到了極點,於是我就跟我們事務所的高瀨先生把一切都說了。在東京一家我們常去的吉祥寺居酒屋。
高瀨先生聽完我辭職的理由後,很沉重地開口說你說的理由我都懂,不過你不能跳過自己亂花公司錢的事不講吧?哎呀呀,被發現了。我常趁去別的地方出差時黑點小錢。
說黑是太誇張了,因為金額也不是多大筆。不過就是我們去Live House表演時,結束後公司其他人先搭公司車回去,我則一個人去跑附近城市的電台跟唱片行推銷新歌,拜託唱片行把我們唱片擺前面一點。我們這種小事務所不像一般大公司,經紀人什麼事情都得做,包山包海。
出差時我會跟公司詐領一些根本就沒去的地方的交通費、跟朋友吃喝玩樂當然也照請,其實就是一般上班族很常見的行為,但一筆筆累積下來倒也是不小的金額,我原本打算趁還沒有人發現時趕快包袱款款閃人,沒想到被社長高瀨先生看破了,哈哈哈。被反將一軍。
哎呀,我怎麼從熱血沸騰的心情聊到貪小便宜的行為去了,有聽眾朋友的信進來了。嗶嗶!直接傳進了我頭裡囉。這封信來得真是時候,不然現在話題像大雨即將落下的天空那麼沉悶了。Nice timing!趕緊來拜讀。
「晚安,DJ Arc。」
晚安
「我在和你截然不同的地方收聽節目,這裡冬天很短。我離你那裡很遠,看不見你在杉樹上的樣子,不過可以清楚聽見你迷人的聲音。我在我們這裡的live house聽過你帶的那個《Metals》耶。那時候幫他們暖場的是我前男友的樂團。我記得《Metals》是個三人組成的ska樂團對不對?很酷,而且他們表演完後還下來跟我們聊天。我跟那個金髮主唱聊了滿久。我記得他說他跟他女朋友住的房間水龍頭出水有問題對不對?那時候可能跟你在同一個地方擦身而過幾次吧?太巧了。我一定會繼續收聽這個節目,請加油。」
感謝來自福岡的想像之名小風呂敷小姐。哇噻,真是太巧了,嚇我一大跳。居然這麼快就碰到了有緣人。那時候跟你聊天的那個金髮男叫做寬太。我記得我們是三年前去福岡的天神表演吧?那小子啊,後來跟一起住在水龍頭有問題的那間房間的女生結婚了。那場表演過了大概一年之後吧,他在初夏的某個週日跑去西新宿喝酒時跟一個陌生男人吵架,拿酒瓶砸了人家的頭後跑了。他說,也不曉得為什麼當晚就跟他女朋友求婚,可能是怕被抓走就沒機會吧。不過他們兩個好像也沒登記。他把頭髮染綠,改變一下外貌,現在還在《Metals》唷。
咦,怎麼又扯到了奇怪的話題。明明是本節目第一封來信耶。來轉換一下氣氛好了,聽首好歌──1979年,The Boomtown Rats的《I Don’t Like Mondays》。
感謝各位收聽,來自Bob Geldof的名曲。一次又一次唱著「我討厭星期一」的這句歌詞,給這首歌帶來了濃厚的憂鬱效果,並且也充滿了戲劇性。大家可能知道這首歌來自於某個年輕女孩持槍亂射的真實案件,當然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已經有點年代了。各位還記得那個大我十歲的大塊頭哥哥嗎?他房間很幸運地位於二樓的東南邊,那傢伙是我們家族的小霸王,什麼最好的東西都留給他。那時候我常溜進他房間聽唱片,就在那時候聽了許多音樂。不過在星期五播放這首描寫星期一的歌曲好像有點奇怪噢。不對,現在是半夜,正確來說應該是禮拜六了。喔哦,我選錯歌了,哈哈。
好囉,各位聽眾對於本節目《想像收音機》以及對於我──DJ Arc是不是已經有了點認識呢?接下來時間還早,我們還沒有要進入下一個階段,我想先拉低一下聲音,提一下稍微複雜的情況。剛剛小風呂敷小姐的來信裡也提到,我現在正困在一棵高聳的樹梢上。在一座俯望小鎮的、長滿成排杉樹林的山上。我斜斜地掛在一棵彷彿要刺像天際的杉樹頂端,頭往下垂地仰躺著,望著遠處的小鎮,視野整個顛倒。感覺好像吉爾伽美什(Gilgamesh)神話裡,洪水退潮後被留在高處的方舟一樣。
現在大地雖然籠罩在幽冥之下,不過我右手邊有好幾座也長滿了杉樹的小山,從那邊,有條水位稍低的小河往我現在的這片山林穿過一路流經了小鎮,最終匯入太平洋。沿著太平洋岸邊有條鐵軌,再往前不遠應該可以隱約看見一座山的中間挖了一條隧道。那些景象現在在我眼裡完全上下顛倒,好像違反了重力法則,統統從地面往下吊。
我左手裡握著一台打開的防水手機,雖然我很努力讓畫面進入視線範圍內,可是手機的歪斜角度太大了,根本看不到字。我有時候看得到亮光,也能從震動模式跟光線裡知道有人打來,大概猜得出是誰,因為我設定了很細膩的震動模式。我想應該是家裡人打來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不曉得為什麼在這麼高的樹梢上,從我左手邊延伸過去的方向有隻白鶺鴒停在樹枝上,我可以隱約透過手機發出來的光看見牠。白鶺鴒是種像鴿子那麼大、尾巴細細長長的鳥,我很喜歡。不知道為什麼,那隻鳥一直往下盯著我……噢不對,應該是我由上俯視牠,因為現在上下顛倒了。總之那隻鳥從剛才就一動也不動,好像在監看我主持節目一樣。啊哈哈,牠該不會以為牠是節目監製吧。
總之我好像維持這個狀態已經有一陣子,可是我完全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出事前的記憶一片空白,我只記得我的身體漂浮在半空中,被左拉右扯一直不斷繞圓圈。所以我考慮了各種可能性,譬如聽眾朋友不曉得知不知道一位叫做良弁的和尚?以前我念書時,也就是還沒跟我老婆結婚前,她有個女性朋友剛好多了幾張票,我們三個人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就去看了文樂──那種傳統的日本偶戲。當時我完全看不懂在演什麼就回家了,還被不久後結婚的老婆取笑,不過我記得內容大概是演長大後興建東大寺的良弁在嬰兒時期曾被一隻大鵰攫走,從不曉得京都或滋賀縣的地方一路攫到了奈良的二月堂附近。那隻大雕把他掛在杉樹的樹枝上。後來一個偉大的和尚發現了他,把他救下來。
我現在大概只記得這些。那時候我覺得故事內容好虛幻,好像是誰的夢境一樣。舞台上,一個很嚴肅地拉著三味線的人身邊坐著一個頭髮雪白的爺爺,漲紅了臉很認真地講故事。我有一瞬間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因為實在太睏了,我幾乎睡了一整場。
現在我懷疑一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雖然我不是嬰兒,我以後也不會變成高僧,不過就在我回到故鄉打算先安定下來再想辦法、把家當都搬進了公寓五樓的隔天大概中午過後吧,因為我答應我老婆不在新家的室內抽菸,跑去了陽台,拿出紫色打火機,正當我往下一看,忽然間一隻巨鵰伸爪掠住了我的肩膀,把我左搖右晃地抓起來。我就這麼晃呀晃呀晃、不停往上升,我茫然地看著底下閃過的街道景象。狹窄的港灣、圍繞著港灣的群山,人們努力在港灣跟群山之間的狹小土地上開發出來的住宅跟店鋪、郵局、醫院等等,感覺好像在看谷歌地圖。
說真的,我好像真的有聽到啪咑啪咑的翅膀拍動聲耶,鼻子深處似乎也聞到了巨鵰的臭味。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扯,但不然你怎麼解釋一個大男人為什麼會被勾在樹梢上呢?所以這一定是真的。
只不過我還沒有被偉大的和尚發現。不要說和尚了,四周安靜得好像連一個人也沒有。眼前顛倒的這個小城市裡沒有半個人影,我就是為了克制心底的恐慌才開始劈哩啪啦地講話,這個《想像收音機》根本就是我為了排遣寂寞而在無奈下做出來的節目。我現在到底處在一個發生過什麼事情的世界?想到這點,我頭又開始痛了。
想~像~收音機~~
喊完了台呼,話題還是不變。哈哈說真的,我現在在這裡有好幾次都想起我爺爺。那應該是我兩、三歲的時候吧,正好是人類最早有記憶的年紀。後來再對照上我爸媽的講法、看了照片,我發現我好像一直記得自己被爺爺抱起時的那份感覺。
我很討厭他。嬰兒的時候,大概只是害怕被他抓住而已,長大後無意間察覺他跟我國一時過世的母親合不來,何況我還看過我媽跑到倉庫後那棵大柿子樹底下去偷哭。說到那棵大樹,後來倉庫改建時砍掉了,真的很高大唷,寬厚的樹幹從倉庫的屋簷角落穿過,挺拔聳立,如果下雨時雨滴不是橫著飄,樹幹永遠都是乾的。爬上那棵樹時,手腳總會被乾裂的樹皮刮出一條一條長長的刮痕,很痛。
那時候我媽跑到大樹後的時候,身上還穿著圍裙,大概是晚餐前吧。我聞到了味噌湯的香味,也聞到了燒洗澡水的柴香。說來丟臉,我小時候我們家還是燒水洗澡。我聽見從主屋的後頭,爺爺房裡傳出了咳嗽聲,還夾雜著我爸壓低音量不曉得在說些什麼。我印象中,那時候已經塊頭很大的老哥無動於衷地繼續看著他的電視,那傢伙掌握了選台大權。不過說起來,我長大後居然還清楚地記得這一幕,可見我搞不好從本能上,從小就很討厭爺爺,就像所有想保護母親的小孩一樣。
至於他們兩個人為什麼處不來呢?我媽跟我爺爺現在都不在了,問我爸大概也問不出個答案。不過我知道我媽是從附近村落裡來的,她信基督教,也常上教會。現在家裡還留了幾張那時候的照片,所以我知道。我也摸過她的十字架項鍊,她也曾帶我去教會。有張不曉得是誰婚禮的照片,新娘子很漂亮,我也在照片裡。所以那時候她可能常常帶我去教會吧。
可是老哥卻沒有這一類相片。我媽剛生下我哥時應該也想過讓他受洗,因為有一次,我們一起坐在主屋的緣廊上,那時候當然是夏天,右邊前方那棵梅樹的綠葉擋著了豔陽,在庭院地上形成了一片濃密的樹蔭。我大概還在念小學低年級吧,上午課就上完了,跟老媽並坐著。老媽那時候對拿著她給我的冰涼果汁、一起坐在緣廊上的我說你哥其實還有一個名字,可是現在大家都忘了。我記得我那時候有點不開心,以為她想嚇唬我,可是我年紀已經沒有那麼小了。
我說,那個大家都忘了的名字叫什麼,結果老媽說了一個碎裂短詰的怪字眼。那怎麼可能會是人的名字呢?聲調那麼奇怪,而且也不像是會從老媽嘴裡吐出來的聲音。
那時候還很黏人的我問,那我呢?我有沒有別的名字?老媽沒有恬恬地笑,她只轉過頭去輕輕嘆了口氣。庭院石頭上反射出來的陽光折射在了她的臉龐上閃著,接下來,就出現一陣會在這種時刻出現的嘈雜蟬聲了。這是我腦海裡的印象。
但說起來,我爺爺也不是多麼虔誠的佛教徒,兩個人應該不會為了宗教原因而水火不容。我家的佛桌跟其他世居當地的大戶人家相比根本不算體面,佛桌上應該被線香燻得變色的那地方擺著遙控器跟爺爺揀回來的一些奇怪的小石頭、以及從我有記憶以來便已經過世的奶奶的相本。至少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搞不好爺爺只是跟我一樣,對於老媽嘴裡發出來那個奇怪的聲音下意識感到反感而已。我爺爺在這方面搞不好很敏銳,所以我可能是因為他的遺傳才喜歡音樂。話說我爺爺從米店批發業賺了不少錢後常找藝伎來家裡彈太鼓、三味線,吵得要命,還喜歡當場唱起鄉土民謠。我聽說過我老爸被他這些行為搞得很頭痛。
而且說是爺爺,其實年紀也沒有那麼大。現在我在這棵樹上算了算,那時候穿著圍裙跑去柿子樹後的老媽剛好三十歲,爺爺也才不過六十歲左右,一點都不老。當然在那時候被抱起來的嬰兒我眼中,他可能很老了,臉上有皺紋,嘴裡有種奇怪的味道,聲音嘶啞,下顎的白鬍子扎在臉上很癢。不過對於現在的我來講,那年紀並不會多遙遠。事務所的高瀨先生差不多就那年紀。
這麼一想,被我討厭了那麼久的爺爺其實也有些有趣的小故事呢。當然我也不是要把我媽長年吞忍的委屈給抹消掉,只是有一瞬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接下來的人生裡或許也會有需要跟爺爺討教的地方。
晚安。
早安,
或者,午安。
歡迎收聽想像收音機!
不好意思,節目一開播的招呼說得這麼模稜兩可,其實本節目沒有時間限制,只在聽眾的想像力中播放。你可以選擇在靜謐月光洩下的銀色夜晚即時收聽,也可以在清晨還積著一層薄雪時重聽兩天前的深夜節目──如果有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在陽光普照的大白天裡重播我今天早上清爽的聲音。
不過完全沒有一個基準時間好像也有點麻煩,我看看……好!就以我這兒的時間為準吧!現在應該要跟大家說晚安了。此刻是萬籟俱寂的深夜兩點四十六分。哎唷唷,好冷呀!快結冰了。其實我現在全身凍僵,在...
推薦序
作為安魂曲的小說
新井一二三
首先,我得坦白: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和接著發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對包括我在內的全體日本人,衝擊實在太大了,平心說出自己的感受非常困難。當時就有不少外國媒體報道說:日本人面對如此大的災難,但是在表面上看來大家都很平靜,即使在災區都很少看到哭鬧的人,社會秩序保持得又非常好。後來的四年時間裡,我們逐漸發現了:其實在災區有不少商店、房子給搶劫,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心,守紀律的。不過,表面上看來平靜這回事,倒是一向沒變的事實。
比如說我吧,平時是自他承認的「鬼婆脾氣」,以日本標準來看,感情起伏很不小。可是,那天經歷了平生第一次的大震動,我最關注的是兩個孩子的心情;為了不讓他們感到過度的不安,我作為母親盡量控制自己的感情,裝出了沒甚麼的樣子。過一年,有家台灣電視台送記者來日本做地震一週年的節目,他問我:你流過眼淚哭泣過嗎?我說:沒有,我住的東京西郊離震源有約四百公里,考慮到災區居民的心情,哪兒有份哭泣呢?台灣記者搖頭表示不理解;當時,我才知道,其實我都算是控制感情過多的日本人。
自從二〇一二年五月起,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重復播送慈善歌曲《花兒將開》。那是災區出身的音樂界人士攜手創造的一首歌兒。以影片《情書》聞名的導演岩井俊二寫的歌詞道:花兒,花兒,花兒將開,為了有一天出生的你,花兒,花兒,花兒將開,我到底留下了甚麼?顯而易見,歌詞的講述者是地震海嘯的受難者。也就是,眾幸存者站在死難者的立場唱這一首的。我每次聽到都心中受震撼,可還是不敢叫自己給感情淹沒。二〇一四年春天,我參加女兒的小學畢業典禮,聽到了孩子們合唱《花兒將開》,才讓自己流一次淚水,卻匆匆用手絹兒擦乾了。
地震發生後,一時有多數日本作家齊聲道:受了這麼大的刺激,沒法執筆寫東西了。後來的四年裡,還是一部又一部小說,一本又一本詩集出來,表達了作家、詩人的思念和感情。二〇一三年三月問世,被提名成芥川龍之介賞、三島由紀夫賞的候補作品,最後獲得了野間文藝新人賞的伊藤正幸作品《想像收音機》可說是其中的先驅。
伊藤正幸一九六一年出生於東京,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律系期間就當起藝人,畢業後則做了講談社時尚雜誌的編輯,辭職後的一九八八年寫小說《No Life King》受了注目。後來,他在平面媒體、電視台等各方面展開多彩的活動,最常用的頭銜是「creator」即創作者,對此誰也不敢反駁。三一一後,伊藤就到災區做志願活動,據說聽到了很多「死者的聲音」。作為創作者,他決定重新執筆把那些聲音用文字記錄下來,並傳播給廣大群眾聽,結果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目共睹,這是震後日本出現的第一部安魂曲。
雖說每個地方的災難都是很大的不幸,三一一特殊之處在於:因為後來發生了核電站事故,地震和海嘯的受難者沒能得到應得的救援和追悼。前所未有的大海嘯一下子奪走了無數無辜居民的生命,本來該盡量救援,衷心哀悼的。可是,後來的核電站事故,以看不見聞不到的核輻射嚇壞了人們,把整體社會的視線從受難者身上奪走了。有反省能力的人都很快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岩井俊二寫了《花兒將開》,伊藤正幸寫了《想像收音機》。
尤其在後者裡,吊在杉樹梢頭上不停地講話的主播,其實以視覺化的形式,嚴厲批評著自私冷漠的日本社會。
現在,通過翻譯,中文讀者都能讀到《想像收音機》了,我感到非常高興。台灣民眾對三一一受難者的慷慨支援,感動了很多日本人的。說實在,那大款捐金叫日本人重新認識到南方鄰邦台灣了。跟二〇一三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上,台灣隊離開球場前一齊脫帽子敬禮的場面叫觀眾刮目相看一樣,許多日本人在生活中和網路上都重復談到,並且相信會長期記住下去的。謝謝台灣!(日本作家,明治大學教授)
作為安魂曲的小說
新井一二三
首先,我得坦白: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和接著發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對包括我在內的全體日本人,衝擊實在太大了,平心說出自己的感受非常困難。當時就有不少外國媒體報道說:日本人面對如此大的災難,但是在表面上看來大家都很平靜,即使在災區都很少看到哭鬧的人,社會秩序保持得又非常好。後來的四年時間裡,我們逐漸發現了:其實在災區有不少商店、房子給搶劫,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心,守紀律的。不過,表面上看來平靜這回事,倒是一向沒變的事實。
比如說我吧,平時是自他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