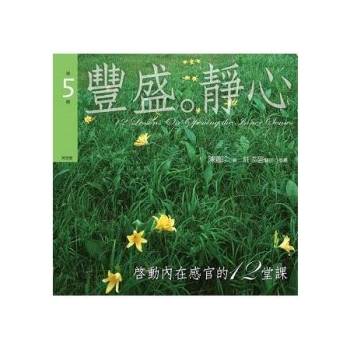為了所愛,即使僅有一絲絲希望,我也將予以反擊!
「救命!救命!如果有人聽見,快撤離這個區域。……已經被消滅了……我重複,安全之家已經被消滅了。……」
安珀告訴自己不要再逃了。
幾個禮拜以來,她和查斯是聯邦感化局通緝的最危險逃犯。
終於抵達安全之家的他們,以為多年來未曾感受到的安心與和平終於到來……
誰知安全之家早被感化局摧毀,只剩廢墟。
最後的希望被摧毀,安珀跟查斯心力交瘁,只能踏上唯一的道路——
跟蹤從廢墟離開的行跡,深入野外和荒廢的城市逃避追捕。
沿著可能的路線朝海岸地區接近,終於找到一座由廢墟建造而成的難民營。
然而,讓查斯最無法承受的是,迎接他的人,是他這輩子最想念,卻也最不想面對的人。
懷著一份渺茫的希望,他們決定一起投靠傳說中的反抗據點:組織三。
但這個組織真的存在嗎?
安珀利用他被誤認為狙擊手的身分反咬道德軍一口,卻忘記防備自己最該防備的人。
塔克,安珀的殺母仇人,最終還是背叛了他們。
查斯被道德部隊俘虜。被槍斃前,像畜牲一樣被鍊起來示眾。
士兵震耳欲聾地吶喊。在最後的反擊時刻,誰會死?誰又能存活下來?
本書特色
★超刺激的生存逃殺愛情小說!喜愛《飢餓遊戲》的人絕對不能錯過!
★《血衣安娜》作者凱德兒.布雷克看到愛不釋手
★國外熱銷!繼《夜之屋》之後,重點主推的暢銷系列
作者簡介:
克莉絲汀‧西蒙斯(Kristen Simmons)
克莉絲汀‧西蒙斯擁有社會工作碩士學位,也是推廣心理衛生的支持者。她與她的丈夫傑森,還有他們心愛的靈提獵犬魯迪,一起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第五條款》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作者網站:www.kristensimmonsbooks.com
譯者簡介:
楊佳蓉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現為自由譯者,背負文字橫越語言的洪流,在翻譯之海中載浮載沉。譯有《早安,陌生人》、《下一頁,愛情》(三采)、《壁花姊妹秘密通信》系列(繆思)、《女人心事》(馬可孛羅)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血衣安娜》作者凱德兒.布雷克大推:
克莉絲汀‧西蒙斯的《第五條款》實在是一個扣人心弦、愛情動人的生存故事。除了激烈的高壓政府,西蒙斯創造了一個暗淡陰鬱的失落國度。我簡直愛不釋手。
◎《暴風舞者》(Stormdancer)作者傑•克里斯多夫(Jay Kristoff)盛讚:
顛覆。反抗。絕望,在面對國家暴政下掙扎著人性的光芒。這本書引人入勝,故事充滿驚喜,徹底真實。我好愛啊!
媒體推薦:
◎Parajunkee書評網站:
情節快速,愛情又感動人,讓我邊咬指甲邊緊張。《第五條款》從第一頁就緊抓我的目光。
◎Book Reader Addicts部落格
今年一整年,只有少數幾本書能讓我看到整晚沒睡,《第五條款》就是其中一本。這本書是喜歡反烏托邦類型小說讀者「千萬一定要看的」,就算你不愛看這類型小說,也不該錯過!
◎VOYA雜誌:
喜歡看青少年小說的人必看的一本小說。
◎學校圖書館期刊:
《第五條款》絕對是一本超級刺激的生存逃殺羅曼史小說。老實說,我很喜歡這本書,眼睛一刻也離不開它。
◎美國著名Huffington Post新聞網站
這本像動作片般的反烏托邦小說,是我過去前所未見的。
◎哈芬登郵報
這部情節緊湊的作品中充滿我從未見過的敵托邦要素。
◎VOYA書評網
作者描繪出的世界很可能就是我們的未來,流暢的文筆創造出易讀的故事,令讀者大開眼界,看清喪失自由的後果。這本書是所有青少年應該收藏的小說。
◎亞特蘭大CW電視台
讓人念念不忘的情節,使讀者無比投入。真正的敵托邦勢力。
◎《最後的家園》的書評
很難判斷要相信誰、該相信多少。作者針對實用主義與暴力崛起提出很有趣的道德疑問,這些議題的答案都不簡單。劇情緊張,令人揪心。
名人推薦:◎《血衣安娜》作者凱德兒.布雷克大推:
克莉絲汀‧西蒙斯的《第五條款》實在是一個扣人心弦、愛情動人的生存故事。除了激烈的高壓政府,西蒙斯創造了一個暗淡陰鬱的失落國度。我簡直愛不釋手。
◎《暴風舞者》(Stormdancer)作者傑•克里斯多夫(Jay Kristoff)盛讚:
顛覆。反抗。絕望,在面對國家暴政下掙扎著人性的光芒。這本書引人入勝,故事充滿驚喜,徹底真實。我好愛啊!媒體推薦:◎Parajunkee書評網站:
情節快速,愛情又感動人,讓我邊咬指甲邊緊張。《第五條款》從第一頁就緊抓我的目光。
◎Book Reader Add...
章節試閱
夢境在變。即使還睡著,我依然感覺得到。
過去,夢中有母親跟我手挽著手,同樣的蠻橫命運拖著我們行過荒涼的街道:家園、士兵和鮮血。總是佈滿鮮血。但現在有些不同。有什麼東西中斷了。像是無法解開的謎題一般煩擾著我。
柏油路依舊破裂。鄰近住家等在原地,那鬧鬼般的沉默,每扇前門都貼著宛如瘟疫警示一般的條款。頭頂上蒼白呆滯的天空往兩側延伸,我獨自一人。
母親應該在我身後的,但這回換成查斯登場。
他不是現在的查斯,是那個我多年前認識的男孩——蓬亂的黑髮,大膽好奇的八歲小孩眼眸,有點太小的牛仔褲底下皺巴巴的白襪。他沿著車道奔跑,我咯咯笑著追在他身後。
他跑得很快;每回我揮手抓他,都被他溜開。我的手指總是與他飛揚的T恤相距數吋。他的笑聲往我心中填入某些遭到遺忘的溫暖記憶,霎時間,夢中只有歡愉。
但天空開始泛出青紫色澤,他在路中間無憂無慮踢石子的模樣突然令我擔憂。他還太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地方已經不再安全。我急忙握住他的手。
宵禁,我告訴他。我們得要回家了。
可是他反抗。
我想拉他進屋,沒用;他的小手好滑溜。漸漸消逝的天光讓我的恐懼更加緊繃。
他們要來了。我感覺到他們的腳步聲在我胸腔內迴盪。
黑暗降臨,如同煤炭一般漆黑深沉,最後我再也看不到兩旁屋子,眼前只剩天真的男孩,以及我們腳下的破碎路面。
一名士兵走近,制服燙得整整齊齊,即使身在遠方,修長靈活的身形依然太過熟悉。他的金髮閃閃發亮,在沒有月亮的夜色中泛出光暈。
我知道夢境的走向,但心臟依舊一路往肚裡沉。我試著把男孩往後推,讓他遠離這個殺了我母親的男人。你不准碰他,我對塔克.莫里斯說,然而我的口中沒有冒出半點聲音。腦海中的叫嚷似乎令塔克移動得更快,突然間他來到我們面前三呎處,槍口對准我的雙眼中央。
我尖叫著要男孩快跑,可是在我來得及轉身跟上前,我的視線掃過男子的臉龐。
不是塔克。在我面前的,是另一名士兵,膚色黯淡,雙眼早已死去,胸口有個淌血的洞。是我們在芝加哥逃離醫院時,殺死的士兵。
哈柏。
我倒抽一口氣,雙腳一絆,往後倒去。讓身旁的男孩暴露在槍口下。
哈柏開槍,槍響震撼了整個世界,路面裂開。等到槍聲停歇,男孩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胸膛開了一個拳頭大的洞。
我驚醒過來,繃著身子準備打鬥。我們從芝加哥醫院救出黎貝嘉途中,查斯射殺的士兵哈柏的身影漸漸隱沒,留下黏膩的殘骸,使得我無法繼續睡下去。
我的呼吸漸漸平緩,同時我也聽見周遭睡眠的聲響:沉重的呼吸以及此起彼落的鼾聲。背後的堅硬地板提醒我目前正躲在一間空屋,暫時離開我們睡了三晚的海邊。即將盈滿的沉重月輪在沒有玻璃的窗外窺看,幫助我適應黑暗。旁邊查斯的位置是空的。
我抽出纏在腿間的大浴巾。六個睡著的人散在房裡各處。像我一樣來海邊尋找安全之家的人,卻發現安全之家遭到摧毀,那裡是唯一所知、能夠逃離聯邦感化局壓迫的避難處。奇蹟似地,線索顯示有人離開了那片廢墟,於是我們組了一支小隊,循著蹤跡往南尋找,留下在芝加哥轟炸中受傷的成員。他們在爆炸範圍外的小超商等我們,他們身旁只有兩三名健康的守衛,以及極少量的食物與補給品。
我花了幾次心跳的時間擺脫夢境,想起塔克沒跟著我們,他三天前就跟運送人離開,向其他反抗團體通知安全之家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應該要在抵達第一個檢查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還在等他們的消息。
無論我有多希望他消失,當他離開,我還是不太舒坦,儘管他過去幾個禮拜來提供了諸多協助。他在身邊時,我至少可以看著他。現在我感覺像是閉著眼睛丟下刀子,只希望刀刃不會插入我的腳掌。
有人喃喃低語。可能是傑克,芝加哥反抗軍的倖存者之一。自從道德部隊炸毀隧道、我們差點遭到活埋後,他就一直不太對勁。他結實的身軀躺成大字形,擋在門口。另一個名叫老鼠的芝加哥反抗軍成員身形相當矮小,與傑克形成反比,他側身躺在傑克手腳範圍外。尚恩垂頭坐在破爛沙發上睡著了,雙手擱在膝頭,彷彿是在冥想。黎貝嘉蜷縮在他後頭的靠墊上,雙手拄著金屬支架,那是尚恩極想取代的位置。
雖然應該要跟傷者一起留在後方,但黎貝嘉堅持陪我們遠行。我們的步調對她來說很辛苦,可是她沒有抱怨。這點讓我擔心。感覺她是想要證明什麼。
另外兩個癱在用餐室的人也是芝加哥反抗軍的成員,他們沒有放棄希望,認為自己的家人沒有死在安全之家,而是順利逃脫,往南方逃跑。
屋外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我悄悄起身,繞過同伴,走向敞開的門。空氣中帶著濃厚的鹹味跟霉味,既新鮮又污濁。海洋在砂土堤岸外低語,波浪的起落,海邊的長長野草沙沙作響。我們駐紮的廢棄海邊渡假村名叫戴柏什麼的。「歡迎來到……」的標誌已經在數年前掉落,大概是某人拿來試槍的犧牲品;銅子彈把標誌右側打爛了。
「戴柏什麼村」也曾光鮮亮麗過;擋住貧困的柵門倒塌,不過還擱在燒毀的警衛亭旁。大戰時這裡曾經有過暴動,與許多比較富裕的社區命運相同。像復活節彩蛋般漂亮的海邊小屋,現在只剩空蕩蕩的廢墟:骨架往空中伸展,猶如燒黑的手指;墊高屋子的木架破舊不堪,上頭的屋子塌了一半,牆面糊上一層層鹽巴與沙粒,剩餘的窗戶用木板打上叉叉。附近有扇生鏽的百葉落地窗不斷拍打門框。
門階下傳來另一陣輕響。唯一可能的來源是比利,他拱著稜角分明的肩胛骨,手肘抱住膝蓋。他正在剝掉樹枝的外皮,似乎沒有注意到我。
我扯緊嘴角。如果輪到比利守夜,那代表天快亮了。他是來接查斯的班。可是查斯不在;他睡的浴巾丟在窗下,旁邊是裝著我們僅存財產的垃圾袋,裡面有兩個杯子、一把生鏽的餐刀、一把牙刷、幾條從廢墟裡撿出來的繩子。
我踮腳上前,坐在比利身旁,他幾乎連動都沒動。
「今晚很平靜?」我小心翼翼地問。他聳了聳一邊肩膀。我們從運送人卡車拿來的對講機,擱在比利用電工膠帶修補的靴子間,紅色電源燈閃爍不定。這台對講機是金屬製的,約有半個鞋盒大,不是很好拿取的規格,但訊號強度足以跟內陸聯繫。
至少我們覺得訊號夠強。接獲通訊時,紅光應該會變成綠色,但到現在為止綠燈還沒亮過。
我的視線回到比利身上。見到安全之家的廢墟後,他一直都很鎮靜。我知道他懷抱著華利斯還活著的希望,那位諾克斯韋爾反抗軍的前任首領更是比利的養父,他希望他是我們追蹤的倖存者的一員。但這是不可能的。華利斯已經在韋蘭旅館被燒死了。我們一起看著旅館倒塌。
「還剩一些罐頭燉肉。」我說。飢餓啃咬著我的胃。口糧愈來愈少。他皺了皺臉,繼續用指甲刮下樹皮,彷彿這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事情。
比利可以入侵道德部隊的主機。樹枝在他眼中才沒有這麼好玩。
「好吧。嗯。有人找到義大利麵,你——」
「我有說我餓了嗎?」
靠近前門的某人動了動手腳。比利垂頭,把叛逆的雙眼藏在油膩的髮絲間。
我們之間的沉默愈來愈緊繃。他失去至親;我知道那是怎樣的感覺。但我們可沒有殺了他的父親。
跟我們殺害哈柏的感覺不同。
儘管氣溫和煦,突如其來的寒意爬上我的皮膚。
「查斯離開多久了?」我問。
他又聳聳肩。我惱怒地起身,繞過屋子往海邊走,希望查斯是從這個方向離開。往右的野草比較稀疏,於是我挑了那邊,爬上沙丘,皺眉忍受小腿燒灼似的痛楚。我的雙腳成了戰場:芝加哥轟炸時的青紫黃色瘀痕,靴子磨出的水泡,腳踝上錢幣大小的腫包,碎石刺穿鞋跟,鑽進我的襪子。但是當我爬上堤頂時,所有的痛楚全都不見了。
整片星空映在黑暗大海上,沒有城市或基地的光害,如同鑽石般純淨明亮。海水與陸地的分界隱藏在陰影中,浪濤的低語持續不斷,好似心跳。
如此寬闊的光景將我吞噬。清涼新鮮的海風掃起我的髮梢,以前跟母親聊天時,她也是像這樣漫不經心地把玩我的頭髮。在這樣的時刻,在安靜無人的地方,我更想念她了。我閉起眼睛,感覺她幾乎就在我身邊。
「依舊沒有蹤跡。從昨天早上開始就沒再找到了。」我高聲說著,希望她聽得見。我不知道死後的世界是如何,只知道我希望可以聽見她的回應,一次就好。我讓腳跟往沙地裡轉。「沒有小超市那邊的通訊。查斯認為他們的無線電大概沒電了。我們離開前,它的電力已經見底。」我嘆息。「也沒有內陸組的消息。」
每個尋找倖存者的成員輪流扛著無線電,急著獲知其他反抗軍檢查哨的消息。沒有人敢說出真相:我們的通報組可能早就被逮到了。有人逃離安全之家的機率小之又小。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全都死了。
夢境在變。即使還睡著,我依然感覺得到。
過去,夢中有母親跟我手挽著手,同樣的蠻橫命運拖著我們行過荒涼的街道:家園、士兵和鮮血。總是佈滿鮮血。但現在有些不同。有什麼東西中斷了。像是無法解開的謎題一般煩擾著我。
柏油路依舊破裂。鄰近住家等在原地,那鬧鬼般的沉默,每扇前門都貼著宛如瘟疫警示一般的條款。頭頂上蒼白呆滯的天空往兩側延伸,我獨自一人。
母親應該在我身後的,但這回換成查斯登場。
他不是現在的查斯,是那個我多年前認識的男孩——蓬亂的黑髮,大膽好奇的八歲小孩眼眸,有點太小的牛仔褲底下皺巴巴的白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