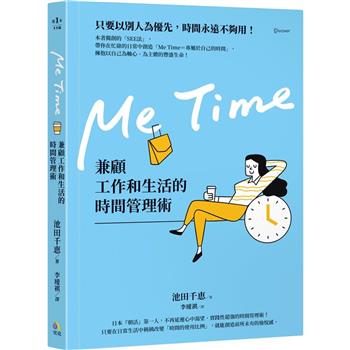傑森
岩佐明在轟隆作響的頭疼,以及光是眼睛聚焦便想嘔吐的強烈宿醉中醒來。
這麼嚴重的宿醉難得一見。他頭暈眼花地環視四周一圈。這才發現自己躺的不是床而是拼木地板。身上什麼也沒蓋,衣服也是昨晚的那套。看來他好像爛醉如泥就這麼躺在地上睡著了。仰望床鋪,妻子靜香早已不見蹤影,床鋪也整整齊齊。
「小靜。我宿醉很嚴重。小靜!」
岩佐躺著喊妻子,卻沒有回音。只要扯高嗓門就感到氣悶心煩。他閉上嘴與作嘔感戰鬥,稍微扭頭看手上還戴著的手表。上午九點半。幸好今天只有下午二點的課。在那之前應該多少會變得舒服一點。
洗手間傳來水聲。妻子八成在那邊盥洗。岩佐撐著暈眩的腦袋爬到走廊。
「小靜,妳在哪裡?小靜,對不起。」
在洗手間洗臉的,是昨晚一起喝酒的友人今川。岩佐覺得被人看見自己怕老婆的糗樣不免有點羞窘。
「噢,你在我家過夜啊?」
「啊,不。我現在馬上要走了。」
今川一看到岩佐就慌忙把眼轉開,拿毛巾擦臉。
「你慢慢來。公司那邊,應該沒關係吧。你不是說過今天要直接去拜訪客戶。」
「那可不行。我該走了,改天見。」
今川也不正眼瞧他便匆忙戴上金屬框眼鏡,抓起放在一旁的西裝外套。
「先吃點東西再走嘛。我馬上叫靜香準備。」
「那怎麼好意思。先走了,我再打電話給你。」
今川簡直像逃命似地直接衝向玄關,在公寓狹小的門口慌慌張張穿上沒擦的鞋子。今川的西裝外套和褲子都皺巴巴的,可見他昨晚應該也是倒頭就睡。
「喂,今川。」
倚著走廊牆壁,岩佐發話。
「幹嘛?」今川轉過身,但他的眼神卻彷彿看到什麼可怕的東西。
「我昨晚是怎麼回來的?」
「你不記得了嗎?」
「嗯。完全不記得。」
「你的確喝得爛醉。我走了,再見。」
今川彷彿害怕被人抓住的貓咪,一溜煙就開門逃走了。岩佐在走廊癱坐,開始搜尋記憶之壺試圖回想昨夜的事。
「我來大學附近辦公事。你接下來有空嗎?」他記得研究所時代的友人今川打電話到研究室來,於是一起去大學附近的居酒屋喝酒。
今川自研究所畢業後任職出版社,是專門出版學術書籍的部門。二人聊工作聊得起勁喝了不少酒,之後,又去了一家酒廊。到此為止他還有印象。
但,後來去哪做了什麼?自己又是怎麼回到家的?記憶完全斷線。唯一能確定的是,他喝了比平時更多的酒。因為很久沒見到推心置腹的好友今川,岩佐喝了酒立時心情爽快,不知不覺喝得比平時更凶。
「我的工作是應付大學女生,所以不能掉以輕心。但是偶爾放鬆一下應該不為過吧,今川。我可要一醉方休喔。」
記得自己好像一直那樣得意忘形自說自話。所以,才會罕見地爛醉如泥。想必給今川和新婚妻子都添了不少麻煩。妻子才二十六歲。在她面前露出醜態很可恥。岩佐朝著盡頭的客廳慢慢走過走廊。
「小靜。我宿醉很嚴重。」
沒有回音。妻子一大早就上哪去了?難道是去倒垃圾了?岩佐走近冰箱想喝冰水,這才發現冰箱門上用吸鐵石貼著便條紙。
「沒想到你是那種人。我要回娘家一陣子。別來找我。 靜香」
因宿醉而暈眩的腦袋,彷彿被人從背後拿大鐵鎚狠狠敲擊。該不會是今川惡作劇吧?岩佐一再重讀。但,那分明是妻子的筆跡。
昨晚,自己到底對妻子做了什麼?岩佐聽著冰箱馬達的嗡嗡聲,無力地坐倒在地。
去大學之前,他一再打電話到妻子位於群馬縣的娘家卻無人接聽。那地方離東京不遠為何到現在還沒抵達?她該不會離家出走了吧?不安的岩佐再也待不住,急忙打電話到今川的出版社。
「我是岩佐。」
「噢,今早不好意思。」
「那個,靜香離家了,我想問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是喔。」今川格外冷靜。「她會去哪裡我可不知道。」
「不是,那個我知道。那不重要。我想問的不是那個,我不懂的是她為何要走。」
一瞬間,出現倒抽冷氣的沉默,最後今川斷然表示:
「你放心,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你要相信我。」
「你在說什麼?」
「抱歉,我要去開會了。」
今川沒回答,匆匆掛斷電話。
岩佐想起這種好像缺了關鍵部分無處施力的感覺,早在遙遠的學生時代已有數次經驗。那同樣是在純男性的飲酒場合。到了早上,嚴重宿醉令他失去前晚的記憶,而一起喝酒的朋友們,全都鬼鬼祟祟不肯正面直視岩佐。
雖非頻繁發生,但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昨晚,自己又對妻子做了什麼?岩佐頻頻側首不解,有生以來頭一次被黑壓壓的不安襲擊。喝醉之後自己不曉得變成怎樣的人但別人卻知道,想到這裡不免有種不自在的不安。
岩佐一步入教室,年輕女孩那種甜甜的洗髮精香氣及雨水淋濕T恤的酸味混在一起的特有體臭便撲面籠罩著他。
宿醉的頭疼與反胃,現在變成突然出現的胃痛。幸好嘔吐感已消失。岩佐無意識地撫摸胃部。否則說不定已忍不住這種氣味吐出來了。
二年前初執教鞭時,與其說被一群大學女生盯著不放嚇得不知所措,其實是被這種氣味刺激得發暈連自己說了什麼都不記得。
岩佐站在黑板前,倏然仰望坐在大階梯教室後方的三、四十名女學生。大家都露出無意味的竊笑互相拿手肘捅來捅去,一邊俯視三十一歲的岩佐。
這所女子大學有很多家境較富裕的子女,頭腦也聰明,但最出名的是花枝招展的女孩特別多。即便已習慣氣味,至今還是動不動就會心虛。彷彿看穿他的心虛,「他好像很不舒服。」上方飄下來一個聲音說。
「宿醉,絕對是宿醉。」某人囁嚅,周遭響起小小的笑聲。
岩佐一驚。他開始感到不安,該不會,自己昨晚喝多的糗事全被學生知道了吧。他很後悔不該在大學旁邊喝酒。頓時感到胃痛,不禁倒抽一口氣。他調整一下呼吸等待疼痛平息之際。
「對不起我遲到了。」
沙啞含糊的聲音響起,只見一名不修邊幅的女學生一溜煙鑽進教室。她想走台階到後面坐,但那裡已無空座位,只好死心地挨在空蕩蕩的前排座位邊上坐下。因她引去大家的注意力而暗鬆一口氣的岩佐,假裝檢視點名簿。
「呃,妳叫什麼名字?」
他當然知道對方的名字。澤登紀美子。此人乃遲到慣犯,是個有點跟不上大家的劣等生。
「我是澤登。」
「噢,是是是。是有這麼一號人物。」
岩佐壞心眼的反應令學生們偷笑。岩佐自己,並不覺得是在欺負弱小。岩佐看到澤登就無法克制滿心不快。因為,澤登無論是成績或外表都配不上這所女子大學。
澤登或許連一個好友都沒有,當她遲到時教室只會蔓延冷笑的氣氛。但,澤登自己似乎不以為意,慢吞吞地從破舊的背包取出教科書。
「那麼,看來人都到齊了,我們開始上課吧。好不好?」
岩佐用盡力氣,如同電視現場節目那樣一喊,「好~」學生們好似聽話的幼稚園小朋友齊聲回答,突然開始竊竊私語。那是一如往常的上課風景。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生鏽的心:桐野夏生極致短篇傑作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生鏽的心:桐野夏生極致短篇傑作選 作者:桐野夏生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5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推理小說 |
$ 264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生鏽的心:桐野夏生極致短篇傑作選
出道數十年 橫掃日本文壇各大獎項第一人
江戶川亂步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直木賞、泉鏡花文學賞、柴田鍊三郎賞、婦女公論文藝賞、谷崎潤一郎賞、紫式部文學賞、島清戀愛文學賞、讀賣文學賞。
社會派寫實小說女王
桐野夏生 首本極致短篇傑作選
這只是人性靜靜的瘋狂,
沒有犯罪,只多了一點執念。
就像月球的背面、門上的鏽斑一般。
幽暗、輕淺,不注意看是可以視而不見的,
但只要知道它在那裡便如同血色烙印記憶,永生難忘。
作者簡介:
桐野夏生
日本寫實社會小說女性代表作家。出道至今幾乎囊括日本重要文學獎項。她筆下的長篇小說,剖析人心針砭時事,力透紙背。短篇小說幽闇晦明雖刻意隱藏,卻因某種偶然的契機,從日常生活的龜裂處,自然曝露出人性的黑暗面。桐野夏生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生鏽的心》收錄的六篇作品,共同描寫的就是這種人性靜靜的瘋狂。日本文學評論家甚至以匹敵於日本社會推理巨匠松本清張的高明手腕來形容桐野夏生的短篇作品。
1951年出生。1993年江戶川亂步賞《濡溼臉頰的雨》、1998年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OUT主婦殺人事件》、1999年直木賞《柔嫩的臉頰》、2003年泉鏡花文學賞《異常》、2004年柴田鍊三郎賞《殘虐記》、2005年婦女公論文藝賞《燃燒的靈魂》、2008年谷崎潤一郎賞《東京島》、2009年紫式部文學賞《女神記》、2010年島清戀愛文學賞、2011年讀賣文學賞《有什麼》。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
章節試閱
傑森
岩佐明在轟隆作響的頭疼,以及光是眼睛聚焦便想嘔吐的強烈宿醉中醒來。
這麼嚴重的宿醉難得一見。他頭暈眼花地環視四周一圈。這才發現自己躺的不是床而是拼木地板。身上什麼也沒蓋,衣服也是昨晚的那套。看來他好像爛醉如泥就這麼躺在地上睡著了。仰望床鋪,妻子靜香早已不見蹤影,床鋪也整整齊齊。
「小靜。我宿醉很嚴重。小靜!」
岩佐躺著喊妻子,卻沒有回音。只要扯高嗓門就感到氣悶心煩。他閉上嘴與作嘔感戰鬥,稍微扭頭看手上還戴著的手表。上午九點半。幸好今天只有下午二點的課。在那之前應該多少會變得舒服...
岩佐明在轟隆作響的頭疼,以及光是眼睛聚焦便想嘔吐的強烈宿醉中醒來。
這麼嚴重的宿醉難得一見。他頭暈眼花地環視四周一圈。這才發現自己躺的不是床而是拼木地板。身上什麼也沒蓋,衣服也是昨晚的那套。看來他好像爛醉如泥就這麼躺在地上睡著了。仰望床鋪,妻子靜香早已不見蹤影,床鋪也整整齊齊。
「小靜。我宿醉很嚴重。小靜!」
岩佐躺著喊妻子,卻沒有回音。只要扯高嗓門就感到氣悶心煩。他閉上嘴與作嘔感戰鬥,稍微扭頭看手上還戴著的手表。上午九點半。幸好今天只有下午二點的課。在那之前應該多少會變得舒服...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桐野夏生
- 出版社: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8 ISBN/ISSN:978986572329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15/05/17
2015/05/17 2014/12/31
2014/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