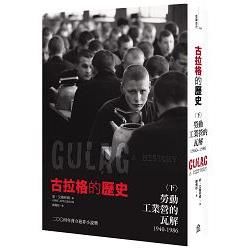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讓悲劇不再發生』這樣的陳腔濫調,而是因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悲劇一定會再度發生。極權思想過去吸引了很多人,未來也會。古拉格歷史上的每段遭遇、每部回憶錄和每份檔案都是一塊拼圖、一部分的解釋。沒有這些資料,有一天醒來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艾普邦姆
古拉格,最大的蘇聯集中營措施,關押了數百萬政治與刑事犯。這個壓制與懲罰體系是用來恐嚇整個社會,蘇聯共產黨最壞的一面全體現在古拉格。這本歷史著作專精、頗受好評,艾普邦姆讓世人首度認識古拉格的完整面貌。它最初起源於俄國大革命,史達林執政時擴張它的規模,直到開放改革時代才崩解。
艾普邦姆深入地重新創造集中營生活的樣貌,並且與整個蘇聯歷史的發展相連結。出版後沒多久,讀者專家一致同意,《古拉格的歷史》是眾人期盼已久、是知識界的里程碑。想要瞭解二十世紀的歷史,應將本書列入必讀書單。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古拉格的歷史(下):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至一九八六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07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史地 |
$ 356 |
政治/法律/軍事 |
$ 356 |
人文歷史 |
$ 383 |
社會人文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世界國別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古拉格的歷史(下):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至一九八六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安‧艾普邦姆
《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及編輯委員。耶魯大學畢業後獲得馬歇爾獎學金。曾任《觀察家》週刊的海外編輯助理、《經濟學人》的華沙特派員、線上雜誌《Slate》專欄作家,並為多家英國報紙撰稿。她的許多文章也登上《紐約書評》、《外交事務》、《華爾街日報》等報刊。目前她與丈夫和兒女定居在華府。
譯者簡介
謝佩妏
專職譯者。清大外文所畢業。
安‧艾普邦姆
《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及編輯委員。耶魯大學畢業後獲得馬歇爾獎學金。曾任《觀察家》週刊的海外編輯助理、《經濟學人》的華沙特派員、線上雜誌《Slate》專欄作家,並為多家英國報紙撰稿。她的許多文章也登上《紐約書評》、《外交事務》、《華爾街日報》等報刊。目前她與丈夫和兒女定居在華府。
譯者簡介
謝佩妏
專職譯者。清大外文所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