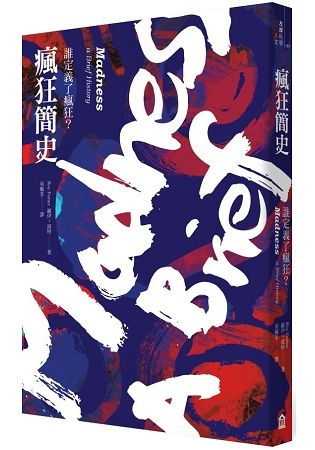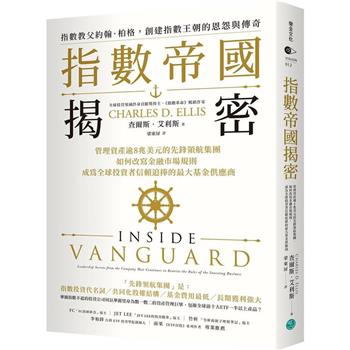導讀
瘋狂中的理性
啊!一半有理,一半不正經!瘋狂中有理性!——莎士比亞,《李爾王》
「著作等身」一詞不足以形容羅伊‧波特在醫療史、精神醫學史以及十八世紀社會思想史方面的成就。就精神醫學史的領域而言,他曾關切過的議題也相當多樣:道德治療、療養院史、神經衰弱、歇斯底里、對傅柯的瘋癲史之評價、瘋狂者的觀點、精神醫學史……等等。除了出版二十多本專書外,精力同見聞過人的波特亦曾主編上百件的出版品及若干專業刊物。這本於二○○二年年初波特去世幾個星期前甫問世、如今被譯成中文的《瘋狂簡史》,壓縮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得。在結構上,此書以主題的方式呈現,介紹西方歷史中的瘋狂與瘋狂者,由於將讀者群設定為非專業人士,在文字與內容上力求深入淺出。然而表面上看似淺顯且文雅的章節,不但表達出波特個人對瘋狂相關課題的興趣,也不著痕跡地回顧了當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並且點出瘋狂史未來的研究導向。
要以極短的篇幅書寫西方兩千年來的瘋狂史必定有所取捨。拋開精神醫學家所代表的輝格進步史觀,以及反精神醫學運動者將精神疾病視為迷思這兩種主要取徑,波特主要關切的是三個主題:在歷史中,哪些人被認定為瘋狂?在當時的認知中,他們瘋狂的起因為何?而社會又是如何處置這些瘋狂的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波特感興趣的不是「是否」的問題:他並非想對過去言行偏差的人進行一種回溯性的診斷,以釐清瘋狂的本質;他也無意於單純排列出瘋狂者在歷史中遺留下的軌跡。他所在意的是「為何」以及「如何」的問題:認定誰是瘋狂的人始終是一種社會的行為,具有特殊的社會意涵,並且造成引人深慮的社會效應。
波特花了相當的功夫勾勒西方歷史中瘋狂者所扮演的不同面貌,或者被社會所賦予的不同身分。藉此,他不僅鋪陳了瘋狂的多樣性,也描繪出瘋狂者身處的社會各自具有的景象。許久以來,瘋狂與天才間只有一線之隔。狂亂的想像力激發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在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伊拉斯謨式的愚人或莎士比亞劇中的弄臣是唯一清醒的人,常有警語,揭露社會的紛擾與不義。在波特所熟稔的十八世紀,那些被拘禁在瘋人院、並且成為公開奇觀展示品的瘋狂者,其實點出喪失理智的是外在的世界。瘋人院裡的瘋子遠比外面正常的人更自由。而在世俗化、理性風潮高漲之後,瘋子與癲人昔日的放浪形骸又被化約成病理現象。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醫藥進步,對波特而言不盡然具有正面的意義。社會始終區別出一些行為乖離的分子,強調這些分子的差異,以維持社會虛幻的整體性。而醫學經常不自省地參與這項將瘋狂者污名化的計畫。換言之,此時的臨床診斷本身變成了一種重整社會次序的行為。
在這個意義上,對疾病所擁有的社會與文化價值提出個人看法的波特,與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的論調不同。在《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從自己罹病的經驗出發,細數沉澱在疾病之上的眾多隱喻,包括結核病與癌症在內的患者或被強加、或自己欣然充任的身分。在其論述中,疾病甚至變成人格的一部分,成為界定個體性的區辨特質。藉由陳述這些對她而言不當、過多的象徵,桑塔格認為應該回到疾病本身。桑塔格強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隱喻式的思考方式,但應當力圖跳脫一些令人窒息的隱喻。在桑塔格這個類似解魅的計畫中,醫學扮演重要的角色。明晰的醫學知識為我們揭露了真相,使得所有的象徵變得多餘。桑塔格這種反對詮釋、意圖還原事物透明性的作法,當然與波特藉由瘋狂者的認定與瘋狂者所受到的待遇來討論社會文化史的作法有所出入。波特主張瘋狂者的行為只有在其身處的社會才能理解;甚至,文明社會本身便是失常的始作俑者。因此,當社會在判定一個人究竟是否神智清明時,這個舉動本身便是可議的。根據同一個邏輯,作為技術官僚的醫師本身並不站在任何智識或道德的高處。
波特這個態度也出現在他對整個瘋狂世俗化過程的見解上。西方文化一直存在以超自然現象來理解瘋狂的作法,這個走向在基督教興起、並成為主流思想之後變得更為明顯。古希臘時期所推崇的理性與自然主義式的思考方式,現在被凡人對上帝的崇敬與虔信所取代。先知與女巫成為瘋狂的兩種極端面貌,一者因被聖靈充滿而受人景仰,另一者因與魔鬼私通而被宗教審判、公開處決。瘋狂的世俗化所帶來的結果也不盡然都是好的。正如痲瘋病患的位置在古典時期被非理性的人所取代(傅柯語),女巫的位置隨著自然主義思考模式的興起也被新的女巫──社會上的不良分子、遊民、乞丐等──所填補。在列舉精神醫學興起的過程及獲得的成就時,波特也不忘保持史家的距離,將醫學的發展放在歷史脈絡下省思,點出科學與醫學發展的盲點,以及社會對人類理性過於天真的期望。例如,皮內爾宣揚的道德治療促使社會對療養院抱持高度期望。療養院成為地上的樂園,啟蒙人道主義與進步精神的典範。但在精神醫學專業化的考量下,大量興建的精神療養機構卻造成了問題。精神醫學專業擴張的同時,無法擔負隨著病人人口增加而來的責任,療養院的功能從治療,變成收容、監管。當療養院成為處置瘋狂者的固定機構與方式,療養院的高牆成為「正常人」與「不正常的人」的分隔線。波特反覆用二十世紀中納粹德國處置精神病患與猶太人的作法為例,質疑單面向的思考方式。在一個成千上萬的精神病患被送進毒氣室的時代,我們應當對精神醫學所宣稱的成就與突破抱持更審慎的態度。雖然波特希望擱置精神醫學專業與反精神醫學運動之間數十年來的爭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討論瘋狂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其以歷史書寫表達對瘋狂者的人道關切這個面向,還是相當鮮明。
在醫學史與精神醫學史的研究領域中,波特最常給人的聯想,便是書寫另類的醫療史。除了關切身體與性意識的歷史之外,他最著名的是鼓吹從病患的觀點出發,讓病患自己發言。醫學成為獨立學門之後,常以現在的成就來認識自己的歷史,一再強調現代醫學知識與持續的技術突破、外科手術創新的英雄與先驅、擺脫先前民俗療法的陰影等等。這種醫學史的主角總是醫生,以及他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技術。不過,波特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中,許多時候病患求助的是家庭與社群的協助,或自力救濟。此外,醫療行為所牽涉的不僅是醫學理論與醫生的實際作為,還包括了病患,也就是治療關係的互動。當然,醫療行為除了與醫病兩造有關,更涉及了家庭、社群等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成規。但在以醫生為主角的醫學史中,我們無法理解一般人如何看待健康與疾病,以及他們如何面對醫病關係。波特因此主張「把患者找回來」,以患者或病人的故事為主題,而不是一味地描述醫生提出什麼理論、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樣傑出的成就。波特所隸屬的新醫學史與文化家傳統,不再用現代的精神醫學分類範疇,或當前的主流文化價值去解讀瘋狂,發現它的內在邏輯,或深層的意涵。而是拉開距離,看歷史上的瘋狂者,他們的話語帶有什麼意義,這些瘋狂者如何面對、訴說、處理他們的處境、衝動、激情與記憶。波特試圖去看這些被社會所驅逐的人如何與社會權力的擁有者抗衡。瘋狂者的妄想、精神醫學的神話,以及社會的意識型態,共同織成一個有意義的網絡。波特的這種看法讓我們明白,瘋狂者的話語與行為並非僅由醫學論述與社會價值所決定,他們的言行也影響了他們身邊的人;或更正確地說,即便是瘋狂的人,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瘋狂者所說的一切,醫生所宣稱客觀的診斷與治療,必須放回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方能理解。
在這個將絕大多數偏離常規、對社會造成實際與潛在危險的行為病理化的時代,波特用社會史的角度切入瘋狂的歷史毋寧是十分重要的。如同他反覆在歷史細節上質疑、不過也受教許多的傅柯一樣,波特認為瘋狂並非單純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只要醫生便可充分說明並處理。不過,在這個意義上,波特不是反醫學、反科學的,只是歷史書寫帶出的寬闊視野,以及文化和知識的廣度,或許讓他跳脫出短視的盲點,進而造成一些改變。就這點而言,波特成了他在自己的《啟蒙》(一九九O)一書中所描述的啟蒙哲人:「筆或許不比劍有力,但啟蒙的文字的確成為危險的武器。以鵝毛筆當箭的那些人並非是專制君主前卑躬屈膝的傳聲筒,而是強盜,那些自此確保了『自由社會』知識無政府狀態的知識土匪。」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