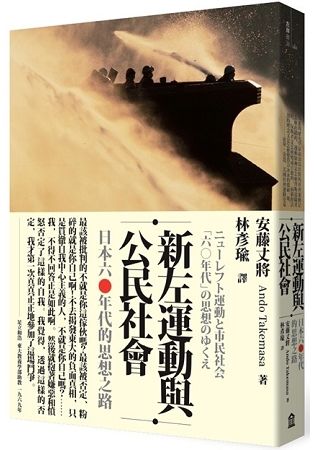這是一段關於日本「狂飆年代」的故事:
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結果卻失敗了。
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
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結果卻失敗了。
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
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六○年代安保鬥爭、學生運動、反戰運動等「新左運動」(New Left Movement)為中心,總覽五○到七○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新左論述的核心思想是所謂「日常性的自我變革」,先是從思想形成之前的戰後民主運動、安保鬥爭、歸鄉運動當中,逐漸建立「自我反省」的思想基礎。等到日本進入高度成長時期,富裕的物質條件使得運動者開始注意到日常生活「被規訓化」的問題,為了有效實踐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運動者積極地參與非暴力的直接行動。然而直接行動遭到警察強力的壓制,使得運動的動員能力大減,運動內部發生的暴力事件更是讓大眾失去對運動的支持。在「社會變革」的理想越來越困難之際,運動開始傾向「自我變革」這一方。到了1970年代前期,當許多人絕望地離開運動之後,留在運動的人只得思考要如何才不至於放棄一切,而他們找到的方法是發展學習運動、到公害現場向當地的「生活民」學習、甚至是去到菲律賓與種植香蕉的農場工人合作改善農業環境。
那麼,新左運動究竟為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什麼遺產呢?第一,是「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成了「公民力量」的泉源。而這個思想,在一九七〇年代新左運動動員能力衰退之後,強化了運動「自我反省」的性質,雖然人們參與運動的門檻變高了,但這樣的性質也同時傳播到各式各樣草根公民運動的場域,成為支持運動的基底。第二,運動的體制化相當受限。和「政治變革」切割的「自我變革」論述,使運動者對參與體制內政治一事相當猶豫。而且,在與警察的紛爭中所產生的「過激派」新左運動形象,也成為都市和農村的運動之間建立連帶的障礙。因此,新左運動並沒有辦法把「新政治」帶入國家內政之中。第三,是對「直接行動」的厭惡感越來越普遍。新左運動的論述之中,雖然把直接行動視為「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評估指標,但是「直接行動等同於暴力」這個形象被主流媒體形塑出來之後,社會中普遍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從而使得直接行動作為人民的一種政治表達手段,就這樣遭到剝奪了。
那麼,曾經狂飆的新左運動,對現今的日本公民社會難道一點影響也沒有嗎?作者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公民社會出現了快速的變化,社會運動的性質也與過往大不相同。作者注意到「反貧困運動」中,運動者致力於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放出來,以及在「志工文化」中強調做志工這件事情很快樂,一方面說明了越來越多人支持「自我解放」的論述之外,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自我反省」的思想,已經不像過往那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共鳴了。
在這個意義下,新左運動說不定可以說是已經成為歷史了。然而三一一福島核災的發生,讓作者重新反思新左運動所標舉的核心價值:「在大都市過著富裕的、像人一樣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是坐在員工椅上面對激烈競爭的生活方式。工作占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然後把賺來的錢花在超出必要以外的消費之上的生活方式。像核廢料處理那樣,讓那些地方或外國的弱勢者去支付我們浪費的代價的生活方式。我們真的必須守護這樣的生活方式嗎?日本國內那些想要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人所期待的生活,難道就是這樣的生活嗎?
在不得不試圖創造人類與自然之間更溫柔的生活方式的今日,新左運動中所謂的「日常性的自我變革」一詞,所點出的「改變生活方式」這個問題,就會慢慢浮現出來。
名人推薦
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梅森直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