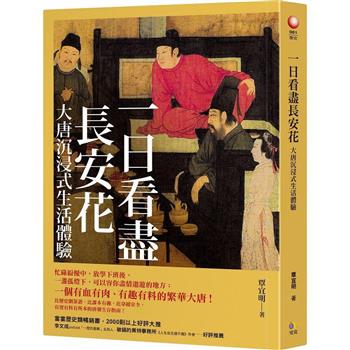書摘/試閱那是一個炎熱的早晨。太陽很大,在這個南緯五度、貼近赤道的太平洋小島,除了陰雨時,沒有一天不是烈日當空。我剛在美國的大學修畢人類學博士班課程,通過資格考和研究計畫,選擇了大洋洲的一個小社群──所羅門群島的Langalanga人──作為研究的對象。我在Lan¬galanga的一個海邊村落安頓下來,準備進行看起來像是很「傳統」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在沒水沒電沒瓦斯沒電話(嘿,當然也沒網路!)的偏遠小村落,與當地人一同生活一年以上,學習當地語言,研究當地異文化,作為博士論文的基礎。
剛住進村子沒幾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展開初步調查了。戴了棒球帽遮陽,入境隨俗地穿了長裙,帶著筆記本和相機,開始一戶一戶地走訪。濕熱的空氣中,全身都是汗臭,而為防瘧蚊和毒辣的太陽,不斷噴灑防蚊藥和塗抹防曬油,與汗水混合成怪異的味道跟揮之不去的黏膩,然而我的「氣味」和當地人帶椰油成分的汗水味顯然格格不入。
我的出現在村中是項大新聞,雖然很多人在前日的教會禮拜時見過我了,然近距離的接觸還是頭一遭。沿著村中主要道路走著,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小孩跟在我身邊。比較害羞的, 保持距離好奇地瞧;膽子較大的,則跑過來「順道」摸一下我的衣服和手臂,然後咯咯笑著飛奔而去。我停下來,蹲下身,想和他們打招呼,拉近距離。一個小女孩靠過來摸了我的頭髮,發現「沒事」,馬上有一群小孩跟進,蜂擁而上用小手感受我的臉、手臂和任何可以摸到的地方。我覺得自己像是誤闖小人國的格利弗,楞楞地不知如何反應。這些肢體接觸讓孩子們開心極了,有幾個趕快跑去通知其他小孩也過來玩,他們一面狂奔一面高喊著:「Waet¬man! Waetman!」
我皺了皺眉頭,waetman?
「Waetman! Waetman!」孩子們更大聲地呼喊,對這個稱呼非常興奮。
我忽然聽懂了,他們講的「waetman」是所羅門洋涇濱(Solomon pijin),那是有數十種不同語言的所羅門群島居民,在殖民時期發展出的通用語言。洋涇濱使用當地南島語的文法,融合許多本土化發音的英文字彙。「waetman」源自英文的「white man」,意思是「白人」。
我試著用洋涇濱加上比手畫腳,想跟他們解釋:「我不是waetman(白人),我叫佩宜。」
然而孩子們不懂洋涇濱,只懂得洋涇濱裡的名詞「waetman」,繼續開心地喊著:「Waetman! Waetman!」
顯然是徒勞,我放棄解釋,繼續往前走。前方有個小女孩,約莫五、六歲,抱著她稚齡的小弟弟;小寶寶睜著大眼睛,又好奇又膽怯。我走上前去,想要逗逗他,誰知道我一靠近,他就大哭了起來。
只聽到圍觀的小朋友們更興奮地呼喊,還沒學當地話的我完全聽不懂,只聽到「waet¬man」不斷出現在他們彼此的對話中,我猜大概是在講我這個「白人」弄哭了小寶寶的「事件」吧?
我無奈地匆匆離去,儘量別再弄哭小孩。然而這樣的場景幾乎天天上演,也算不清到底嚇哭多少小孩了。我安慰自己,可能因為我是陌生人,小寶寶才會哭,不是因為我的膚色。往好處想,我為更多小孩提供娛樂與歡笑,不是嗎?
然而小孩子一直喊我「waetman」,還是讓我耿耿於懷。我實在無法想像自己被歸類為「white」(白皮膚/白人),況且,嚴格說來,我根本不是「man」(男人),我是個「woman」(女人)!
有天我把自己的疑惑提出來,與教我當地話(Langalanga語)的老師塞勒斯討論。他只淡淡地說:「小孩子嘛。」但我還是困惑。小孩會以「waetman」一詞稱呼我,最直覺的解釋為:或許那是他們對外人的描述方式,以明顯的膚色差別來標誌。雖然所羅門群島也有東方人──幾代以來從廣東移民的雜貨店老闆、日本商人和青年志工,以及馬來西亞華裔的伐木公司人員。但超過一世紀殖民經驗的歷史中,英國、澳洲、歐洲,甚至美國的白人人數最多、影響力最大,「waetman」一詞大概也是由此而來的吧?然而,當地人不區分黃種人與白種人嗎?
塞勒斯認為,小孩子不懂,但大人都清楚這些膚色的差異,並未混為一談。
「但是有特別的詞來稱呼我這樣膚色的人嗎?」我問。
似乎沒有。後來塞勒斯也提到,有些所羅門群島的族群,使用「araikwao」一詞來指稱外人,主要以歐洲人、白人為主,但有時也廣義包含了亞洲人。我要研究的Langalanga人倒是沒有這樣的慣用詞彙,而是採用洋涇濱的「waetman」一詞,因此當地小孩才會這樣稱呼我。
這個回答很有意思,似乎也符合過去在文獻中看到的說法。對「外來者」以特殊標誌來統稱、分類,在南島語族中很常見,例如台灣原住民常稱漢人為「白浪」(據說源自福佬語的「壞人」),而大洋洲許多民族也有類似的例子。因此waetman/white man的重點可能不是「white」,而是非我族類的「他者」(the Other),而且是有政經權力優勢的外來者。一個初入田野的人類學者被如此歸類,大概無法避免吧?
而實際上,我自己在田野的第一天也曾強烈意識到膚色差異。那天晚上我到教堂參加安息日開始的禮拜,在昏暗的燈光下,赫然發現我的膚色和當地人對比,竟是那麼明顯地白!我驚訝地發現彼此的膚色差異如此鮮明,還特別在田野日誌中記錄了那一刻的震撼(shock)──原來我的不同是那麼地刺眼!光是膚色的對比就給我那樣強烈的感受,其實,我不也依照自己的文化慣習,以膚色差異來做第一層認知?
既然當地人所說的「白人」是他們分類人群的一種方式,而膚色其實也是我的文化包袱中認知他人的一種系統,那麼我為何對自己被標誌為「白人」還是覺得不太舒服?我想了一下,或許是在美國念書幾年後,特別覺得用膚色來標誌一個人的「類別」,是政治不正確吧?尤其是當那樣的分類同時又隱含、對應了政經的權力位階的時候,格外觸動許多人的神經。
「白人」的稱呼讓我頭一次省思Langalanga、還有我熟悉的台灣與美國文化中的人群分類概念與政治後,這個問題就暫時放下了。然而,這樣的「定位」,對我這個懷抱熱情且天真的人類學者,還是不免耿耿於懷,總覺得是不斷被提醒的階級身分差異,如同原罪一般整天無奈地揹著。傳統人類學的主張,認為田野工作是透過學習當地語言、長期與當地人一同生活,慢慢進階理解當地文化,甚至「成為當地人」(becoming natives)。如果我只是個「白人」,那就很難真正進入當地文化脈絡去思考,也不可能做出好的人類學研究。這樣的「理想」在近年受到許多批評,我也不再天真地認為透過一年多的田野工作有「成為當地人」的可能;但或許儘量「去白人化」是我該努力的目標吧?當下我也只能朝著那漫長而忐忑的路走下去,看著辦了。
雖然不再超級在意「白人」的稱呼,但那樣的刻板印象卻是我每天生活直接面對的。從進入村子的第一天開始,我是誰──當地人如何看我,而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是田野的實際課題。我翻了田野日誌,回想起數天前──經過幾番波折,連繫、等待,終於到了搬入村中的日子。我被安排暫住於牧師家,那是村中最「高級」的住宅,為南島語族常見的杆欄式建築。一樓充當幼稚園,二樓是居住空間,包括客廳和幾間臥房,因為大兒子在外地工作,有一間空房能租給我使用;牧師夫婦英文流利,也解決了我初期語言不通的問題。剛把行李搬進去,對面鄰家的年輕媳婦就過來打招呼,熱情地詢問。我很開心地接受她的善意,羅莎琳是村中少數能自在講洋涇濱的女人,我在田野前自修過所羅門洋涇濱,因此基本溝通無礙。
聊沒幾句,她說:「你衣服拿給我洗。」
我楞了一下,不確定這句話的意思。
她解釋:「我可以幫你洗衣服。」
我急忙說:「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
她再度表示沒關係,讓她洗就好。我還是推辭了,覺得很尷尬。在所羅門群島僱工很便宜,從殖民時代開始,當地人就常受僱於英國、澳洲等外國人,擔任打掃、煮飯、園藝等工作,同時,廣東移民來的商人很快地都開店當老闆,僱用當地人當店員。「waetman」一詞在洋涇濱裡有個同義語,是「mista」,源自英文的「Mister」(先生),即反映了殖民的權力對等關係──白人被尊稱為「Mister」或「boss」(老闆),而當地人則是「house boy」或「house girl」(男傭/女傭)。這樣的權力結構在所羅門群島於一九七八年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後,依舊難以改變。在城裡,人口比例低的非原住民普遍經濟階級高於原住民,幾乎每戶都聘了當地人幫傭。或許羅莎琳因此覺得我也會請個「house girl」吧?
然而我對這樣的階級結構感到很不舒服,同時,作為人類學者、從事田野工作,不就是要和當地人過一樣的生活,才能進入當地的脈絡?因此我壓根不考慮請人洗衣服,很快轉移話題,免得不好意思。
我希望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因此決定搭伙,房東家吃什麼,我就跟著吃。午餐時間到了,牧師太太煮了白米飯,還有泡麵。當地賣的泡麵是最陽春的那種,只附了一小包調味料,有幾種口味選擇。她另外還炸了地瓜條,我超愛吃炸地瓜薯條,聞到味道食指大動,但發現白飯和泡麵是給我和牧師太太的,炸薯條則是給牧師讀小學的兒子和女兒。面對看來有點奇怪的一餐,我不太確定要怎麼吃──是要扒白飯,還是吃泡麵?人類學者學習能力最強,所以我按捺著,想先看狀況再拷貝「正確禮儀」,很快發現泡麵是「一道菜」,用來配飯吃。
當下覺得這真是非常有「創意」的吃法,但不合我的口味,只能客氣禮貌地吃一些,同時看著薯條流口水。我發現小朋友似乎很想吃我的那份,就建議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於是我也吃到了薯條,覺得很欣慰。接下來好幾餐,牧師太太還是煮了白飯和泡麵給我,我感到頗為難,雖想當個不挑嘴的好客人,但又很納悶──為何每餐都吃這個?後來我還是忍不住探探牧師太太的想法,終於搞懂了──他們以為「白人」一定不喜歡當地食物,地瓜很廉價,而白飯和泡麵都是進口食品,牧師太太為了特別照顧我,於是每天準備「大餐」伺候。我趕快解釋,只要照平常煮就好了,不要麻煩,我什麼都可以吃,食量也不大。
因為沒有自來水,這裡家家戶戶都在屋簷下擺了盛接雨水的容器,一般多是原本用來裝石油的大鐵桶。不同的容器乾淨程度不同,最乾淨的雨水用來煮飯洗碗,其次用來沖澡和洗衣。傍晚時我提了桶水快快沖了冷水澡,然後問牧師太太在何處洗衣。牧師家的洗衣用水就在門前的方形廢棄冰櫃中,村子裡沒有電,冰櫃是他們先前住在城裡時用過的。於是我把髒衣服和肥皂、刷子放在菜市場買來的藤編籃中,開始在門前洗衣──其實也不過是內衣和T恤、長裙罷了。不一會聽到大聲笑鬧和嘰哩呱啦的聲音,抬頭一看,屋前路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正在「參觀」我洗衣服!婦女們指指點點,興奮不已,她們七嘴八舌問了牧師太太,牧師太太急急地講了什麼,似乎有點緊張,但大家又很快笑成一團。我有點吃驚,心想是否犯了什麼禁忌,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難道在Langalanga洗衣服要偷偷洗,不能給別人看到?還是女人的衣服要偷偷洗?
看我一頭霧水,牧師太太很熱心地翻譯和解釋。原來剛剛幾個婦女從田裡回來,看到我在門口洗衣服,她們覺得很新奇──「看,白人在洗衣服耶!」因為牧師家位於村中主要道路旁,從學校回家、從田裡回來的人大都會經過,於是聚集了一群人,像看馬戲一樣開心。有人問牧師太太怎麼讓我自己洗衣服?她怎麼沒幫我洗?於是她急忙解釋,是我堅持要自己洗的,可不是她怠慢。另外她也順道八卦了我中午不愛吃白飯愛吃地瓜的怪事。
我鬆了口氣,幸好不是做了什麼蠢事,只是打破了當地的刻板印象。她們第一次看到「白人」洗衣服的事情很快就傳遍村內,連續好幾天,我都是在眾人圍觀和大笑的狀況下洗衣服。幸好新鮮感很快就過去了,人們只會在經過時和我打招呼:
—妳在洗衣服阿?(Koe sau kaleko o gi?)
—對阿,我在洗衣服。(Eo, la kae sau kaleko gi.)
這也是我很快就學會的「實用會話」。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學習貼近當地人的生活與思考方式,關鍵的工具就是當地語言。在文化的研究上,許多概念必須要透過母語,才能精準地呈現,因此學習當地語言對深度了解當地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在實際使用的層面也是如此。雖然曾受英國殖民,目前義務教育的小學課程也有英文,但大部分村民鮮少使用英文。所羅門洋涇濱是各族間的通用語,然而村中女性多半不願意說。村民的對話都是以Langa¬langa語進行,因此若只會英語和洋涇濱,往往只能鴨子聽雷。我在進入田野前已經先自修過所羅門洋涇濱,田野初期進行的基礎家戶調查需用到的簡單問句「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幾個小孩?年紀多大?」等,以洋涇濱和大部分成人溝通不是問題,但真正要研究當地文化,不學當地話是不行的。
Langalanga語是所羅門群島八十幾種語言之一,使用的人口大約五千人,這麼小的群體可沒有現成教科書或語言學資料可用,一切得自己摸索。我一到村子就開始尋找能教我Langalanga語的老師,牧師太太立刻自告奮勇。首先是簡單的招呼與問候,早安、午安、晚安──這個容易。但接下來她立刻要我跟著重複長長的句子,結果聽到句尾時早就忘了句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這樣教我實在學不來。幸好過了一週,找到了理想的老師──塞勒斯。第一次見到他就印象深刻—他個子矮小,光著腳,留著像雷鬼歌手的髮型,穿著自己手染的波西米亞風彩色T恤,但講話非常溫文,與造型截然不同。他是村中少數能說流利英文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公認懂得深奧而古典的Langalanga語的人;大家認為我應該要學習最正確、最優美的Langalanga語,而他是最恰當的人選了。於是我開始每天早上到老師家的走廊上課,下午則做基礎家戶調查,有空就背單字和句型。由於沒有課本,雙方都沒有經驗,塞勒斯與我一起摸索,幸好在研究所上語言學時打好了底子,倒也順利愉快。猶記國中英文課時老師教我們背每日一句,從實用的句子入手,我也把這招帶進來。那麼要學什麼實用對話?很快地我發現要先背好下面的句子:
—你要去哪裡?(Koe la i fe?)
—我要去海邊。(La kae la i asi.)
—你剛剛去哪裡?(O io mae i fe?)
—我剛去了海邊。(Lau io mae i asi.)
每天平均要進行上述對話四至五輪,每輪遇到五到六個人,大家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因此我每日總共重複二、三十次這套對話,背得滾瓜爛熟,作夢都會夢到。的確,這裡的海景很不錯,落日尤其迷人,但不是我超愛「去海邊」──其實在Langalanga語中,「去海邊」是「上廁所」的文雅說詞。Langalanga是靠海生活的民族,聚落臨海而建,如廁處自然選在海邊,讓海水帶走所有不要的東西。一般村民都是走到村子南邊的紅樹林,選擇隱密處如廁,男人一區,女人一區。現在比較有錢的人開始學城裡的做法,在海邊蓋「小廁所」,有門有牆,甚至還有馬桶──但沒有沖水功能,要自己舀海水沖掉。
無論去哪種「廁所」,都得往海邊走。我住的地方離廁所距離兩百公尺左右,上個廁所可是大工程,半夜要去的話就慘了,還得找伴拿手電筒摸黑去,因此我精密的算好飲水與如廁時間,降低跑的次數。每次去廁所,一路上大家總是問候個不停,「你要去哪裡?」就和台灣人問「呷飽沒」來打招呼一樣,大洋洲很多地方流行問「你去哪裡」。剛開始我對於這樣的問候覺得很新鮮有趣,而且使用頻率很高,很快就能流利地背出那幾句對話,假裝一副好像學會Langalanga語的樣子,很有成就感。而且有些人聽到我說「去海邊」,還很讚賞那是優美的Langalanga話,而非粗魯地回答「去上廁所」(kabara)。
然而一陣子之後覺得有點厭煩了。距離廁所太遠,每次來回都得不斷問答,讓全村都知道我要去上廁所,或是剛剛解放過,實在是很沒隱私!而且小孩子發現這是我們唯一能「溝通」的語句,更不放過這麼好玩的事,他們特別愛問,沒完沒了,然後笑成一團。
有一天,我忍不住和塞勒斯抱怨此事。
「你也可以回答別的阿。」他說。
對啊,我怎麼沒想到呢?真是死腦筋。就像在台灣,路邊歐吉桑隨口問「呷飽沒」,也沒必要認真回答「我從早上忙到現在都還沒空吃東西快餓死了」。但在這個人際互動密切的小村子裡,亂答很容易拆穿,要如何不撒謊地回答?
「就說你溜溜罷了。」(Liliu mola.)
於是那成了我最喜歡的制式答案。而這個問候語的小困擾,再度成為我一窺當地文化的窗口。我對於這樣的文化差異感到很好奇,什麼樣的文化特性,會以到過哪裡、或要去哪裡作為相互問候語?(同樣地,為何傳統台灣人愛問「呷飽沒?」)後來我發現,「liliu」(走走、溜溜)在所羅門群島是很重要的一種人的移動──無目的、休閒性的閒晃,但具有建立並維繫人際網絡,以及交換資訊的功能。而Langalanga的問候語也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一個人去了哪裡,是連結人、地方和歷史的記憶機制。在Langalanga文化中,人在地景上的作為──旅行遷徙、建造房屋、開墾農田、種植作物、命名地方等,都是個人力量與能動性(agency)的展現,祖先的遷移尤其是當地歷史記憶的核心。在反覆練習問候對話時,我完全沒預料到看似簡單的語言學習第一課,竟啟發了我對Langalanga文化認識的重要突破,而人與地景的關係後來也成為我博士論文探討的核心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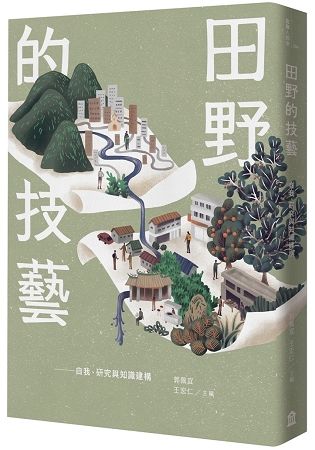
 2019/03/26
2019/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