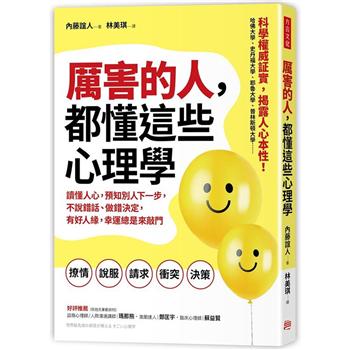【導論】
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當歐洲帝國向全球擴張,歐洲醫學也進行知識論與結構的根本改變。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歐一些小國開始建立全球帝國。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這位熱內亞出身的航海家從西班牙出發,在一四九二年橫跨大西洋抵達美洲。數年後,葡萄牙旅行者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一四九八年透過繞過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抵達了印度。這些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路,為西歐帶來與大西洋和印度洋新的在商業與文化方面的新接觸。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些區域有一大部分成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當歐洲人探索並利用這些殖民地的自然資源時,歐洲醫學也突破了古老的蓋倫式醫療(指的是──中世紀歐洲自西元二世紀名醫蓋倫(Galen)傳承之希臘醫學傳統)──並且從殖民地獲得金雞納、瀉根(jalap)、菸草與吐根(ipecacuanha)等新材料,以及關於其用途的醫學洞見。在越洋的漫長殖民航程以及在殖民前哨與戰場的艱苦勤務中,歐洲外科醫師取得重要的醫學技巧與經驗。歐洲在炎熱氣候中得到關於熱帶的熱病(fevers)、害蟲與病媒的醫學經驗,讓現代醫學得以整合環境、氣候與流行病學的因素,在隨後帶來所謂現代醫學的「整體論轉向」(holistic turn)。歐洲與其他種族相遇,而在現代醫學思想中建立了種族與人類演化的觀念。在此同時,現代醫學透過降低歐洲軍隊與移民的死亡率,推進了幫助殖民美洲、亞洲與非洲的殖民。歐洲的醫師、旅行者和傳教士把他們的醫藥提供給遭到殖民的種族,歐洲人將這樣的行為當成救命良方或是慈善與優越的表徵。本書探討帝國主義史與醫學史的交會,辨識歐洲帝國的興起與現代醫學的構成在知識上與物質上的連結。
除了探討醫學與帝國的歷史,本書還有兩個進一步的目標:幫助我們以全球尺度來理解醫學的歷史,也提出今日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層問題之歷史脈絡。
本書將此一漫長的歷史分為四大歷史時期: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1600-1800)、帝國時代(the Age of Empire,大約在1800-1880)、新帝國主義時代(the Age of New Imperialism,1880-1914)、以及新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年代(the Era of New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1920-1960))。每個年代在醫學史與帝國主義史都有其獨特的定位,但也有著延續和重疊。
歐洲帝國主義與現代醫學
從十六世紀起,歐洲人如何建立全球帝國?這些帝國是透過漫長而複雜的歷史過程建立起來的,以不同的階段來分別探討將這段歷史會有所幫助。第一個階段是貿易的時代,在新的貿易路線發現後,這段時期歐洲人(特別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開始在大西洋與印度洋建立航海帝國。西班牙人殖民所謂的新世界,而葡萄牙人則在亞洲與非洲的部分區域取得領土;這兩國對統治下的人口施加程度不一的政治與經濟控制。荷蘭、法國與英國等歐洲國家從十七世紀起加入海上的擴張,導致十八世紀重大的殖民戰爭。商業與貿易是這段時期權力與繁榮的要素,歷史學者常形容這是現代史上第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接下來是十九世紀的帝國時代。這個時期的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和英國,在亞洲和非洲建立起龐大的領土帝國(territorial empires)。歐洲人這時治理著龐大的人口,設計了殖民行政部門,發展出新的農業政策,訂定法律,創辦大學,並且在殖民地建立醫學觀念與實作。這些是歐洲人統治的支柱。此時也是歐洲的工業化時期,而殖民地則逐漸成為歐洲產業原物料的提供者,導致殖民地與全球經濟有更大的整合。這些經濟變遷也導致帝國內部大量人民由於成為移民或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ers)而遷徙。
十九世紀晚期出現一股更加競相擴大帝國領土的潮流,特別是在非洲;這段時期常被形容為新帝國主義的時代。工業國家之間進行全球經濟競爭以取得更多的資源和土地,追逐帝國的威望和領土以及傳播歐洲文明的渴望,導致在一八八○年代展開「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歐洲殖民強權在世界各大洲擴張,此一帝國主義的高峰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醫學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更為專科分化,來為殖民的目標與利益服務,這點特別可見諸熱帶醫學的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引人注目之處,是一些殖民地在這段時期展開追求獨立的國族主義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樣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更加蓬勃,在非洲尤其如此。這個時期也稱為「解殖」(decolonization),期間有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從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從事刺激而困難的建國大業。就文化與國族主義而言,這段期間這些國家對自己的醫療有更大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帝國主義並不總是依循著清晰或是線性的模式,這點很重要。帝國史的不同時期有顯著的重疊與平行。例如,「文化開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這個名詞,和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對非洲的殖民有關(這點我們將在第七章和第八章討論),此時歐洲人相信他們是透過殖民非洲而將現代文明與基督教引進該大陸。然而,這個名詞也可以適用於西班牙在十六與十七世紀的殖民美洲。西班牙人宣稱,要將基督教與文明帶給他們視為野蠻人的美洲原住民,藉由宗教使命正當化對美洲的殖民。同樣地,歐洲的大發現時代(European Age of Discovery)通常指的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當時歐洲人旅行到世界各地,對亞洲、美洲與太平洋地區進行自然史的發現與調查(參見第一、二章)。就非洲大多數區域而言,十九世紀下半才是發現的時代,尤其是在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的尚贊比西探險(Zembezi Expedition)之後,歐洲的地理學家和自然學者開始蒐集中非的動、植物,然後送到歐洲的博物館研究與展示。就本書所探討的醫學史而言,這些年代的重疊很重要,可以幫助我們注意並比較不同大陸、不同時期的歷史事件,了解期間的相關性聯與相似之處。
帝國主義的每個階段幾乎都明顯地和醫學史變遷的階段相互對應。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醫學不只是歐洲帝國主義的重要成分份,而且醫學本身也和帝國主義的歷史一起演變。本書第一章會描述十七世紀的貿易年代,歐洲的本草學(materia medica)大為擴張與多樣化(本草學指的是醫療所使用的各種物質及其製作方法)。異國藥物進口到歐洲市場,改變了歐洲的藥典與醫學理論。當歐洲人在十八世紀旅行到世界不同地方並遭遇到不同氣候,歐洲的疾病理論也隨之改變。醫生重整傳統醫學理論來解釋疾病,特別是他們在炎熱氣候所經歷的各種「熱病」(fevers);十八世紀的英國醫師廣泛討論所謂的「腐熱」(putrid fever)或「疫熱」(pestilential fever),這些熱病在漫長的殖民航程中侵害歐洲水手與海軍人員健康的所謂「腐熱」(putrid fever)或「疫熱」(pestilential fever)。為了因應船隻和殖民地營區過度壅擠的問題,詹姆士‧林德(James Lind)以及約翰‧普林高(John Pringle)等歐洲醫師發展出衛生理論。他們鼓吹採取衛生做法的必要性,包括海軍與陸軍之營區和船隻的垃圾處理、保持清潔以及確保通風。清潔與衛生的觀念在十九世紀逐漸成為歐洲預防醫學與國家政策的一部分(參見第三章與第五章)。在十九世紀,霍亂從亞洲傳到歐洲,的霍亂造成數次嚴重疫情,這為歐洲與美國重要的公共衛生措施鋪路。
另一方面,以實驗室為基礎的醫學在十九世紀的帝國年代改變了歐洲的醫學。歐洲的工業化與實驗室的成長,對現代藥品的生產很重要,也有助於現代製藥產業的出現,在法國和德國尤其是如此。第二章會說明,殖民主義如何使得以植物為主的藥物,轉型為使用現代製藥產品。從一八八○年代起,主要在法國和德國的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也帶來發展出病菌理論(germ theory),這主要發生在法國和德國。法國化學家與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透過對病毒的部分減毒(partial attenuation)來發展疫苗。他在一八八五年發展出狂犬病疫苗,而帶來著名的突破。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s)很快就散布到非洲與東南亞的法國殖民地,病菌理論與疫苗成為全球醫療與帝國醫學的一部分份。尤其是在一八九○年代的新帝國主義時期,殖民地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為法蘭西帝國「文明開化使命」的一部分份。這些新發展讓歐洲醫學在殖民地變得更加專斷自信。歐洲現代藥物與疫苗的進口與推廣,成為十九世紀殖民醫療政策的重要部分份。相較於過去的時期,這段期間醫療的關鍵差異是殖民醫學如今不只是專門照顧歐洲的水手、士兵與移民,還涵蓋當地居民。現代藥品與疫苗不只對於保護熱帶地區歐洲人的健康極為重要,也在殖民地也呈現為歐洲現代性與優越的象徵。
在新帝國主義時代,病菌理論在熱帶地區嶄露頭角;這段時間歐洲人認為熱帶的氣候環境是不健康的,這些區域充滿了疾病。對熱帶氣候的關切結合了病菌理論,而在十九世紀末帶來熱帶醫學這個新的醫學傳統。歷史學者指出,熱帶醫學鼓吹了十九世紀晚期的「建設性帝國主義」(constructive imperialism)觀念,尤其是在強烈帝國迅速擴張時期的非洲;這種觀念認為帝國主義終究會為受到殖民的人民與民族帶來好處。
另一方面我們在第十章會看到,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不是只以被動的方式接收現代醫學所帶來的各種變遷。亞洲與非洲的本土醫師和醫療人員以創造性的方式因應現代醫學,常用獨特的方式加以界定和運用、,同時也現代化其本土醫學。這在二十世紀國族主義意識與解殖運動興起時尤其明顯。亞洲與非洲的當地醫療人員回應西方醫學的支配,而將自已的醫學典籍化與標準化,挑選符合現代醫學觀念與要求的藥物與做法,引進新的醫療物質與現代實驗室技術,並且製作本土的藥典(pharmacopeias)。因此,所謂「傳統」或「另類」醫療的出現,是和殖民主義的歷史有關的。
二十世紀也是進行國際健康照護合作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之後的流行病,──像是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導致一九二一年設置國聯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LNHO)。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導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於一九四八年在瑞士日內瓦設立。世界衛生組織標誌著全球衛生與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時代。在這個時期,原本孤立的殖民地公共衛生措施和國際的政策與工作努力接軌,而以「全球衛生」(global health)之名為人所知。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的主要活動是針對麻疹、小兒麻痺與天花的全球疫苗接種運動、防瘧調查、處理貧窮與衛生的問題,以及保障世界不同區域的基礎醫療建設。二十世紀的全球衛生計畫與政策,是與殖民醫療措施合作下而所發展,而並保留強大的殖民遺緒。我們將會說明,為何了解殖民醫學史對於認識全球衛生的當代挑戰是很重要的。
【第九章】細菌學與文明開化使命
法國科學在大革命之後有一段沒落時期,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遠離帝國戰場的法國科學歷經了一段「黃金時代」,主要是隨著巴斯德式科學的興起而出現了實驗室研究的復興。直到十九世紀初期,醫師都還是藉由瘴氣和體液來理解疾病。到了一八三○年代,科學家找到證據,顯示酵母是一種小球體,能夠繁殖,因此具有生物的性質。在新式顯微鏡與實驗室的協助下,科學家透過實驗發現「生命的新世界」。到了一八六○年代法國微生物學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確定了發酵必須借助於細菌這種生命形式,發酵的變化具有生命的動態特徵。他主張對牛奶、酒或食物進行局部滅菌可消滅其中大部份分的微生物和酵素,使之能夠安全食用並改善保存。他在一八六四年示範在牛奶裝瓶前先以高溫高壓加熱。這個對牛奶、酒、農產品與食物進行部份分滅菌的過程,稱為巴斯德滅菌法(pasteurization),現在已經受到廣泛使用。
巴斯德接著主張細菌也引起人類和動物的疾病。這被稱為病菌學說,主要於一八八○年代在法國和德國的醫學傳統下大幅發展。他主張疾病是由病菌或微生物所引起,而非瘴氣、環境或體液所造成。德國醫師柯霍(Robert Koch)率先設計一系列的試驗來確認疾病的病菌學說。他在一八七五年首先應用其設下的判準來證明炭疽熱這種感染牛隻的疾病,是由炭疽桿菌(Bacillus anthracis)這種細菌所引起。炭疽熱是當時歐美農業與皮革業的主要憂慮。這些判準今天仍用來決定新發現的疾病是否是由某一特定微生物所引起。
另一方面,巴斯德結合病菌的辨認與部份分滅菌法的研究,發展對抗細菌的疫苗。巴斯德在一八七○年代將此一免疫方法應用於炭疽熱,在一八八一年成功製造出炭疽熱疫苗。然而,他最重要的突破是在一八八五年發展出治療狂犬病的疫苗,這種令人恐懼的疾病是從狗和野生動物傳染到人身上。巴斯德認為若要用實驗的方法實驗繁殖複製實驗用狂犬病病毒,主要目標應該放在神經系統上面。他和他的合作者透過讓病毒多次感染兔子來加以減毒。從剛死於狂犬病的兔子身上取出一條條新鮮的脊髓物質,並在消毒過的乾燥空氣中暴露一段時間,接著將脊髓組織研磨成粉,懸浮於消毒過的培養液中。此一溶液被用來製造疫苗。狂犬病疫苗的發現促成一八八八年在巴黎成立第一所巴斯德研究所,巴斯德在那裡為來自歐洲各地的人進行疫苗接種。
從一八八○年代開始,疫苗與巴斯德滅菌法成為巴斯德科學的兩大支柱,影響了法國的公共衛生政策、獸醫學、農業與食品工業。巴斯德研究所在歐洲進行狂犬病、炭疽熱、結核病與鼠疫的疫苗接種,並參與食品保存、農業、酪農與肉品生產的公共衛生工作,以及飲食與營養標準的決定。巴斯德研究所很快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特別是法國的殖民地,而病菌學說與疫苗則成為帝國醫學的一部分份。
病菌學說標示著一種決裂,一種和以體液學說與瘴氣論為基礎的既有醫學之間的決裂分道揚鑣,其歷史重要性就在於此。如今疾病的因果關係變得更為特定,而不再訴諸多重或多元的解釋。病菌學說認為病菌是真正的敵人,可以透過運用細菌學來辨認與消滅;病菌學說也將實驗室置於公共衛生政策的核心。實驗室也是殖民地的西方醫學與現代性的新制度與新象徵。病菌學說還帶來對人體的新看法:早期將人體視為環境的一部份分,在病菌學說之後,身體與環境是否和諧就不再重要,這點特別影響了置身熱帶環境之歐洲人的看法。如今人體(尤其是某些人的身體)似乎是充滿著細菌,必須接種疫苗或加以隔離。這建立了病菌學說的普世性: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出致病的病菌,並可以用疫苗加以撲滅。這也容許更為侵入性的公共衛生措施,國家和醫師可以將抗原注入公民或其他人的身體。
病菌學說挑戰了醫學的主要信條,在殖民醫學裡引進新的焦點,該學說認為熱帶的疾病是由病菌所引起的,而非炎熱或瘴氣。它也為殖民醫學帶來新的信心:熱帶氣候、瘴氣乃至於白種人在熱帶氣候下的退化皆不足為懼。接下來將探討這種信心在帝國的歷史中是有多麼地的有效和重要。
病菌與文明
我將就病菌與文明的關係來探究帝國主義下得史的病菌史。病菌學說發現特定的病原是特定疾病的成因,提供了消滅疾病新的可能性以及迫切性去消滅疾病。然而,醫師和衛生官員從未完全接受病菌學說。即便在病菌學說已經確立之後,盛行於熱帶地區或歐美窮人的疾病仍和數個世紀前一樣,和骯髒連結在一起。例如,一八九○年代的霍亂被形容為「由骯髒的人帶到骯髒地方的骯髒疾病」。
一八七○年代的酵素學說(zymotic theory)認為疾病是由分解與退化所造成,而創造了新的連結,將病菌學說與稍早的腐敗觀念之間的連結關連在一起,並納入原先和骯髒腐敗相連結的道德價值觀,認為骯髒與病菌都會助長疾病。【168】醫師相信道德瘴癘和物質瘴癘是相對應的;道德汙穢和身體汙穢同樣令人擔憂。就衛生與道德而言,新的病菌都代表了汙穢。病菌的「人類帶原者」(human carrier)理論認為,即便是最健康的人也可能在體內帶有病菌而感染他人,但本人卻沒有顯示出任何的疾病症狀,這重申了要根據種族和階級來進行醫學隔離。因此消滅病菌也成為一種清潔行動,清理掉汙穢、不乾淨的習慣與偏見,甚至隔離不受歡迎的種族與族群。另一方面,巴斯德學派的科學家、公共衛生官員、疫苗接種者和政府,認為消滅熱帶疾病或窮人的疾病不僅是針對病菌進行疫苗接種,也是改革社會與文化的行動。汙穢與病菌的觀念在熱帶殖民地被賦予新的意義,帝國的醫療人員採取道德十字軍姿態,對抗殖民地和熱帶的病菌、疾病與偏見。細菌學在殖民地成為科學與工業現代性的新象徵,。巴斯德滅菌法和疫苗接種在殖民地許諾了商業與工業的進步,。因此消滅病菌經常象徵著消滅野蠻。
在亞洲、非洲、澳洲及南美洲的不同殖民脈絡下,「文明」一詞取得了不同的意義。就階級、種姓與種族而言,它反映了一個群體或社群將其文化優越感強加在另外一群人身上,使得前者能夠決定後者的生活條件和經濟活動。病菌為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歧視和隔離提供科學上的有效性。例如,十九世紀晚期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該城的菁英使用「文明」與「病菌」等名詞來保護自己的特權並且,區隔城市的窮人。先是將窮人等同於汙穢與疾病的帶原者,接著將他們從市中心驅離,改變其日常習慣,並且大規模強迫接種疫苗。而里約城中日益增長的隔閡有更大的帝國背景。巴西是「非正式帝國」的一部分份,高度依賴外國對成長中的可可與橡膠大農場進行投資,這同時導致移工和都會菁英的增加以及貧富差距擴大。對國際資本的需求導致里約快速成長,國際資本提供資金並且規畫和督導經濟轉型,不僅里約熱內盧甚至整個巴西都是如此。城市菁英藉由「文明」一詞「改革」窮人的生活。由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奧斯華多‧克魯茲(Oswaldo Cruz)擔任公共衛生總長,採取清潔城市的新措施,並引進對都會窮人的疫苗接種。一九○二年克魯茲在里約建立細菌學研究所,並在城中展開嚴格的疫苗接種規定,且限制窮人進入城市某些區域,讓窮人遠離富人的視線。
在澳洲,「文明」用來標示白人居民和亞洲移民之間的分隔線。澳洲政府在二十世紀發動了一位記者所謂的「對外國病菌的戰爭」,基本上這是對中國移民的戰爭。在政府對「白澳」(White Australia)的想像與規劃中,中國移民被視為是危險病菌的不潔儲主。當鼠疫於一八九○年代在中國爆發時,這樣的觀念變得非常明顯。隨著細菌理論的興起,澳洲的檢疫系統變得更為嚴格與更侵擾。移民與病菌被視為是同義詞,澳洲政府為了保護邊界不受入侵,甚至在一九二○年代介入美拉尼西亞與波里尼西亞島嶼的公共衛生事務。澳洲的衛生官員如此做,就是認為島民「原始」而容易受到病菌侵襲,需要現代科學衛生措施。澳洲醫師在太平洋島嶼建立預防衛生措施,自認為是在將文明帶到這些島嶼。
病菌與文明在巴勒斯坦指涉的是現代性與東方主義之間的分隔。李奧‧波姆(Leo Böhm)這位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醫師在二十世紀初期發起運動,要在巴勒斯坦設立巴斯德研究所,。這個運動是要將「曠野」文明開化、並轉變為現代國族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部份。他的努力受到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orld Zionism Organization)的支持與鼓勵。該組織的成員抱持同樣觀點,認為猶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復國,有賴現代科學與科技的應用。由歐洲一些猶太醫師與博士所組成的「猶太醫師與自然科學家巴勒斯坦衛生權益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Jewish Physician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for the Sanitary Interests in Palestine)對此也加以支持。波姆在巴勒斯坦發動對抗瘧疾的戰爭,他認為瘧疾是現代文明的禍根。他也教導人們健康衛生的習慣以及檢疫制度的好處。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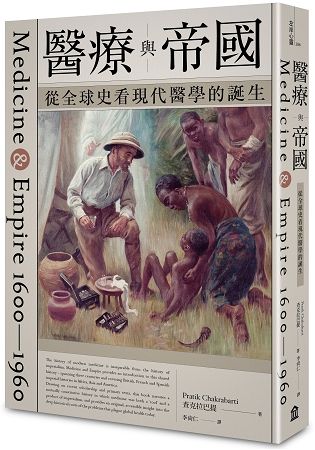 |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 譯者:李尚仁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2-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95 |
二手中文書 |
$ 434 |
世界歷史 |
$ 435 |
醫學總論 |
$ 435 |
醫學總論 |
$ 435 |
Social Sciences |
$ 468 |
健康醫療 |
$ 484 |
中文書 |
$ 495 |
醫療保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並理解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層問題。
現代醫學的誕生不是西方人獨自完成的。現代醫學具有濃厚的殖民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西方向外殖民的歷史,不只依賴軍事力量,醫學伴隨其中,扮演照護殖民者生命健康的角色。透過醫學的進展,我們可以了解現代世界如何應運而生;從西方國家在美、亞、非洲的屯墾殖民史,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如何藉由醫學促進經濟活動,完成文明開化的道德使命。
但是,醫學只是一種工具,幫助殖民者治理他者嗎?是殖民者帶來醫學福音,幫助被殖民者脫離疾病、改善環境嗎?根據歷史考察,答案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本書從西方將被殖民者的自然知識納入藥典,到對金雞納樹的生物探勘狂熱;從種族和氣候為基礎的疾病理論,到寄生蟲學到細菌學如何影響國際合作;從西方鄙棄殖民地的醫事人員,到殖民地傳統醫學的「被發明」,廣泛呈現醫學史的多層次與多樣性。直至二十世紀,殖民醫療措施仍延伸至全球衛生政策,掌握醫學史成為理解當代健康挑戰的鎖匙。
本書在地理尺度上橫渡美、亞、非,並顧及澳洲、太平洋島群;在時間刻度上,自十七世紀以降,橫跨三百年;在資料取用上,參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資料,總和出這樣一部作品,能夠回應過去各自研究者侷限於特定區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
推薦人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推薦記錄
「這是一本極為有價值的著作…達成並超過了教科書的要求,因為這本書所提出的綜合詮釋本身就很有價值。」──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英國牛津大學醫學史教授以及醫學史中心主任。
「這本書提供了和帝國史相關的敘述,將此一敘述放在對帝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功能更寬廣的理解之中;本書向讀者介紹此一主題豐富而多樣的歷史書寫,並提供當代醫學與國際衛生問題的長時程背景。」──大衛.阿諾(David Arnold),英國沃瑞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歷史學榮譽教授。
作者簡介: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目前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研究中心」,教授醫學史與科學史。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被英國大學聘任之前,於印度教書。著有《當代印度裡的西方醫療》(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物質和醫療》(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英屬印度的細菌學》(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他的研究主題,其地域擴及南亞、加勒比和大西洋,時間維度跨越十八到二十世紀,主題從科學史、醫學史展開到世界史、帝國史。是頂尖期刊《醫學社會史》編輯之一。
他曾經以水為主題進行過「淨化水」(Purifying the River: Pollution and Purity of Water in Colonial Calcutta)的研究計畫,未來這個子題會擴展成「全球南方的水歷史」。
譯者簡介: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有《帝國的醫師》(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譯有《老科技的全球史》《歐洲醫療五百年》《科倫醫師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
章節試閱
【導論】
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當歐洲帝國向全球擴張,歐洲醫學也進行知識論與結構的根本改變。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歐一些小國開始建立全球帝國。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這位熱內亞出身的航海家從西班牙出發,在一四九二年橫跨大西洋抵達美洲。數年後,葡萄牙旅行者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一四九八年透過繞過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抵達了印度。這些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路,為西歐帶來與大西洋和印度洋新的在商業與文化方面的新接觸。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些區域有一大部分成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
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當歐洲帝國向全球擴張,歐洲醫學也進行知識論與結構的根本改變。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歐一些小國開始建立全球帝國。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這位熱內亞出身的航海家從西班牙出發,在一四九二年橫跨大西洋抵達美洲。數年後,葡萄牙旅行者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一四九八年透過繞過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抵達了印度。這些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路,為西歐帶來與大西洋和印度洋新的在商業與文化方面的新接觸。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些區域有一大部分成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貿易時代的醫學,一六○○到一八○○
第二章 植物、醫學與帝國
第三章 醫療與殖民部隊
第四章 殖民主義、氣候與種族
第五章 帝國主義與疾病的全球化
第六章 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
第七章 醫學與殖民非洲
第八章 帝國主義與熱帶醫學
第九章 細菌學與文明開化使命
第十章 殖民主義與傳統醫學
結論:殖民影響下的全球衛生
第一章 貿易時代的醫學,一六○○到一八○○
第二章 植物、醫學與帝國
第三章 醫療與殖民部隊
第四章 殖民主義、氣候與種族
第五章 帝國主義與疾病的全球化
第六章 印度殖民時期的西方醫學
第七章 醫學與殖民非洲
第八章 帝國主義與熱帶醫學
第九章 細菌學與文明開化使命
第十章 殖民主義與傳統醫學
結論:殖民影響下的全球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