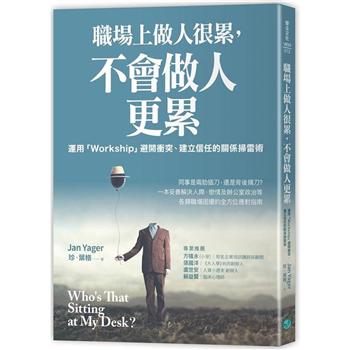夜半
「你歇一會兒不說話難道會死掉?整個下午給你一張嘴巴填滿了,嗡嗡嗡嗡地,跟蒼蠅一個德性。」木瓜不客氣地對冬生說,「讓人耳根清淨一會兒好不好?哥正想事兒呢!」
正說在興頭上的冬生,像突然斷了電的喇叭,戛然而止。兩片布鞋底般厚實的嘴唇還保持著打開狀態,張在寒風中,像出土的西漢說唱俑。灰僕僕的臉上剛剛著陸的兩朵紅雲,轉眼飛跑了。
可他的情緒還深陷在述說的興奮中,一時半會兒拔不出來。他眨巴眨巴眼睛看著哥哥,傻裏傻氣的,十分逗人愛。
對冬生來講,被哥哥呵斥是稀鬆平常的事。哥哥的脾氣就這樣,喜歡沉默,愛思考,琢磨事兒的時候,最討厭冬生那張隨便找個話題就能說得黃河潰堤的嘴巴。每到這時候,木瓜免不了擺出哥哥的派頭,呵斥弟弟。弟弟冬生呢,天生一副說嘴,讓他憋尿都可以,讓他憋話可不行。
這片小菜地,就是他弟兄倆為說話方便才開出來的。
那一陣,整個世界仿佛吃錯了藥,火柴廠凡是能貼點東西的牆壁,都給貼滿大字報,不僅要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受苦受難的世界人民,還要把內部的敵人清理乾淨,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別說做事情,連說話都得小心,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到處是身著草綠仿軍裝的革命群眾,無論男女,跟說話的腔調一樣,都一個款式。除了火柴廠,所有工廠都停產,所有學校都停課。火柴畢竟是家家都離不得的。
這塊地,位於火柴廠圍牆南邊牆根底下,有兩塊草席大。一年前,兄弟倆下班後,覺得閒著也是閑著,就把它開出來,種點蔥啊蒜啊辣椒啊什麼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木瓜覺得冬生嘴巴多,不給他找個說話的地方,即使不被人家打報告、揪辮子,也會憋出問題來―在這裏說話方便,只有他弟兄倆,冬生偶爾發幾句牢騷,說幾句怪話,沒人聽牆根,安全。
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個頭差不多,衣服穿得一樣,長相更是讓火柴廠的大嬸子姑奶奶們又好笑又犯愁,都說這一對「瓜錘」將來怎麼得了,誰家姑娘敢嫁過去啊,要不給他們編個號,保證其中媳婦兒一晚上要做兩回新娘。有人接話說,編號有啥用啊?脫掉衣服誰還看得出號頭?都一樣!一群娘們一提起弟兄倆,笑得腰桿都直不起來。
冬生知道哥哥並不是真的討厭他,就那脾氣,見怪不怪。而他冬生,傻慣了的,時不時被哥哥吼一嗓子還感覺特別舒服,不是親人,誰吼他呀,這世上,他就這一個親人!像這次,哥哥木瓜的呵斥只讓冬生愣了一下,僅僅一下,冬生吞了泡口水,粗大的喉頭一上一下動了一個來回,兩片鞋底很快正常工作起來了。這回,冬生換了話題。
木瓜無可奈何地掃了冬生一眼,晃了晃鵝蛋形的腦袋,埋下頭繼續鋤地。
他們要把這塊地翻過來撒小青菜。到開春,這裏將會綠油油一片。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某年某月某一天:李新勇中篇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94 |
華文創作 |
$ 332 |
中文現代文學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小說 |
$ 378 |
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420 |
小說 |
$ 54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某年某月某一天:李新勇中篇小說集
一個來自農村的樸實孩子,身上竟帶著珍貴的中醫古書?他在陌生的城市中學裡,會有怎樣的遭遇?
一個遇到寫作瓶頸的作家,在遇到暴雨而突然停電的電梯裡,竟然意外找到了靈感?
一個已經入棺的女人,怎麼會又活了過來?
在一個個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故事背後,是作者身為一位「70後」代表作家,對土地的尊敬和熱愛,以及對人性和自然的獨特思考。在不動聲色的批判背後,是作家對人、對世界的愛與寬容。
本書特色
本書共收錄18篇風格獨具的小說,是新銳作家李新勇的最新創作精選。
作者簡介:
李新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於《花城》、《長城》、《飛天》、《北京文學》、《小說界》、《青年作家》等刊物,並於《文匯報》、《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報紙文學版,先後發表小说、散文近三百萬字。出版小說集《麗日紅塵》、《風月》、散文集《穿草鞋的風》等七部。
章節試閱
夜半
「你歇一會兒不說話難道會死掉?整個下午給你一張嘴巴填滿了,嗡嗡嗡嗡地,跟蒼蠅一個德性。」木瓜不客氣地對冬生說,「讓人耳根清淨一會兒好不好?哥正想事兒呢!」
正說在興頭上的冬生,像突然斷了電的喇叭,戛然而止。兩片布鞋底般厚實的嘴唇還保持著打開狀態,張在寒風中,像出土的西漢說唱俑。灰僕僕的臉上剛剛著陸的兩朵紅雲,轉眼飛跑了。
可他的情緒還深陷在述說的興奮中,一時半會兒拔不出來。他眨巴眨巴眼睛看著哥哥,傻裏傻氣的,十分逗人愛。
對冬生來講,被哥哥呵斥是稀鬆平常的事。哥哥的脾氣就這樣...
「你歇一會兒不說話難道會死掉?整個下午給你一張嘴巴填滿了,嗡嗡嗡嗡地,跟蒼蠅一個德性。」木瓜不客氣地對冬生說,「讓人耳根清淨一會兒好不好?哥正想事兒呢!」
正說在興頭上的冬生,像突然斷了電的喇叭,戛然而止。兩片布鞋底般厚實的嘴唇還保持著打開狀態,張在寒風中,像出土的西漢說唱俑。灰僕僕的臉上剛剛著陸的兩朵紅雲,轉眼飛跑了。
可他的情緒還深陷在述說的興奮中,一時半會兒拔不出來。他眨巴眨巴眼睛看著哥哥,傻裏傻氣的,十分逗人愛。
對冬生來講,被哥哥呵斥是稀鬆平常的事。哥哥的脾氣就這樣...
»看全部
目錄
母親的朱家阿哥
小兄弟
飯票
青澀
在路上
洋蔥地上的兄弟
無邊落木
風月
夢醒
夜半
沒有身份的人
誰承諾的遠方
像鳥兒那樣飛翔
看起來什麼也沒發生
玫瑰炸彈
社日去看趙肉麻
荷爾蒙
你的寓言我的紙傘
小兄弟
飯票
青澀
在路上
洋蔥地上的兄弟
無邊落木
風月
夢醒
夜半
沒有身份的人
誰承諾的遠方
像鳥兒那樣飛翔
看起來什麼也沒發生
玫瑰炸彈
社日去看趙肉麻
荷爾蒙
你的寓言我的紙傘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新勇
-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4-03-04 ISBN/ISSN:978986572902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