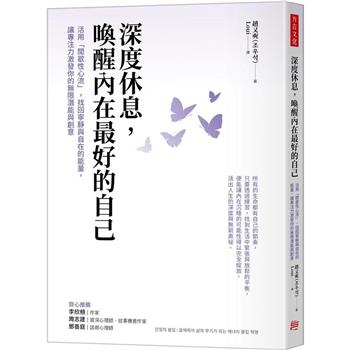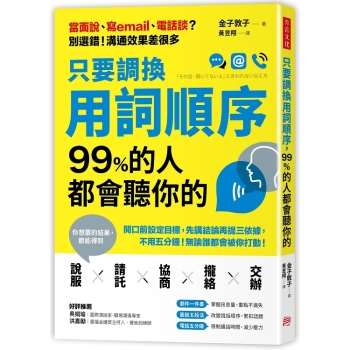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的圖書 |
 |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作者:唐納德‧大衛斯,尤金‧特蘭尼 / 譯者:馬建標,金瑩,秦嶺,盧曉璐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4-04-1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20頁 / 16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70 |
社會人文 |
$ 589 |
中文書 |
$ 590 |
政治 |
$ 596 |
社會哲思 |
$ 603 |
地緣政治/外交 |
$ 603 |
社會人文 |
$ 603 |
政治 |
電子書 |
$ 670 |
國際趨勢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本書通過對20世紀美國對華、對俄關係史的梳理,強調美國對中俄兩國長期形成的文化立場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而非美國對上述兩國的外交政策影響了這種文化立場。本書認為,縱觀20世紀美國對中俄兩國的關係史,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固有文化立場始終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而且這種觀念的影響對21世紀的美國對華和對俄關係仍然是重大的關鍵。假如這種固有的文化偏見再度出現的話,那麼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仍將受到它的莫大影響和牽引。
|